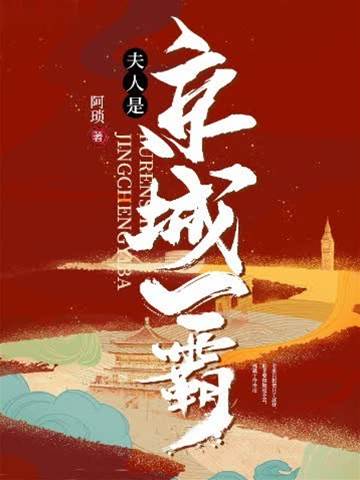《侯爺你咋不上天》 全部章節 第51章 你爲什麼沒有護住她?
跑了一天,蘇梨有些累了,靠在馬車壁上不想說話,楚懷安許是還在跟蘇湛賭氣,只雙手環盯著蘇梨,也抿著脣一言不發。
一路回到逍遙侯府,侯府門口停了幾輛馬車,也是有人前來拜會。
楚懷安下車看了眼,以往來侯府的多是他的那些酒朋友,今日這些馬車倒都是說得出名頭的。
一個昭冤令,影響便能如此大。
“侯爺,晚上有客人在,夫人讓您回來趕去飯廳,大家都等著你呢!”管家上前急切的說明況,楚懷安滿不在乎的吹了聲口哨:“急什麼,跑了一天,爺不得洗個澡換服麼?”說完回到自己的院子。
下人擡了熱水來,楚懷安溫吞吞的泡著澡,還讓蘇梨幫他按,又讓思竹不停地幫他送熱水來,折騰了將近一個時辰纔算完。
隨意地換了服,楚懷安這才帶著蘇梨和思竹前去飯廳,一進門,楚劉氏的訓斥便傳了來:“大家都在等你一個,謹之你也太不像話了!”
楚劉氏故意冷著臉,實際心裡哪裡捨得訓斥楚懷安,不過是給其他人一個臺階罷了。
下人將熱了好幾遍的飯菜又端上來,楚懷安落座,拉著蘇梨和思竹一左一右在他邊坐下,左擁右抱的,竟像是旁若無人的調。
其他人臉各異,楚劉氏再度開口:“謹之!別胡來!”語氣已是警告。
楚劉氏很疼楚懷安,一直也盼著楚懷安爭氣些,能做出點什麼建樹,不要一直這麼渾渾噩噩的過下去。
以往他在朝中任著沒什麼實權的閒職也就罷了,如今了昭冤使,得了昭冤令,朝中有人結上來了,楚劉氏自然也看得出這是楚凌昭信任楚懷安,要給他機會往上爬,楚劉氏當然希楚懷安能借機一展才華。
Advertisement
“娘,你又不是沒見過我這樣。”
楚懷安哼哼一聲,就著思竹的手喝了一杯酒。
蘇梨挽著袖子幫楚懷安佈菜,目不聲的掃過在座的幾人。
門外的馬車並不算多豪華,這幾人的階自然也不會很高,見楚懷安如此態度,幾人都有些無所適從,張幾次都沒能說出話來。
就這麼詭異的吃完一頓飯,待下人撤走飯食,楚懷安也沒有要陪客的意思,擁著蘇梨和思竹就要離開,終於有一個人坐不住,住楚懷安。
“侯爺,下乃貴妃省親那日的護衛副統領胡擂,那日是下的疏忽纔會險些釀冤案,還請侯爺大人有大量,莫要與下計較!”
胡擂坦的說,朝楚懷安拱手行了個禮,誠懇的道歉。
楚懷安拿著昭冤使可以隨意查抄任何人,這些人語氣等著楚懷安找上門來,不如自己先上門認錯,說不定還能從輕理。
“哦,原來是此事,胡大人不必張,本侯不是毫髮未傷麼?”
你現在是毫髮未傷,可這事不是已經捅破天了嗎?還能一句話翻過去?
“若侯爺有分毫損傷,下萬死難辭其咎!”胡擂跪下,其他幾人也都跟著跪下同呼。
楚懷安冷眼瞧著,心裡跟明鏡似的。
這些人都是聽命辦事的,如今出了事,上面的人不敢出面,便派他們來府上打探楚懷安的口風,以便做好應對之策,免得到時被楚懷安打個措手不及。
“各位大人這是做什麼,皇表哥給我這昭冤令也就是讓我玩玩,諸位都是肱骨之臣,本侯哪敢借機來,搖國之基啊。”
楚懷安說著,面上還是那副吊兒郎當的模樣,手裡拿著瓷白的玉箸輕輕敲著配套的鑲金邊瓷碗,發出叮噹的脆響。
Advertisement
這話說得也是實誠,楚凌昭再怎麼疼他,總不能把他這個大個人當親兒子疼,由著他胡來。
聽這話他像是能拿到分寸,衆人心裡都鬆了口氣,卻也不敢表現出來,只盯著自己的服下襬附和:“侯爺言重了。”
“諸位大人沒什麼事就回吧,爺耍了一天,困了!”
隨口一句打發了人,楚懷安擁著蘇梨和思竹回了自己院子。
一進屋,思竹招呼著下人送熱水來,過幾日纔開春,屋裡還燒著炭火,楚懷安扯了外套丟到桿上。
薄薄的中鬆垮垮的掛在上,約可以見白皙的膛和肋下面一小片青紫的痕跡,是蘇梨早上倒肘打的,這人質如此,稍微點傷,痕跡就會留很久。
方纔思竹也看見了這傷,只是微微皺眉,聯想到早上聞到的藥酒味,並未聲張。
晚膳前楚懷安剛泡了澡,這會兒熱水送來,思竹放了藥材在裡面給楚懷安泡腳。
“侯爺,忙了一天,泡腳解解乏吧。”
自了逍遙侯府,思竹也是真心在伺候楚懷安,這人花天酒地灌了,不知酗酒傷,便尋了許多解酒調養子的法子,變著法的給他補。
他仗著自個兒年輕不在意,旁人不能不替他著想。
楚懷安大約也習慣了思竹的伺候,鞋子一蹬,任由思竹捧著他的腳放進盆裡。
男人寬大的腳掌與人纖細的指尖形鮮明的對比,蘇梨只瞧了一眼便移開目,正想說沒什麼事就回去了,楚懷安被思竹按腳按得滿意的哼哼,衝蘇梨招了招手:“過來!”
蘇梨走過去,思竹按的作遲緩下來,猶豫地看著蘇梨,猜測著楚懷安是不是要讓蘇梨幫他按腳,卻見他抓著蘇梨傷的手細細的看,同時踢了踢思竹:“按你的,別停!”
Advertisement
說完手解開了蘇梨腕上的紗布,紗布上浸染的早就幹了,最裡面的一層與傷口粘連,楚懷安嘗試著扯了一下,立刻又珠涌出來。
“都粘在一起了,怎麼弄?”楚懷安皺眉,有些難以下手,不敢再扯。
這點傷對蘇梨來說本不算什麼,連眉頭都沒一下,擡手抓住紗布飛快的一拉。
凝結的塊被扯開,傷口立刻涌出來,涌得太快,有兩滴滴進盆裡,楚懷安瞳孔一,下意識的手替蘇梨按住傷口,沒好氣的怒吼:“老子讓你手了嗎!?”
他兇得很,好像蘇梨扯掉的是自己纏傷口的紗布,眼珠子攢著一團火,熾熱灼人。
“撒點止散就好了,沒什麼大礙,紗布和傷口粘在一起很常見,這樣還好得快些。”
蘇梨低聲解釋了一句,想回手,反而被楚懷安拉得彎了腰,與他湊得很近,聽見他憋著怒火的聲音:“爺不管你這過去五年是怎麼理的,在爺這裡,有什麼傷都給爺老老實實金貴的養著,一點疤都不許給老子留下!”
這話霸道極了,完全是他這麼多年的行事作風。
蘇梨垂著頭沒吭聲,楚懷安站起來,赤著腳踩在地上,把蘇梨丟到牀邊。
“思竹,去西街善世堂請大夫!”
大年初一,又是晚上,這個點找大夫出診得費多事?
可這人哪會管別人如何?
“奴婢這就去,侯爺還是先把鞋穿上吧,地上寒氣重,容易涼。”
思竹低聲說著往屋外走,出了門,還沾著水的手迅速變涼,凍得嚇人,連同那顆卑微至極的心也跟著發涼。
蘇梨回來的時候說不會和思竹搶楚懷安的寵,可就算不搶,只要回來了,楚懷安眼裡心裡就容不下其他人了。
Advertisement
過去五年,楚懷安沒過思竹,可除了這件事,其他的他都給思竹了。
這人看似紈絝,實則待人極大方,去攬月閣喝了花酒,沾著一胭脂氣回來,偶爾卻會給思竹帶些小點心,有時無聊了,也會在泡腳的時候跟思竹聊聊天說說話。
楚劉氏這些年擔心楚懷安的婚事,見思竹做事妥當,也曾提點過讓做楚懷安的通房丫頭,思竹過心思,卻又不願趁楚懷安醉酒做了別人的替。
心裡卑微的期盼著,想要待在楚懷安邊,若日子久了,楚懷安收了,那便是此生修來的福氣,就是做一輩子的通房丫鬟也願意,若是楚懷安不收,能一直待在他邊,做個己的丫鬟,也覺得知足了。
然而蘇梨回來以後,打破了思竹心裡這點微末的念頭,楚懷安所有的心思都撲在了別的地方,嘗過了他給的甜頭,怎麼耐得住如今這樣的寂寞?
思竹踏著月出府去請大夫,楚懷安抓著蘇梨的手坐到牀上,手探到的腰間,被蘇梨擋住:“侯爺想做什麼?”
楚懷安止了手,下微擡:“之前給你那塊玉呢?”
他說的是之前在宮裡給蘇梨那塊銀鏤空白玉,蘇梨從腰間出來,見隨將玉帶著,楚懷安點點頭,沒接,讓蘇梨把玉又揣回去。
“這玉先放你這兒保管著。”說完想到什麼,又盯著蘇梨警告:“爺是讓你保管,要是哪天在別人上瞧見,你揹著爺把這玉給張三李四做了定信,爺就宰了你喂狗!”
“……”
莫名覺自己拿了個燙手山芋。
蘇梨抿著脣沒說話,手上忽的一鬆,楚懷安將翻了個面在牀上,手扯了的腰帶。
“侯爺……”
“閉!”
楚懷安命令,抓著蘇梨的領蠻力一扯,將服退到腰間,小的背立刻暴在空氣中,雖然屋裡溫度不低,蘇梨還是打了個寒。
背上的鞭傷早就結痂,有的痂殼落,留下縱橫錯的傷痕,與陳年舊傷重疊,展示著過去五年他不曾參與的時。
然而除了那些鞭傷,蘇梨肩上和腰窩還有好幾磨破了皮,有的還往外冒著珠,楚懷安看得面黑沉,著一質問:“這又是怎麼來的?”
蘇梨被他得哼了一聲:“做活靶的時候揹著靶殼磨破了皮,不礙事。”
不礙事!
又是這三個字!
被施了家法說不礙事,背上這麼多舊傷說不礙事,中了劇毒還是說不礙事。
是不是隻有和陸戟有關的事才礙事?
腔被無名的煩悶填滿,楚懷安又想起白日在尚書府蘇梨和蘇湛親暱的樣子。
他再三的問過蘇梨,問蘇湛是不是陸戟的孩子,蘇梨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蘇湛再怎麼鬼,和蘇梨那種自然而然的親暱是裝不出來的。
楚懷安不想也不願承認,蘇湛會是蘇梨和陸戟的孩子,可如果孩子不是陸戟的,按年歲來算,那也只能是蘇梨當初失節於土匪時有的。
無論哪種結果,楚懷安其實都不願意接。
兩人安靜的待著,誰也沒有開口說話,蘇梨把腦袋埋在枕頭裡,不願面對屋被燭火映照的亮。
不知道過了多久,有人敲門,然後是思竹恭敬地聲音:“侯爺,大夫來了。”
話落,楚懷安扯了被子蓋在蘇梨上。
“進來!”
楚懷安站到旁邊,大夫進來,個子小,肩膀上掛著只藥箱,臉蠟黃,點著痦子,和上次見面完全是兩個人。
楚懷安皺眉,下疑問沒說,看向思竹:“你回去吧,有事我再你。”
“侯爺,一會兒大夫可能需要熱水或者筆墨開方子,奴婢可以幫忙……”思竹提醒,話沒說完,楚懷安不耐煩的擺擺手:“這些事我來就行,你走吧!”
他說得那樣理所當然,一點沒察覺這裡面有什麼不對勁。
他是逍遙侯,是生來就被人寵著伺候著的貴胄,什麼時候竟然能這樣雲淡風輕的去伺候另一個人?
“侯爺……”
思竹喃喃低語,窒息來得突兀,猝不及防。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337 章

獵戶農妻寵上癮
一覺醒來,竟成了古代某山村的惡臭毒婦,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就算了,還被扣上了勾搭野漢子的帽子,這如何能忍? 好在有醫術傍身,於是,穿越而來的她扮豬吃虎,走上了惡鬥極品,開鋪種田帶領全家脫貧致富的道路。當然更少不了美容塑身,抱得良人歸。 隻是某一天,忽然得知,整日跟在身後的丈夫,竟是朝廷當紅的大將軍……
58.4萬字8 5668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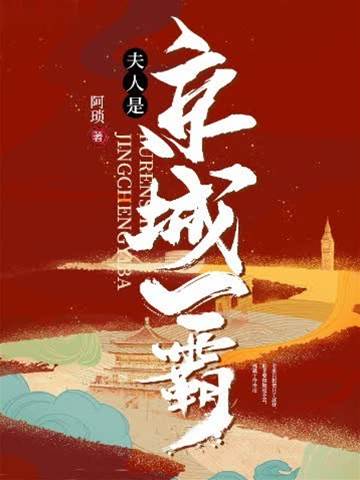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808 章

毒妃禍國不殃民
偶買噶,穿越成了惡毒女配?還作天作地作得人神共憤犯在了超級渣男手上! 好吧,既然擔了惡毒的名頭,她蘇陌涵就讓那些渣渣好好看看,什麼叫做“最毒婦人心!” 管她什麼白蓮,圣母還是綠茶,她蘇陌涵沒二話,就是一個字,干! 至于渣男嘛!嘿嘿,還是只有一個字,干!
173.5萬字8 19998 -
完結2428 章

農家娘子致富記
穿越到惡毒倒霉的肥婆身上,明九娘欲哭無淚——前身想謀殺親夫卻作死了自己……醒來時家徒四壁,兒子面黃肌瘦,相公蕭鐵策恨她入骨。 別人穿越懂醫懂葯懂軍火,她懂個鳥……語。 擼起袖子加油干,發家致富奔小康,相夫教子做誥命! 蕭鐵策:為了殿下,熬過這一次……這個毒婦總想攻略我,我抵死不從……從了從了,我給娘子暖被窩!
225.6萬字8.33 452725 -
完結185 章

權相養妻日常
重回豆蔻年少,令容只求美食为伴,安稳度日。 谁知一道圣旨颁下,竟将她赐婚给了韩蛰。 听到消息的令容狠狠打了个哆嗦。 韩蛰这人心狠手辣,冷面无情,前世谋朝篡位当了皇帝,野心勃勃。造反前还曾“克死”两位未过门的妻子,在令容看来,其中必有猫腻。 婚后令容小心翼翼躲着他,不敢乱戳老虎鼻。 直到韩蛰将她困在床榻角落,沉声问道:“为何躲着我?” 禁欲厨神相爷X吃货美娇娘,女主只负责美美美,架空勿考 前世所嫁非人,这辈子1V1;部分设定参考晚唐,男十五女十三听婚嫁,介意慎入哈
51.6萬字8.25 19300 -
完結258 章

抄家流放后,我搬空了敵人的庫房
【種田】+【流放】+【基建】+【雙潔】+【架空】開局穿成丞相府不受寵的嫡女,還是在新婚夜就被抄家的王妃。溫阮阮:我要逃!!!帶著我的空間先收王府的庫房,再去渣爹的府上逛一逛,順便去皇宮收一收,給皇帝和渣爹送份大禮。流放就流放吧,一路上順便罵渣爹,懟白蓮,好不樂哉。等到了蠻荒之地,再和自己的便宜夫君和離,逍遙自在去!“王爺,王妃又逃了!”“找,快去找!”入夜,蕭塵淵猩紅著一雙眼,在她耳邊輕語,“阮阮,不是說好了,會一直陪著我嗎?”
45.1萬字5 446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