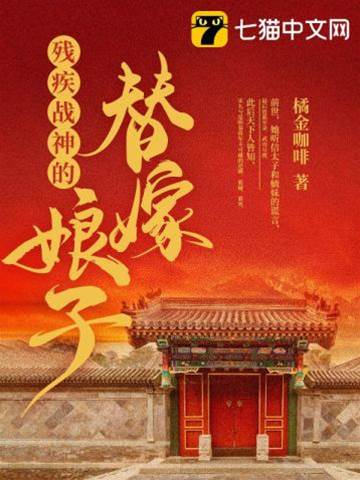《郡主有喜,風光再嫁》 第53章 圣旨到
梅香倒還的將門關上。
舒適寬闊的正房之中,兩人相對而坐,氣氛便的十分微妙。
蕭玉琢了,笑著開口,“當初我仗著蕭家在朝中的權勢,仗著我娘親是長公主,鬧著要先皇下旨賜婚,是得你不得不娶我……是我唐突了你。”
心里繃不住的笑,溢出在角,只好微微彎低頭,好似賠禮道歉般,遮掩住臉上的欣喜。
“如今既然有公主對郎君如此上心,蕭家又不復昔日風,我如何能再擋郎君的福氣?”蕭玉琢搖頭嘆息,“只愿不是好的開始,卻能好好結束。郎君一紙放妻書給我,也好另娶公主。”
真正的壽昌郡主已經為了他吊死了,才不要再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樹上!
不是說三條的蛤蟆不好找,兩條的男人多得是麼?何必守著個不自己的男人,擔驚怕的,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被人給害死了?
“不能與郎君相濡以沫,只盼著不要彼此生恨。以前得罪過郎君的地方,郎君念在我及時為公主騰地方的份上,都既往不咎了吧?”蕭玉琢拿著帕子,假惺惺的沾了沾眼角。
景延年一直沒有說話。
抬頭看他一眼,清了清嗓子,“雖還不知是哪位公主,但先恭喜郎君就要作駙馬了……”
一室安靜。
蕭玉琢抬眼看著景延年半晌,他穩穩當當的坐著,形如鐘,不不說。
蕭玉琢微微皺眉,這是什麼意思?
“郎君意下如何?”試探問道。
景延年的目落在上,陳墨暈染的眼眸太過深沉,人看不他的緒。
他俊臉淡然,似乎并沒有生氣呀?
“郎君若是懶得筆,不如由我代勞?郎君只用落下名諱就好。”蕭玉琢心急。
Advertisement
景延年哼笑一聲,“蕭氏,你想和離?”
口氣不對啊?蕭玉琢心中警鈴大作。
細細打量他神,小心翼翼道:“郎君若覺得有損面,那……那休妻也。”
“蕭氏,”景延年忽而傾靠近,雙眼盯著的眼眸,要噴薄而出的怒氣翻滾在他墨的眸子之中,“你記不好啊?”
蕭玉琢皺眉,“我記很好。”
“不準再提休妻的話,我才說過沒多久,你倒忘得干干凈凈了?”景延年冷笑。
他牙齒潔白整齊,這麼齜牙一笑,只讓人覺得眼前寒閃爍。
蕭玉琢向后退坐了些,那日王氏小產,在園子里他確實說過,可……可如今看上他的人是公主啊!公主怎麼說也比這個過了氣的郡主尊貴的多呀?
“你還說什麼?”景延年一面說,一面起靠近,“恭喜我為駙馬?”
蕭玉琢干笑著點頭,“是,是啊……”
他抬手擒住的肩膀,他手指修長有力,宛如鷹爪,抓得肩膀生疼,“唔,你弄疼我了……”
“你看我像是要尚公主的男人麼?”景延年一把將從坐榻上拽了起來。
他順勢將扛在肩頭,大步朝室走去。
蕭玉琢屁朝天,腦袋朝下,額頭磕在他堅實如鐵的脊背上,登時頭暈眼花,“你放我下來!”
砰——
被扔在了寬大的床榻上,的被褥都被砸的深陷下去。
他傾下。
蕭玉琢大驚,“修遠,修遠別怒……”
“呵,”景延年冷笑一聲,“你都自家夫君去尚公主了,還我別怒?”
尚公主這說法,在他口中,怎麼聽怎麼有點兒小白臉兒的意思。
蕭玉琢懊惱,就不該提駙馬這茬的,景延年這種剛愎自用的男人,當面這麼說,不跟打他臉,諷刺他靠人吃飯一樣麼?
Advertisement
“我說錯了,你且饒……啊!”蕭玉琢尖一聲。
上一涼,景延年已經手撕開了繁復漂亮的羅。m.166xs.cc
“景延年,你給我……唔……”
他低頭含住的。
蕭玉琢拼命的掙扎,都說到和離,說到休妻了!現在——這算什麼事兒?
“放開我……”從牙里出含混不清的字來。
奈何那點兒力氣,在景延年面前本不夠看。
他終究是將的服服帖帖。
蕭玉琢以為又是一場磨難,不了還要在床上躺個一天兩天的。
不曾想他竟頗有耐心,并不像剛占據了這副時那般魯殘暴。
以至于蕭玉琢從腳尖到發梢都是抖的,興的抖。人里的有時候不大腦的控制,歡愉就是歡愉,不會騙人。
第一次真真正正的會到,夫妻之事床笫之間,原來是這麼的讓人迷醉,回味無窮。
香汗淋漓的躺在他懷中,連掀起眼皮的力氣都沒了。整個人從里到外都是的。
“記住了?”他的聲音帶著歡愉之后的慵懶,好聽的人耳朵都生出眷來。
蕭玉琢唔了一聲。
“還我休了你,去尚公主麼?”景延年笑了一聲。
蕭玉琢假裝睡著,并不理他。
景延年抬手勾起的下,“我問你呢?”
蕭玉琢閉了眼,“好困……”
他翻又將下。
“不說了,再不說了!”蕭玉琢連忙投降。
……
這夜,景延年在主院沒有離開。
寬大的床,本離他遠遠的,可醒來的時候,卻不知怎的就滾進了他的懷里,枕著他強壯有力的手臂,口水濡了他的皮。
蕭玉琢連忙又滾遠了些,再睜眼——又在他懷中,不但枕著他的胳膊,還抱著他的腰……
Advertisement
蕭玉琢扶著酸的腰,憤憤起。輕手輕腳來到門外。
“過來。”拉開門,朝外喚道。
梅香正在外頭,聽聞聲音,連忙上前,眼角眉梢都是興之意,“怎樣,怎樣?郡主得償所愿了麼?”
蕭玉琢嘆了口氣,輕輕搖頭。誰知道他為什麼不肯和離呢?分明現在是對他最好的時機呀?
梅香一聽,小臉兒便垮了下來,“聽起來激烈的呀,郡主的月信恰好過去十天,時間也剛好……不會是郎君不行吧?”
蕭玉琢翻了個白眼,他不行?
“香過來!快點!”
梅香愁眉苦臉,蹬蹬蹬跑去香。
“熬一碗避子湯,速速送來,要快!”蕭玉琢伏在香耳邊說道。
香驚愕的瞪大了眼,“郡主,這湯藥傷,您正清寒毒,不能……”
“輕重緩急我還分得清,快去,別驚了郎君!”蕭玉琢沉下臉來。
香被的臉唬住,不敢再勸,輕手輕腳的退了下去。
蕭玉琢時不時從屏風外向床上張一眼,見景延年一直都睡的沉沉的,才松了口氣。
不過小半個時辰,卻張的度秒如年。
香小心翼翼的端來一碗濃黑的湯藥,連忙接過。
“郡主!”香皺眉,“您想清楚了?這一碗藥下去,本來肅清的差不多的寒毒,又沉積下來……”
蕭玉琢連連點頭,“我明白,這不是形勢所麼?”
仰頭就要喝。
卻有一只大手,猛的將碗奪去。
蕭玉琢只覺背后一涼,僵的回過頭。
景延年是什麼時候站在背后的?怎麼一點兒腳步聲都沒聽見?
“這是什麼?”景延年端著藥碗,似笑非笑的看著。
蕭玉琢莫名覺得嗓子有些,“補……補氣的。”
Advertisement
“香?”景延年一把推開門。
香噗通跪倒在地,卻閉口不言。
景延年笑著點頭,“不說?去請大夫來驗驗。”
蕭玉琢面泛冷。
“若不是補藥,就砍了香的手。”景延年冷聲說道。
香跪在地上,埋著頭,仍舊不吭一聲。
“來人——”景延年揚聲喚道。
蕭玉琢面如寒霜,“不用驗了,是我香調的避子湯。”
景延年端著藥碗,轉過臉來,的盯著的臉。兩人太近,他目里像是有把烈火,生生灼燙著。
蕭玉琢哼了一聲,“是我命準備的,你不可罰。”
景延年緩緩點了點頭,英武的臉頰映著初生的朝,染上了紅,劍眉星目看不出喜怒。
“你準備的?好。”
好字剛出口,他猛的抬手“啪”的摔了那藥碗。
白玉碗砸在廊下青石地面上,碎了渣。
濃黑的藥濺的四下都是。
“把這丫鬟給我帶下去。”景延年咬牙切齒,聲音像是從牙里出來的。
蕭玉琢大驚失,“你干什麼?”
景延年冷笑一聲,“你說呢?”
蕭玉琢跳出門外,擋在香跟前,“我的陪嫁丫鬟,不到你來管教!”
“你嫁我景家為婦,連你都是我的,更何況你的丫鬟?”景延年一把將拽懷中,反剪住雙手,讓人將香帶了下去。
“想讓活著回來,就乖一點。”景延年說完,放開了的手。
蕭玉琢著被他疼的手腕,著他離開的背影,滿心憤懣。
竹香卻在這時從外頭回來,拱手在面前,低聲說道:“昨日同舅夫人見面的兩個小娘子,是宮里的宮。”
蕭玉琢打起神來,“那便和青池招供的對上號了,是哪個宮里的?”
竹香皺眉,無奈搖頭,“一路跟著只見們進了宮門,哪個宮里的卻是不知。”
蕭玉琢長嘆一聲,當今圣上有好些兒,適齡未嫁的也有三四個。究竟是哪個和以前的郡主品味一樣,看上了這麼個喜怒無常的翻臉比翻書還快的男人?
“對了!”蕭玉琢眼中猛的一亮,“我們回蕭家去,阿娘的畫師照著描述,描繪出那兩名宮的相貌來。阿娘出宮中次數多,許認識也說不得!將此事告訴阿娘,阿娘定會幫我!”
竹香輕輕搖頭,“長公主何等份,豈會記得兩個小小宮?”
“總是有那麼一希的,就算不認識也無妨,好阿娘知道我在景府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那就能幫我……”蕭玉琢抿笑了笑,阿娘若是能同意離開景延年,并出面幫,這事兒就會簡單的多吧?
竹香皺眉不語。
梅香哭喪著臉道:“或許長公主還能給郡主指點,如何將香從郎君手中要回來。”
竹香一愣,左右看去,只見地上碎裂的瓷碗,和滲石的濃黑藥,“香怎麼了?”
梅香看了看蕭玉琢的臉,沒敢多舌。
蕭玉琢哼了一聲,不顧腰肢酸,是備車去往蕭家。
一路上梅香頻頻看向蕭玉琢。
無奈的別開臉,“想說就說吧。”
梅香嘀嘀咕咕將早上避子湯的事兒,告訴了竹香。
竹香本就有些黑的臉,更黑沉了幾分,小心翼翼的著蕭玉琢,默不作聲。
車廂抑的氣氛,蕭玉琢有些煩悶,掀開車窗簾子剛要口氣,就瞧見一輛寬大的馬車蹭著的車角,飛馳而過。
若不是景府的車夫躲得快,只怕要掀翻了的車架。
梅香驚呼一聲。
竹香連忙扶住蕭玉琢。
氣不順的蕭玉琢正要破口大罵,卻見那車架停在了蕭家的大門前。
“咦?這是老太爺的車架?”梅香眼尖口快。
老太爺的車架怎的那般躁躁?
蕭玉琢好奇的側臉看去,卻見幾個手腳麻利的宮人從車架上跳了下來,相互招呼著從車上橫著抬下一人來。
“呀……”梅香驚呼一聲。
竹香眼疾手快,連忙捂住的,“不可喧嘩。”
蕭玉琢心里一慌,快步向那馬車跑去,“祖父?祖父?”
門上的蕭家門房瞧見此形,慌忙開門,招呼門口等著的轎,將蕭老太爺扶進轎子,幾個轎夫腳下生風的往院跑去。
“怎麼回事?”蕭玉琢上前喝問那幾個準備退走的宮人。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904 章

田園錦色:空間娘子種田忙
她空間在手,醫術也有,種田養娃,教夫有方。他抬手能打,拿筆能寫,文武全才,寵妻無度!他們雙胎萌娃,一文一武,天賦異稟,最會與父爭寵!“孃親,爹爹在外邊闖禍了!”大寶大聲的喊道。“闖了什麼禍?”“孃親,爹爹在外邊招惹的美女找回家了……”二寶喊道。“什麼?該死的……”……“娘子,我不認識她……啊……”誰家兒子在外麵幫爹找小三,還回來告狀坑爹。他家就兩個!
266.7萬字8.18 93047 -
完結52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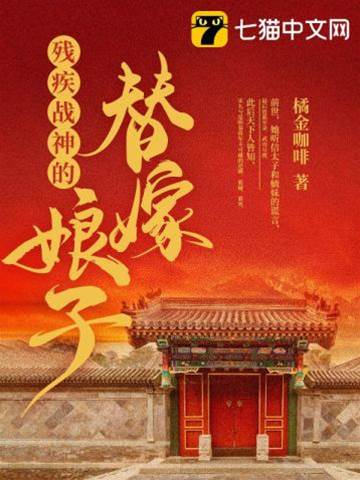
殘疾戰神的替嫁娘子
【重生+男強女強+瘋批+打臉】前世,她聽信太子和嫡妹的謊言,連累至親慘死,最后自己武功盡廢,被一杯毒酒送走。重生后她答應替嫁給命不久矣的戰神,對所謂的侯府沒有絲毫親情。嘲笑她、欺辱她的人,她照打不誤,絕不手軟。傳言戰神將軍殺孽太重,活不過一…
97.6萬字8.18 35390 -
完結530 章

撿了五個哥哥後,京城無人敢惹
流浪十五年,薑笙給自己撿了五個哥哥。 為了他們,小薑笙上刀山下火海,拚了命賺錢。 哥哥們也沒辜負她,為妹妹付出一切。 直到,將軍府發現嫡女被掉包,匆匆忙忙找來。 可也沒好好待她。 所有人譏她粗野,笑她無知,鄙她粗獷。 卻無人知道,新科狀元郎是她哥哥,新貴皇商是她哥哥,獲勝歸來的小將軍是她哥哥,聖手神醫是她哥哥,那一位……也是她哥哥。 假千金再厲害,有五個哥哥撐腰嗎? 不虐,男主未定,無固定cp,任憑大家想象 ???
101.3萬字8 193896 -
完結302 章
悍妃從商記
當再次醒來,看到兒子,她心情激動,卻不想卻深陷在一個帝王陰謀當中,且看花想容如何用自己的商業頭腦,打造一片,古代的驚天商業帝國……
77萬字8 110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