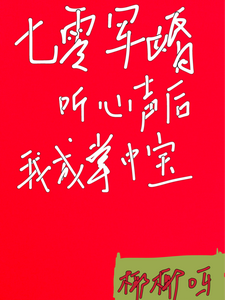《女配她一心禮佛》 47. 第 47 章 違令者,殺無赦
章玉麟尚未反應過來, 李慶元已經率領著一眾將士趕到了這邊。
郡主人還沒到城北校場,就已經發生了這等事,李慶元及他邊的將士臉都很不好看。
因著心中急切, 也怕郡主出事, 趕得很急。
然在一群人策馬拐了這條小道上后, 皆盡數怔住了。
四五百人的隊伍里, 眼下雀無聲。
李慶元的面一時間沒有繃住,他下意識看向了章玉麟,卻見章玉麟面上也有些怔忪。
是了, 一起從校場里出來的,章玉麟又能夠比他們快多,如何能夠在片刻間斬殺這麼多的人。
而且……
李慶元上前半步, 蹲下了子查探了其中的一尸。
這里的尸首,全部都是死士!
凡是能夠為死士的人, 皆是手了得的好手, 且所有死士接到的, 都是極為殘酷的訓練。
放眼去, 這道上躺著的死士尸, 就差不多有三四十人。
也即是說,在他們趕來之前,就已經有人將這刺殺郡主的所有死士,全部屠殺殆盡。
因為太過震撼,李慶元連一句話都說不出口,只被震懾在了原地。
死士訓練有素,便是他們趕過來,只怕也要跟對方纏斗一下,在人數絕對的優勢況下, 必然是會取得勝利的。
但也說了,是人數的絕對優勢。
并且還一定會有傷亡。
然眼下……
他看了眼馬車的方向,此前何等況不知,但他們趕到時,確實只看見了郡主一個人。
所以到底是誰救了郡主?
在城北校場的所有將士中,可以在這麼多死士的圍剿之下全而退的人,大概只有章玉麟吧。
“收拾一下,把這里的人,都抬到校場去。”溫月聲淡聲吩咐道。
Advertisement
章玉麟低聲應是,想了下,還是問道:“郡主可有傷?”
溫月聲道:“無礙。”
就是又損了一條新開的佛珠。
從頭到尾表現得不像是一個正常的子,因為正常子在看見了這一幕時,決計不會是這般冷靜,或者說是冷淡至極的表現。
然不知為何,周圍的將士此刻都不敢去多思多想,甚至不敢多去看幾眼。
總覺得現在并不是同郡主多說話的時候。
秋日確實多燥。
溫月聲一行人抵達了城北校場時,留守在了這邊的校尉匆匆行來,見得溫月聲沒事,也是長松了一口氣,隨后高聲道:“見過郡主、將軍。”
“郡主,皇上召見。”
皇帝的鑾駕也是剛抵達城北校場。
溫月聲第一天來校場,便遇見了行刺,皇帝震怒非常,親臨校場,命人徹查行刺之事。
同圣駕一起來的,還有恒廣、渭兩位王爺。
聽得溫月聲沒事,人已經到了校場中,殿中的氣氛總算是緩和了些許。
待得大軍整理好之后,底下的將士按照了溫月聲的吩咐,將皇帝一行人請到了外邊的高臺殿上。
皇帝走在了前面,渭王看著那校場上橫著擺放著的數十尸,當下便是一愣。
恒廣王傷暫未恢復,是以如今去哪都是坐著椅,被后的人推著,聽著底下人的回復:
“……是死士,幾乎全部是一刀斃命,其所用的刀,就是這些死士攜帶的刀,除此外,找到郡主的時候,整個道上只有三個活人。”
“郡主和邊的丫鬟,以及一個駕車的車夫。”
渭王聽得心頭狂跳:“那這些死士是誰殺的?”
“將士們趕到的時候,這些人已經全部死亡,所以暫且不知。”
Advertisement
恒廣王輕瞇了瞇眼睛,沉聲道:“看來思寧遠比咱們所想象的要厲害,邊除了章玉麟外,還有這樣的能手。”
渭王想了下,問道:“
難道是陸青淮?”
“不是陸將軍。”說這個話的,是前來赴命的李慶元,他定聲道:“陸家劍法所造的傷勢絕非是這般模樣。”
“且陸小將軍武藝高強,通諸武,但最為擅長的是長槍。”
不是章玉麟,不是陸青淮。
渭王扯了扯:“難不是思寧自己殺的?”
沒人搭理他。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場的人皆清楚,今日之事一出,那些暗地里不管是有想法還是沒想法的人,只怕都會消停不了。
恒廣王看了那邊幾眼,忽而道:“這般場面,思寧倒是面不改。”
皇帝座后,底下的人將今日遇刺的細節稟報了番。
他面冷沉,看向溫月聲:“此事你可有頭緒?”
派出來的死士全部被剿滅,沒有一個活口,想要查是誰的手,還真不太好查。
然越是如此,這邊的人臉越是難看。
皇上才賜下金腰牌,就有人按耐不住了手,這等行為,可還有將皇帝放在了眼里?
溫月聲那雙漆黑如墨的眼眸,較往常還要冷。
恒廣王道:“可是與你結仇之人?”
這話一出,殿安靜了片刻。
若提及與思寧郡主結仇之人,眼下所有的人都會想到景康王和梁府。
說起來倒也有幾分道理,梁家倒塌的源在于溫月聲,對憤恨到了極點,以至于無論如何都想要死,卻也是理之中。
渭王道:“要有私仇,往常什麼時候不能報,非得要選在了來驗兵的路上。依本王看啊,這哪是什麼私仇,分明是了有人的權益,某些人心里不舒服罷了。”
Advertisement
這個話可只有他敢說。
恒廣王面冷沉下來,譏笑著看他:“三弟,沒人教過你,凡事都要講究個證據嗎?”
渭王:“隨口猜測而已,大哥怎麼還惱了?”
“夠了!”皇帝冷聲斥道:“朕問的是思寧,問你們了?”
兩人同時噤聲。
溫月聲還在手,然怎麼,心底那燥意都褪不下去。
抬眸,冷聲道:“比起誰的手,眼下更應該查的,是軍中傳遞消息的人。”
“章玉麟。”
章玉麟聞聲,了兩個小將進來。
這兩個小將,是章玉麟到城北校場后,從新兵營里面提拔上來的。
尋常極跟在了他的旁,長相和武藝也不是最為起眼的,但為人格外聰明。
“回稟皇上,三日前,郡主接到了金腰牌后,便傳令于臣,讓臣在軍中挑出幾人,觀察全軍向。”
這話一出,滿殿安靜。
恒廣王和渭王臉都變了一下。
思寧得了金腰牌,卻沒有第一時間去往校場,原是早就已經提前做好了準備。
只是溫月聲以為對方會點什麼高明的手段,未想到竟是直接派人刺殺。
因前世的經歷,是以從未想過會遇到行刺這種事。
倒也是破天荒頭一回了。
溫月聲今晨去了天慈寺,沒有從公主府出發,而對方恰好埋伏在了天慈寺往校場的路上,便足以說明是有人傳遞了消息出去。
這傳遞消息的人,也只有兩種可能。
要麼,是溫月聲邊的人,要麼,就是軍營中的人。
不是溫月聲的人,那就只能是軍中之人了。
殿上的皇帝神微緩,沉聲道:“可有什麼發現?”
“回皇上的話,李慶元將軍的信,是今晨傳出去的,在收到了郡主回信之后,整個城北校場中,只有一人離開過校場。”
Advertisement
“此人便是孫校尉。”
他口中的孫校尉,是近來才提拔上來的武將。
殿安靜非常,沒想到這個走消息的人,竟還是個校尉。
這兩個小將的證詞可以互相佐證,幾乎坐實
了孫校尉傳遞消息的事。
孫校尉被帶上來時,竟還矢口否認。
“請皇上、郡主明察!”孫校尉高聲道:“臣今晨離開校場,是因為家中老母生了急病,府中之人著急,這才來校場找了臣。”
“前來報信的是府中管事,可任由郡主審問。”
溫月聲聞言,垂眸淡聲道:“聽見了嗎,去查他府中的管事,今日去過何,見過何人。”
那孫校尉一愣。
他斷沒有想到,溫月聲竟是連解釋都不聽。
旁邊的將士應下后,抬手,指了下孫校尉:“至于他。”
“拖到校場,斬首示眾。”
靜——
邊上的恒廣王驟然抬頭,那雙銳利的眼眸掃向了。
渭王亦是神大變。
在此之前,他們路上還有議論過。
“父皇將城北軍權予一個子,本就極為不妥,思寧那般養在深閨里的子,到了戰場上,只怕隨時都能嚇暈過去。”
“說不準此番的事,正好能將嚇退了。”
然真正到了這邊,發現不僅能面不改地面對那般況,且手段亦是極狠。
他們心中皆格外復雜。
“郡主、郡主!”那孫校尉也是慌了,他驚聲道:“末將是冤枉的,還請郡主開恩啊!”
溫月聲卻道:“你是不是冤枉的,待查驗過你府中管事便可知曉。”
那校尉神巨變,卻仍舊死咬著未松口。
溫月聲派出去的人作很快,迅速將消息傳了回來。
章玉麟沉聲道:“孫校尉府中的管事招了。”
“今晨他以買藥之名,去了醫館中,將郡主自天慈寺出行的消息傳遞了出去!”
那孫校尉聽得這番話,當下面如死灰,為求活命,當下高聲道:“郡主開恩!末將該死!此事皆是上面的人吩咐下來的,末將只是按照上面的吩咐在行事,求郡主開恩,饒末將一命……”
溫月聲并不想聽他的解釋,甚至當著幾位王爺和皇帝的面,并未過問指使他的幕后之人。
將死之人的會撒謊,證據不會。
起,往高臺上走去。
一邊走,一邊冷聲吩咐道:“將他拖下去,斬了。”
那孫校尉還未反應過來,便已經被拖到了場中。
下面的校場上,人頭攢。
溫月聲站在了高臺上,神淡淡,開口卻道:“我大徽將士里,容不得叛軍。”
“違令者,殺無赦。”
話音剛落,被按在了場中的孫校尉已是人頭落地。
滿場死寂。 com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94 章

七零炮灰嬌寵記
要是有後悔葯,林曼曼絕對會把愛看言情小說這毛病給戒掉,這樣,她就不會手賤去評論,就絕不會穿進書裡,成了一名炮灰。 這是一手爛牌,穿進的這書裡,是個七十年代不說,還是被書裡重生的主角報復的一名炮灰,因為跟姐姐搶物件,被重生回來的姐姐設計報復,成了家裡最不受待見的孩子,最後炮灰,下場淒慘。 她該怎麼辦? 唯有躲開姐姐的主角光芒,去當兵了。 PS:林曼曼是別人物件的時候,某人覺得她又矯情又作,當林曼曼成了自己物件的時候,某人覺得怎麼看怎麼可愛! 男女主軍人,女主文藝兵。
69.8萬字8 16376 -
完結480 章

穿書之沒人能比我更懂囂張
––伏?熬夜追劇看小說猝死了,她還記得她臨死前正在看一本小說〖廢材之逆天女戰神〗。––然后她就成了小說里和男女主作對的女反派百里伏?。––這女反派不一樣,她不嫉妒女主也不喜歡男主。她單純的就是看不慣男女主比她囂張,在她面前出風頭。––這個身世背景強大的女反派就這麼和男女主杠上了,劇情發展到中期被看不慣她的女主追隨者害死,在宗門試煉里被推進獸潮死在魔獸口中。––典型的出場華麗結局草率。––然而她穿成了百里伏?,大結局都沒有活到的百里伏?,所以葬身魔獸口腹的是她?噠咩!––系統告訴她,完成任務可以許諾...
86.1萬字8 11706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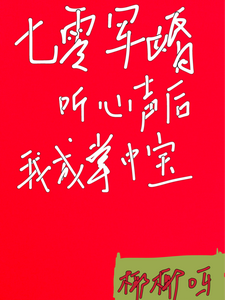
七零軍婚:聽心聲后,我成掌中寶
【心聲+年代+爽文+寵文+穿書+先婚后愛+七零+發家致富】 俞向晚穿成七零年代文中的炮灰。 新婚當晚,渣男被海王女主叫走,原主獨守空房,一個想不開,氣死了。 俞向晚:這能忍? 她當場手撕渣男,大鬧全家,奪回嫁妝,索取精神損失費,在新婚第二天離婚
19.2萬字8 5734 -
完結105 章

甜誘!協議結婚后京圈太子真香了
【已完結】【京圈權貴·病嬌瘋批大佬vs冷艷嫵媚·富貴嬌氣花】【女主身嬌體軟+自帶體香+萬人迷+修羅場+蓄謀已久+強制愛】 沈昭昭天生媚骨,一身冰玉雪肌,偏偏長相清純,極致的艷色與純真交匯。 令人沉迷。 某天,她穿進一本真假千金文,變成了流落在外的真千金。 為了利益。 寧家棄她與不顧。 屬于她的未婚夫更是選擇跟假千金結婚。 口口聲聲希望沈昭昭理解。 沈昭昭:祝福鎖死! 沒想到一夜荒唐,她居然招惹上了京城赫赫有名的太子爺。 榮鶴堯。 對方還要求她負責。 她們甚至還領了證!!! ———— 榮鶴堯,赫赫有名的權三代,京城數一數二的太子爺。 自幼含著鑲金鑲寶石的湯匙出生。 身高一米九,九頭身的完美比例,長著一副俊美清冷的絕世容貌。 自幼就被家中當做繼承人培養。 為人卻桀驁不馴,心思深沉。 在商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行事狠辣。 卻為愛低頭。 他說,昭昭,是你先招惹我的。 你要一輩子愛我。 我們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 ———— 眾人得知榮鶴堯結婚的消息。 都認為榮鶴堯只是玩玩。 紛紛下盤猜測兩人什麼時候離婚。 可只能眼睜睜瞧著素日他們瞧不起的平民,成了榮家的主母。 眾星捧月。 【HE】【雙處】
18.4萬字8 22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