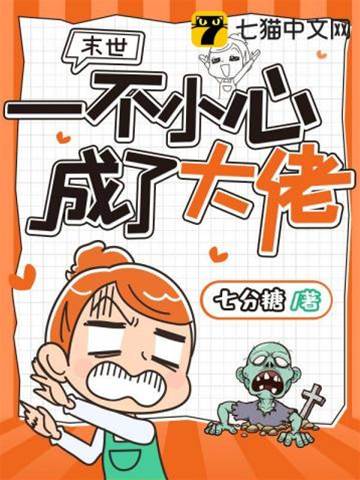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疾風吻玫瑰》 第88章 第88章
三天之后, “風暴”車隊來了都。
本來只是個小比賽,沈璐用不著親自來現場,但是江堯在這里, 也隨隊過來了。
除了維修組和后勤組, 也來了幾個新進隊的車手,眾人聚在一起開了個小會。
李堡是眾人里最高興的:“又可以和我哥一起跑比賽了,閑了大半年,我都快不認識東南西北了……”
眾人笑:“你哥發機一響, 你又要在車里。”
李堡憨憨地笑著:“我那是痛并快樂著的尖,你們懂什麼, 我哪次我哥沒贏?”
一旁的葉打斷道:“大寶, 這次比賽, 我做江堯的領航。”
李堡有點沒反應過來,“啊,你做領航啊?你怎麼做領航啊?”
江堯單手兜,嘖了下:“怎麼著,我老婆坐我副駕駛, 還要和你商量?”
“不是,哥, 你不要我了啊……”李堡覺得自己要被拋棄了,他哥重輕友, 嚶嚶嚶。
江堯敲了煙,低頭含在邊, “咔”地掀開打火機點上, 著眼皮看過來, “沒不要你, 下次, 這次跟我跑一次。”
李堡立馬高興了,他好哄得狠:“那不急,我等你,不影響你們兩談。”
江堯提了一條,還沒踹,李堡老早跑沒影了。
葉掩笑了一瞬。
江堯嘶了口煙,看,“他是金牌領航,不能不哄。”
葉:“哄唄。”李堡可是跟了他很多年的搭檔,江堯和他是相互就。
江堯挑了下眉梢,眉骨上的小痣也跟著了下,眼睛里亮晶晶的:“我這不是怕你吃醋麼。”
葉:“我又不吃男人的醋。”
江堯低頭靠在耳邊小聲說:“你可以吃,大不了我哄你唄。”
Advertisement
他靠得太近了,葉一偏頭,到了他的下。
江堯懶懶地垂著眼睫,看了一眼。
葉耳泛熱,立馬站直了。
沈璐:“坐下說吧。”
江堯吐了口煙,也沒再調戲葉,轉踢了張椅子給,自己拉開個凳子,在邊上敞坐下,胳膊過來,懶懶地搭在后的椅背上,也不是抱,只是有一下沒一下地卷的頭發玩。
葉看了他一眼,嗔:“開會呢,好好聽。”
“哦。”江堯挑挑眉把手撤走了,他臉上的表還是散漫的,著些藏不住的氣。
都的這場比賽,不是全國賽,只是片區賽,不歸fia管,也沒有太繁瑣的程序,比賽一共就兩天。
總里程94公里,一天堪路加開幕,一天正賽加頒獎典禮。
雖然是小比賽,但是因為在山區,盤山路,比賽難度還是比較大的。
沈璐:“我來之前查過天氣預報,后天有大雨,主辦方的意思是不發生地質災害,比賽就不會取消。”
葉聽完稍稍有些擔心,一旁的江堯很輕地握住了的指尖。
他掌心溫熱,而指尖冰涼,指尖被暖融包裹的覺非常鮮明,葉側眉看向他。
江堯正認真聽沈璐講賽程安排,側臉英俊,棱角分明,就像漫畫里出來的人。
那些新參賽的車手還有很多問題,沈璐依次做了回答。
江堯不聲地把的手翻折過來,指尖在掌心畫個心。
他做得而自然,除了葉,其他人都沒發現。
手心太了,葉想把手收回來,江堯偏偏不讓,他又寫了個“安”字。
他在讓安心。
葉很輕地笑了下,也沒什麼可怕的,應該要完全相信江堯。
Advertisement
wrc比賽可比這個難多了。
而且,是他的領航員,張會影響他的心緒。
沈璐講完,眾人各自回去休息。
次日一早,各個車組前往現場堪路。
天氣灰蒙蒙的,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
江堯開著車,和葉一起緩緩繞著賽道跑了一圈。
每一個彎道他都下來,仔細看一遍,然后把路書報給葉。
“江堯,明天下大雨,這泥土路影響大嗎?”
江堯把腳上的泥在草葉上:“有影響,不過可以克服。”
葉點頭:“好。”
里的路堪完,再對照路書走過一遍,確定沒有問題,他們才回到起點。
小比賽,開幕儀式比較簡單,卻吸引來了不育頻道的記者。
江堯傷后復出的第一場比賽,他們都比較關注。
賽車陸續排在了賽道的口,頭頂的無人機卻一直在拍藍旗亞。
葉偏頭看了看江堯,他目視前方,臉上的表非常自然。
江堯四下看了看,在視鏡里對上了葉的眼睛,不住彎:“,你看我?”
葉輕咳一聲,“沒有……”
“看就看了唄,有什麼關系。”他笑著,聲音有些許戲謔。
“我是看你不張。”葉解釋道。
江堯左邊胳膊搭在窗戶上,故意擰了下眉頭,“嗯……是有點張。”
葉當真了,“啊?那怎麼辦啊?”
江堯徹底笑出了聲:“我怕跑得太快了,你會暈車。”
葉連忙說:“我吃過暈車藥了,你大膽開。”
江堯抬手過去,握住了的后脖頸,兩人四目相對。
江堯指尖在脖頸里輕輕挲了幾下:“小玫瑰,你放心,今天我會贏的。”
他說話的聲音不高,聽上去就像某種許諾,有些鄭重其事,又很篤定。
Advertisement
葉眉眼含笑:“嗯,我相信你。”
前面的車子陸陸續續出發了,藍旗亞徐徐跟上。
下了雨,雨刮有節奏地在擋風玻璃上掃過去,視線還算清晰。
紅的旗幟一落,他們正式進了賽道。
藍旗亞全油起步,轟鳴的引擎聲,頃刻間漫耳,葉不敢懈怠,立刻開始讀路書。
短途賽道和環塔這些比賽不一樣,路面短時間的變化很快,本沒空聊天。
江堯的車速很快上了140m/h,葉并沒有時間揣測江堯的心理活,念得很快。
天氣越來越遭了,之前的細雨忽然轉做了傾盆大雨。
雨點“噠噠噠”地砸在前面的擋風玻璃上,雨刮開到了最快,視線還是有些模糊。
車窗敞著,暴雨落進來打了服,山道上的積水在車過經過的地方,飛濺出去,泥漿“噠噠噠”地落在車上。
很快,他們遇到了長下坡,大雨浸泡過的山路又又。
有兩輛車在前面發生了側翻,泥濘的山道上有長長的剎車印,側翻的車子擋住了小半個賽道,只剩靠山一側還有兩三米的路可以走。
葉立刻提醒,“事故,注意減速!”
江堯反應很快,作行云流水,剎車“刺啦”一聲。
慣作用下,安全帶在那一刻驟然變,葉的神經也繃到了極點——
眼前的這個況,和那次在阿廷的事故太像了……
擔心江堯,看了他一眼——
江堯遠比想象得冷靜、泰然。
藍旗亞降速后并沒有完全停下來,他稍帶方向,車著堅的石壁了過去。
路太窄了,后視鏡掉在地上,骨碌碌往后滾去。
后視鏡這種東西,對江堯來說本就是可有可無的存在,他也沒撿,直接提速走了。
Advertisement
車子過了這一段,葉驟然松了口氣。
江堯笑:“剛剛害怕了?”
葉:“嗯,很怕。”
江堯單手控方向,另一只手握了握的指尖:“別怕,我剛剛什麼也沒想。”
他的心理障礙不見了。
這才是江堯,真正的江堯。
葉抿繼續報路書。
出了山谷,他們遇到一條小河。
昨天,他們堪路的時候,這河還不能河,頂多算條小溪,邊上盡是碎石。雖然崎嶇,但卻是可以直接開過去的。
但今天山中暴雨,溪水暴漲,水位難測,碎石全部落在了水底。
那河邊也有碎了一地的零件,這是個事故多發地。
雨刮還在前面快速地擺著,視線在清楚和模糊指尖來回切換。
葉問:“江堯,要過嗎?”
江堯:“過!”
他沒有選擇直接過,而是把車往后倒過一段。
那里一個很小坡,剛剛他們下來時,江堯也沒整什麼花,直接開下來的。
藍旗亞往后退過一段,江堯一腳油門到底,葉看到儀表盤上的實時速度飆升到了240km/h。
藍旗亞巨大的引擎聲,“嗡嗡嗡”地響徹了整個山谷,如猛下山,如巨浪拍岸,驚雷滾。
葉下意識地了指尖,那一刻,江堯猛踩剎車,藍旗亞在那個小坡上騰空躍起一米多高。
葉的心也懸在了空中……
車子飛出去近三十米遠,藍旗亞直直地飛過了那條小河,后半截落在河水里,在后視鏡里迸濺起一米多高的水霧。
所以,他們剛剛是……飛過了那條河嗎?
葉心臟怦怦直跳,還陷在剛剛那個不可思議的飛跳里。
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江堯笑著提醒:“老婆,別發呆了,路書。”
葉回神,繼續報路書。
江堯的作太銥誮練了!他過彎干脆利落,路邊的葉子過車,迸落無數雨珠,大弦切切,小弦私語。
再往下,視線開闊了許多。
葉目灼灼,語氣輕快,“油門焊死,直線300米,飛。”
江堯了下齒尖,笑得狂狷而恣意:“yes,.”
藍旗亞箭一樣了出去,車速到270km/h。
風夾著雨卷進來,氣都有低。
電影也拍不出眼前的效果!
太快了!
第一視角更刺激!
葉只覺得從心臟往指尖蔓延,心口都在發麻、發燙,像是失了重。
坐過山車從最高點往下落的一瞬,才會有這種覺。
江堯越開越放松,稍稍側眉問:“怕麼?”
葉吞了吞嗓子:“一點點,太快了。”
江堯:“那我慢點?
葉:“不要!”
江堯笑:“心野了。”
又到了一個長坡,江堯油門到底飛了出去。
“葉,知道現在適合做什麼嗎?”
“什麼?”速度太快了,葉腦子都要一片空白了。
“表白。”
“江堯,你別說話了!前面左急彎下坡!”
江堯毫沒收油門的意思:“小玫瑰,昨天背了首詩,念給你聽啊?
the ed the sea,
(只要海鷗還眷大海)
ght the sun,”
(只要向日葵依舊繞著太轉)
葉再也繃不住了,尖起來,耳朵都快失聰了。
“啊啊啊——”
藍旗亞在合適點降速,一個大擺尾了出彎道。
江堯的聲音還在,語氣輕快:
“,i said, .
and me!”
(你我之間將永世不變)
葉眼窩發熱,心臟炙熱滾燙,江堯念的是王爾德的《的聲音》。
幾分鐘后,藍旗亞到了終點,毫無意外地拿了冠軍。
鮮花和采訪重新圍了過來,葉作為領航員也拿到了一個獎杯。
*
晚上,沈璐在都一家小酒館,給江堯整了個慶祝儀式。
眾人又又笑,喝了不酒。
屋子里有些悶,江堯出去點了支煙。
葉跟出來,手里端了兩杯酒。
一杯給他,一杯給自己:“江堯,破例喝杯酒吧,慶祝重生。”
玻璃相撞發出清脆的聲音。
孩眼中波瀲滟,江堯抿了一口酒,笑:“甜的?”
葉和他并排趴在木質的欄桿上往外看:“嗯,調了些荔枝味的氣泡水。”
江堯笑:“還會調酒?”
葉:“會一點點,之前跟德國的朋友學的。”
這時,李堡也從里面出來了,他喝高了,在發瘋,又是哭又是:“哥,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沈璐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往里拽:“行了,別過去打擾了,給人家留點空間。”
李堡嗓門特別大:“嗚嗚,我哥拿獎了!我哥拿獎。比我娶老婆都開心!我哥還找到對象了,瞅瞅多好啊!沈經理,我們隊發對象不?”
葉挑挑眉笑:“你不去哄哄啊?你的親領航哭了。”
江堯“嗤”了聲:“大老爺們要哄什麼?讓他哭去。”
葉笑,“哦。”
雨還在下,如線的雨粒“啪嗒啪嗒”地濺落在一旁的樹葉上,水汽蒙蒙。
雨夜寂靜又,空氣了附著著初放的梔子花的香氣,甜的,遠的繡球花暈染在白的暈里,霧氣騰騰。
后的木屋亮著橘的燈,說話聲、吵鬧聲斷斷續續的串在一起,熱鬧又嘈雜。
降溫了,稍微有些涼。
葉把杯子里的酒喝完了:“走吧,回去了。”
江堯握住了的手腕:“就走了啊?”
“不然呢?”葉笑得明。
江堯拖腔拽調,表拽拽的:“多得親一口吧?”
“好呀。”葉把杯子放在欄桿上,手環住了他的腰。
是想親他的,但是夠不到,踮著腳尖,也夠不到他的下。
江堯任由鬧,只是笑。
葉試了幾次有點惱了:“江堯,你低點頭!”
“抱歉,是我照顧不周,我們是小個子。”江堯把杯子放在,俯將抱了起來。
葉居高臨上,吻了他的。
甜甜的荔枝味在齒間渡。
江堯等親完,抱著從那木質的長廊里往外走,雨珠落在臉頰上,冰冰涼涼的。
“去哪兒?”葉問。
江堯語氣輕狂:“月黑風高,去車里收個賬。”
葉捶他的肩膀:“你瘋了!”
江堯:“本來要晚點,可你剛剛舌吻我,我忍不住了。”
作者有話說:
正文完結,接下來是甜甜的番外!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25 章
偏執薄爺又來偷心了
“再敢逃,我就毀了你!”“不逃不逃,我乖!” 薄煜城眼眸深邃,凝視著曾經試圖溜走的妖精,當即搞了兩本結婚證,“現在,如果你再敢非法逃離,我就用合法手段將你逮回來。” 女孩小雞啄米式點頭,薄爺自此寵妻成癮,護妻成魔。 但世間傳聞,薄太太癡傻愚笨、身世低賤、醜陋不堪,根本配不上薄爺的寵愛。 於是,全球的十億粉絲不高興了,“誰敢嗶嗶我們家女神?” 世界級的醫學研究院跳腳了,“誰眼瞎了看不上我們的繼承人?” 就連頂級豪門的時大少都震怒,“聽說有人敢瞧不起我們時家的千金?” 眾人問號臉,震驚地看著那被各大領域捧上神壇、身份尊貴的女孩。 薄爺旋即將老婆圈回懷裡,緋唇輕勾,“誰再敢惹我老婆……弄死算了。”
176.2萬字8 141276 -
完結4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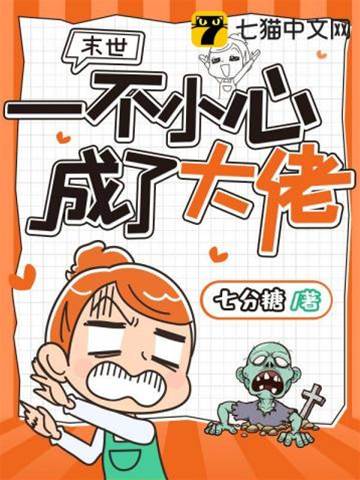
末世一不小心成了大佬
她在末世掙扎五年,殞命瞬間卻回到了末世剛開始,恰逢渣男正想推她擋喪尸。她踹飛喪尸,準備再掀一次渣男的天靈蓋!囤物資,打喪尸,救朋友,她重活一次,發誓一定不會讓任何遺憾再次發生。不過周圍的人怎麼都是大佬?殊不知在大佬們的眼里,她才是大佬中的大佬。
75.3萬字8 11226 -
完結2925 章

影后的嘴開過光
「江小白的嘴,害人的鬼」 大符師江白研製靈運符時被炸死,一睜眼就成了十八線小明星江小白,意外喜提「咒術」 之能。 好的不靈壞的靈?影后的嘴大約是開過光! 娛樂圈一眾人瑟瑟發抖——「影后,求別開口」
524.2萬字8 15366 -
完結486 章

離婚後,虐她上癮的京圈大佬腰酸了
閃婚一年,唐軼婂得知她的婚姻,就是一場裴暮靳為救“白月光”精心策劃的騙局。徹底心死,她毅然決然的送去一份離婚協議書。離婚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裴總離異,唯獨他本人矢口否認,按照裴總的原話就是“我們隻是吵架而已”。直到後來,有人告訴他,“裴總,您前妻要結婚了,新郎不是您,您知道嗎?”裴暮靳找到唐軼婂一把抓住她的手,“聽說你要結婚了?”唐軼婂冷眼相待,“裴總,一個合格的前任,應該像死了一樣,而不是動不動就詐屍。”裴暮靳靠近,舉止親密,“是嗎?可我不但要詐屍,還要詐到你床上去,看看哪個不要命的東西敢和我搶女人。”
86.8萬字8 341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