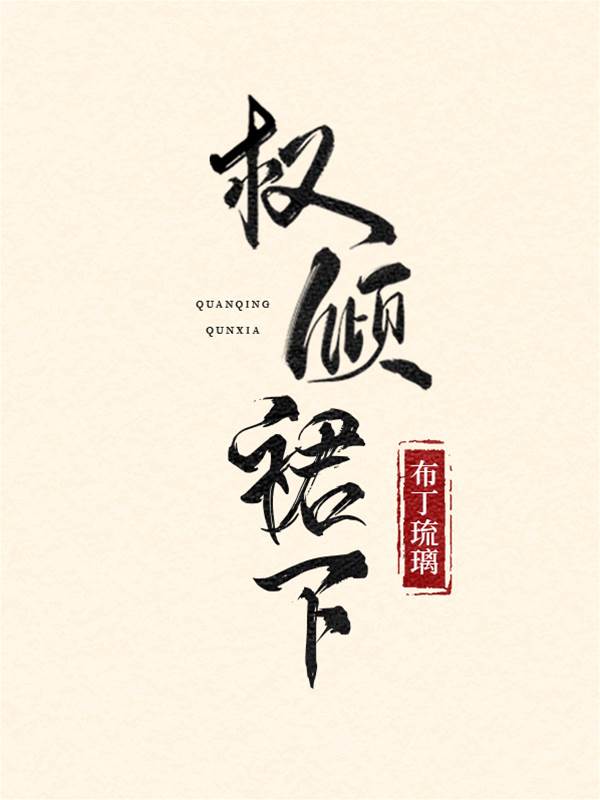《月照寒山》 第64章 陷害(大修)
玉瓊臺上,氣氛驟變。
太后大驚失,而唐公公也驚得了,手指一松,那幅畫便滾落在地,朝著莫衡的方向鋪地展開——
莫衡詫異低頭看去,頓時渾僵直。
畫卷上,先帝和太后并肩而坐。
先帝面容沉靜,表平和,一明黃的龍袍,顯得英武不凡,音容笑貌就在眼前。
一旁的太后著華麗宮裝,云鬢高華,眉眼妙麗,可角邊,卻滲出了一抹駭人的鮮紅。
這鮮紅恍若一跡,從角蔓延到了下,看起來格外刺眼我,讓這副溫馨的畫作,頓時變得無比詭異。
玉瓊臺上,嘩然變。
高麟怒不可遏:“大膽!”
沈映月和莫瑩瑩連忙起,直奔玉瓊臺中央,與莫衡跪在了一起。
莫衡心頭一震,立極伏地叩首:“皇上恕罪!在下也不知道什麼回事!?這畫下午出門時還是正常的,是不是庫房那邊出了什麼差錯!?”
莫衡聲音微,整個背脊都因惶恐而繃著。。
呈上畫卷的太監忙道:“皇上!這壽禮了庫房之后,沒有任何人過!莫衡公子可不要口噴人啊!其他的太監都可以作證!”
太后驚魂未定,不住地著心口。
永安侯伺機站了出來,開口道:“今日可是太后壽誕,鎮國將軍府真是大逆不道,居然敢詛咒太后!”
一提起“詛咒”,左相旁的趙老夫人嚇得不輕,憤然出聲:“你們竟敢對太后不敬!到底是何居心?”
羅夫人也適時開口道:“趙老夫人的話,倒讓臣婦想起一件事來。”
眾人不將目,轉向了羅夫人。
羅夫人道:“皇上,之前在機緣巧合下,臣婦買過莫衡公子的一副畫作……畫的是京城郊外的慈濟村,那副畫作之上,流民衫襤褸,傷兵捉襟見肘,境遇潦倒至極!簡直是看者流淚,聞者傷心。”
Advertisement
“莫衡將民間如此晦暗的一面畫下來,供眾人觀賞……是不是正好說明,他憤世嫉俗,對朝廷的治理不滿呢?”
話音一落,眾人也開始議論。
“難道是因為莫將軍為國捐軀了,所以莫家對朝廷不滿!?繼而詛咒太后?”
“有可能啊!鎮國將軍府門口的石碑上,不是刻了很多名字嘛!有怨氣也正常……”
“就算對皇室、對朝廷不滿,也不至于當面詛咒太后罷?”
“不管是不是故意的,畢竟是莫衡親手獻的畫!不罰他罰誰?”
玉瓊臺上,員們頭接耳,眾說紛紜。
鎮國將軍府在太后壽誕之日,獻上如此不詳的畫作,足以引來天子之怒!
高麟沉著臉開口:“莫衡,你還有何話說!?”
莫衡面慘白,辯解道:“皇上,冤枉啊!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詛咒太后,還請皇上下令徹查!還我們一個清白!”
莫衡的額頭上滲出了大顆的汗珠。
他努力回想著,這一路上畫卷都未曾離,唯一有可能的,便是在庫房中,被人了手腳,但那太監不認,如此景下,也不知道從哪里查起。
戶部尚書孫大人,不徐不疾地開口:“皇上,眼下也分辨不清鎮國將軍府,到底是有心還是無意,但這畫實在不吉!微臣建議先將莫衡扣押,嚴刑拷問!說不定他是人指使……”
沈映月一直沒說話,借著跪地的機會,仔仔細細觀察那畫作。
直到這時,才抬眸看了孫大人一眼。
孫大人的話聽起來中立,其實是要將整個鎮國將軍府拉下水。
若是莫衡進了大理寺,必然會面臨屈打招,顛倒黑白。
如今這種況下,就算皇帝要保他們,也有心無力——他們只能自救。
Advertisement
沈映月思忖片刻,便直起來,徐徐開口:“皇上容稟,要詛咒太后的,并非是我鎮國將軍府,而是另有其人。”
永安侯冷笑了聲,道:“明明是你們獻的畫,居然還要狡辯?”
沈太傅面上波瀾不驚,但見到沈映月跪在臺中,心頭也不免發。
高麟定定看著沈映月,開口:“你如何證明?”
沈映月一笑,甚至從容不迫地攏了攏耳邊發,然后手袖袋,掏出了一方白手帕。
沈映月道:“皇上請看。”
在眾人的注視下,沈映月用白手帕,蓋上了畫中人的,用力摁了摁。
高麟和太后,都忍不住凝神看去,只見片刻之后,沈映月翻轉手帕,沖眾人晃了晃——
眾人定睛一看,那白手帕上,果然有一抹鮮紅!
高麟面微變。
沈映月沉聲道:“皇上,這畫作在三日前已經完,其余部分的料早就風干了,唯獨這邊的‘跡’,還略微潤,可見是有人趁我們不備,了手腳!”
說罷,沈映月目掃視一周。
永安侯面一頓,孫大人下意識避開了目。
莫衡連忙道:“皇上,我們在一個時辰前,就將畫作到庫房了,這‘跡’一定是在庫房的這段時間里,被人加上去的!”
莫瑩瑩心中氣憤,跪地叩請:“皇上,只要盤查庫房的看守太監們,一定能找到蛛馬跡!”
沈映月收了手帕,沉聲開口:“皇上,這背后之人何其狠毒,不但詛咒太后,還陷害我鎮國將軍府!還皇上下令徹查,太后威嚴,不容侵犯!也請還我們一個清白。”
沈映月說罷,伏地不起。
莫衡和莫瑩瑩一看,也立即有樣學樣地趴了下去。
Advertisement
“皇上。”沈太傅終于開口,道:“此事確實蹊蹺,依老臣看,應當立即封鎖現場,找出幕后之人。”
高麟心中了然,詛咒太后不過是個幌子,作案人的真正目的,是想打鎮國將軍府。
高麟眸微沉,憤怒出聲:“將所有庫房的奴才都抓來!一個個搜!若有知不報的,同罪論!”
唐公公連忙應聲而去。
半個時辰后,一個小太監,被推到了玉瓊臺中央。
他子瑟一團,整個人不住地抖。
唐公公道:“皇上,此人宮不久,乃是務府的低等太監。方才搜之后,奴才發現,他的上有一罐印泥。”
說罷,唐公公便將印泥呈了上來。
高麟垂眸看去,那印泥的,與畫像上面的‘跡’十分接近。
唐公公道:“皇上,奴才已經仔細比對了,他的指甲里,還有未凈的印泥,應該是作案之后,來不及去凈手的緣故。”
高麟沉著臉,一拍桌案,怒道:“狗奴才!你哪來的膽子?”
小太監跪在中央,抖如糠篩,語無倫次道:“回、回皇上……是、是奴才整理壽禮時,一時不慎,弄臟了莫衡公子的畫作,這才招來了誤會!并非有意詛咒太后娘娘!請皇上饒命!”
小太監說罷,不住地磕頭。
莫衡氣憤不已:“方才為何不說?”
小太監帶著哭腔:“奴才見皇上大發雷霆,實在不敢……”
沈映月道:“這印泥弄臟的位置如此明顯,你既然弄臟了,為何一點拭或者清潔痕跡也無?”
小太監神一僵。
沈映月抬眸,看向高麟,道:“皇上,臣婦以為,一個小太監并沒有這麼大的膽子詛咒太后,陷害鎮國將軍府,他八是人指使。”
Advertisement
高麟微微頷首,表示贊同,道:“你到底何人指使?若是說出來,朕還能留你一個全尸!”
小太監面惶恐,只機械地磕頭:“奴才不是有意的!還請皇上饒命啊!”
磕頭間,他的眼神不住地看向永安侯,但永安侯卻繃著一張臉,角微。
沈映月恰好看到這一幕,正有些疑。
卻見那小太監,忽然起,一頭沖向了最近的石柱!
全場一片驚呼,唐公公大喊“護駕”,一時混不已。
頃刻間,那小太監頹然倒地,鮮流了半張臉,一命嗚呼了。
他自絕的地方,離沈映月不過一丈遠。
沈映月不由得渾一震,僵在了原地。
這還是第一次,見到有人死在自己面前。
永安侯面白了白,忽然起,走了過去。
他出手指,在小太監的脖頸探了探,不聲地松了口氣。
永安侯拱手答道:“皇上,此人已經咽氣了。”
說罷,他沖旁邊的林軍一揚手,道:“還不把人理掉!?”
林軍連忙上前,將小太監的尸拖走了,地上劃出一道痕,紅得耀目。
高麟不過是個十幾歲的年,自然又驚又怒。
但如今人都死了,此事更無從查起,便只得暫時作罷。
永安侯出笑意,道:“皇上,不如讓禮部繼續走章程罷?可別讓這曲,擾了您和太后的興致!”
高麟看了太后一眼,只見太后面無,而群臣和家眷們也惶惶不安,也覺得現在不是適合追究的時候。
高麟見沈映月等人還在玉瓊臺中央,便道:“方才事發突然,還好莫夫人聰穎,不然鎮國將軍府,便要蒙不白之冤了。”
沈映月斂了斂神,道:“皇上英明。”
太后卻有些可惜那副畫作,道:“好好的一副畫作,居然被歹人毀了這般模樣……”
沈映月恭敬道:“若太后不棄,莫衡可重新繪制一副,獻給太后。”
太后的臉這才好了些,微微頷首:“甚好。”
玉瓊臺上,重新開宴。
雜耍的班子一場,立即吸引了眾人的目。
那小太監的跡,被得干干凈凈,仿佛剛才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切如常。
而沈映月坐在席位前,沉默不語。
莫瑩瑩見面不好,低聲問道:“二嫂……你怎麼了?”
沈映月垂眸一瞬:“沒什麼。”
來到這個時代后,要麼是在府中經營,要麼是打理流閣的生意,還從未面對過這樣你死我活的局面。
就在方才的一刻鐘里,整個鎮國將軍府,差點為了階下囚,而轉眼間,陷害他們的人,又突然濺當場。
沈映月這才真真切切會到了,你死我活的殘酷。
-
壽宴如期散了。
眾臣攜著家眷,紛紛離開玉瓊臺。
永安侯帶著家眷準備離開玉瓊臺,恰逢沈映月等人也站在一旁。
永安侯看了沈映月一眼,似笑非笑道:“莫夫人運氣還真是好,一眼便瞧出了那畫的貓膩,實在厲害。”
沈映月冷眼看他,道:“運氣好的是侯爺罷?”
永安侯勾:“夫人說笑了。”
說罷,他便攜著家眷,離開了。
沈映月看著他的背影,眸更冷。
“莫夫人?”
沈映月斂了斂神,回頭一看,淡淡一笑:“唐公公。”
高麟親自護送太后回宮,便囑咐唐公公,留下來善后。
唐公公見沈映月等人站在此,便特意過來打了個招呼。
唐公公看了沈映月一眼,笑道:“今夜之事,還好夫人隨機應變,不然,鎮國將軍府只怕兇多吉。”
莫瑩瑩和莫衡聽到“隨機應變”幾個字,頓時有些疑。
沈映月凝視唐公公一瞬,微微欠,道:“多謝唐公公關照,這個人,我沈映月記下了。”
唐公公卻什麼也沒說,笑著離開了。
直到上了馬車,莫瑩瑩才忍不住問出了聲。
“二嫂,唐公公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81 章

愛妃在上
愛妃,良宵苦短,還是就寢吧。某王妃嬌媚軟語,伸手輕輕地撫摸著某王爺的臉頰:王爺,咱們不是說好了,奴家幫王爺奪得江山,王爺保奴家一世安穩,互惠互利,互不干涉不是挺好嗎!愛妃,本王覺得江山要奪,美人也要抱,來,愛妃讓本王香一個…王爺您動一下手臂行嗎?王爺您要好好休息啊!某王妃吳儂軟語。該死的,你給本王下了軟骨香!呵呵,王爺很識貨嘛,這軟骨香有奴家香麼?
56.1萬字7.67 24331 -
完結272 章

邪王獨寵:傾城毒妃狠囂張
金牌殺手葉冷秋,一朝穿越,成了相府最不受寵的嫡出大小姐。懲刁奴,整惡妹,鬥姨娘,壓主母。曾經辱我、害我之人,我必連本帶息地討回來。武功、醫術、毒術,樣樣皆通!誰還敢說她是廢柴!……與他初次見麵,搶他巨蟒,為他療傷,本想兩不相欠,誰知他竟從此賴上了她。“你看了我的身子,就要對我負責!”再次相見,他是戰神王爺,卻指著已毀容的她說,“這個女人長得好看,我要她做我的王妃!”從此以後,他寵她如寶,陪她從家宅到朝堂,一路相隨,攜手戰天下!
48.8萬字8 25055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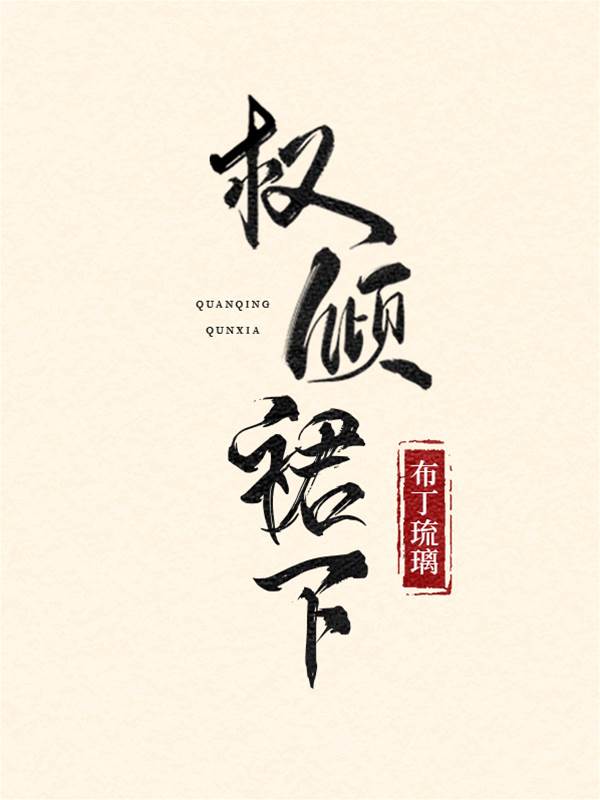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1779 章

快穿:病嬌大佬他好黏人南卿二二
南卿死亡的那一刻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能有一具健康的身體。死后,她綁定了一個自稱是系統的東西,它可以給她健康身體,作為報答她要完成它指定的任務。拯救男配?二二:“拯救世界故事里面的男配,改變他們愛而不得,孤獨終老,舔狗一世的悲劇結局。”“嗯。”不就是拯救男配嘛,阻止他接觸世界女主就好了,從源頭掐死!掐死了源頭,南卿以為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可是男配們卻一個個不粘世界女主粘
247.7萬字8.18 20931 -
完結63 章

長燁無月
【和親公主vs偏執太子】【小短文】將軍戰死沙場,公主遠嫁和親。——青梅竹馬的少年郎永遠留在了大漠的戰場,她身為一國公主遠嫁大晉和親。大漠的戰場留下了年輕的周小將軍,明豔張揚的嫡公主凋零於大晉。“周燁,你食言了”“抱歉公主,臣食言了”——“景澤辰,願你我生生世世不複相見”“月月,哪怕是死,你也要跟朕葬在一起”【男主愛的瘋狂又卑微,女主從未愛過男主,一心隻有男二】(男主有後宮但並無宮鬥)(深宮裏一群女孩子的互相救贖)(朝代均為架空)
20.9萬字8.18 17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