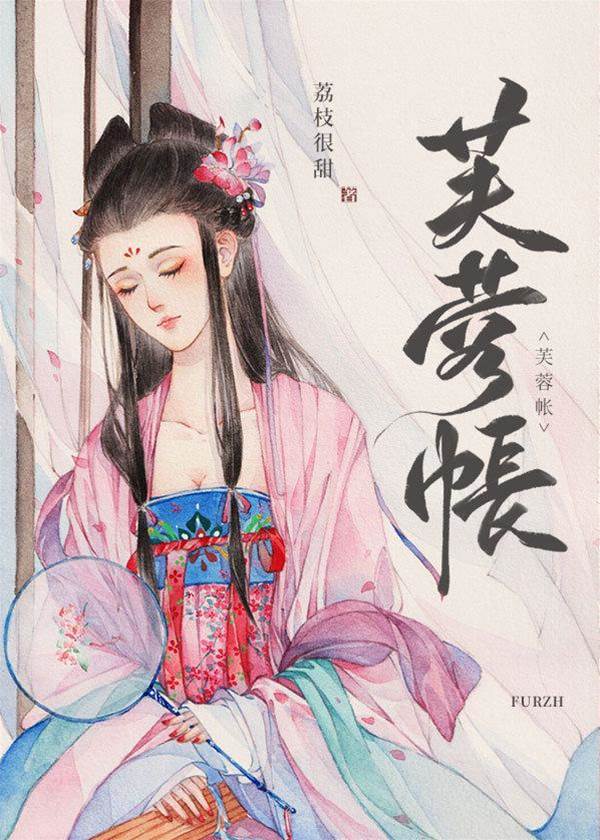《沈婠複仇紀事》 第50節
昨天夜裏頭,沈婠想了又想,決定不刻意地拒絕,幹脆順其自然。
兩人聊得很是暢快,說起醫時,魏子騫換上一副敬仰的模樣,道:“京城裏若是論起醫,怕是沒有人能及得上容銘。沈姑娘,你可有聽過容神醫之名?”
沈婠是容銘的學生一事,京城裏甚人曉得。
容銘不願太多人知道,特地與沈老太爺說了最好莫要聲張。老太爺也應允了。如今曉得沈婠的棋藝由容銘教導的也隻有沈家人,且老太爺還囑咐了不要外說。
夏氏自然是不會與外人說,能得容銘青睞,說出去也是為沈婠添了名聲,這樣的事夏氏才不會做。
沈婠聽到魏子騫提起容銘,笑道:“嗯,自是聽過的。你定是不知容先生除去醫外,棋藝也相當不錯。”
魏子騫一怔。
“容先生?”
沈婠道:“我的棋藝便是由容先生傳授的。”
魏子騫的眼睛一亮。
沈婠看得出魏子騫很想與容銘結,輕咳一聲,“過幾日我會去容先生那兒,若是你想結識容先生的話,可以同我一起過去。”
魏子騫喜不自勝,迭聲道:“好。”.
閑王府裏,覽古看著自家王爺,心都快揪起來了。
這幾日他守夜時常常聽見王爺在咳嗽,一咳就是好長時間。覽古聽得很是心疼,他苦說道:“王爺,你這樣咳下去也不是辦法,不若奴才去把容大夫喚過來吧。”
裴明澤道:“一到春日時節,我的子便會如此,不要。”
覽古道:“王爺,還是把容大夫喚過來妥當些吧,好歹也讓容大夫開個方子止止咳。不然夜裏這麽咳下去,王爺你也睡不,一樣影響王爺您的子呀。到時候沒有侍候好王爺,太後娘娘怪罪下來,奴才即便有九條命也無法擔當呀。”
Advertisement
他這隨從什麽都好,就是太嘮叨。不過這些年來,裴明澤也習慣了。他笑了笑,說道:“罷了,過兩日我剛好要出去,便順便去容銘那兒讓他看看吧。”
56
容銘一大早起來便覺得太作疼,他手一,了外邊泛白的天,接著對阿潭說道:“阿潭,不知道怎麽的,我總覺得今日會有些不好的事發生。”
阿潭笑道:“主子,是您多想了吧。”
容銘想了想,“興許是寧風又想過來找我討錢了。”上回他特地邀了寧風過來,請他喝了上好的碧螺春,用的便是一個將破的瓷杯。不料寧風的眼睛得很,還沒那瓷杯,便與他說,上回落下一茶杯。
容銘無可奈何,隻好說不小心弄壞了。
最後寧風敲了他好大一筆竹杠,以寧風的子,容銘估著他還會拿此事說上好幾回。容銘對阿潭道:“把門關,今日別放寧風進來。”
阿潭隻覺寧大夫像是一陣風,每次來總會刮走一些銀錢。
阿潭心有戚戚,連忙道:“明白!阿潭一定把門關得的,絕不讓寧大夫鑽進來!”
容銘吩咐完畢,心也放鬆了,他打了個哈欠,“行,我再睡一會。過多小半個時辰,你便去沈府接婠婠過來。”
阿潭應了聲“是”。
.
裴淵今日是獨自前來,連衛節也沒有帶。前幾日茗曦來爬床,定是祖母的授意,否則茗曦有一百個膽子也不敢這麽做。且如此一來,祖母的意思也十分明顯了。
祖母極是疼他,若是曉得他的心思,定會二話不說,為他娶來沈妙。
他裴淵要的人,必定是心甘願。
裴淵拍拍門,並沒有人出來回應。且不說此刻容銘正與周公下棋,便是當真聽到了他也隻當是幻覺,若是急診,也會破門而,總之別指他去應門。
Advertisement
裴淵也不死心。
他的人前一刻還來告訴他,容銘的小廝往沈府去了,想來是要去接沈妙過來。既是無人應門,那他等一等便是。約一炷香的時間,裴淵見著有輛馬車正往他這兒駛來,他心中一喜,站直了段。
未料笑容還未完全擺出來,他又見著一輛馬車駛來,車廂上明顯是威遠將軍府的標誌。
裴淵的眉頭蹙,但轉眼間又勾起角——
魏家小兒,甭想與我相爭,我若出手,你定死無葬之地。
裴淵站定。
沈婠今日是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會遇到裴淵,一下馬車,就見到裴淵揚起一抹古怪的笑容,看得骨悚然的。裴淵前來,微笑,“沈姑娘,真巧。”
沈婠心中一窒。
此時,魏子騫亦是下了馬車。他自是認得裴淵的,平南世子,京城中甚有人不知其名,之前不的宴會上,魏子騫也曾遙遙見過裴淵幾麵,周圍的人都在誇讚平南世子風采如何如何,他很難記不住。
正所謂英雄惜英雄,魏子騫未與裴淵結時,心裏一直想與他認識認識的。隻不過如今一照麵,裴淵眼底的敵意濃厚得讓魏子騫愕然。
魏子騫左想右想也不知自己哪兒得罪了裴淵,他拱手道:“沒想到竟能在這兒見到平南世子,在下魏子騫,早已久仰世子大名。”
裴淵皮笑不笑的,“哦,原來是威遠將軍府的二公子。瞧二公子的模樣,是來求診的吧。”
“多謝世子關懷,我並非來求診的。我早已聽聞容神醫聖名,恰好沈姑娘認識容神醫,便想來結識一番,沒想到竟能上世子。”魏子騫一板一眼地回道。
沈婠在心裏歎氣。
這魏子騫不是裴淵的對手呀,裴淵怪氣的擺明是暗有所指,偏偏魏子騫卻聽不出來,還一本正經地回他。不過呆頭呆腦的也是種福氣,想必裴淵此刻心惱火得很。
Advertisement
裴淵瞧了眼沈婠,沈婠默不作聲的。
裴淵又說道:“雖是春日,但如今時辰尚早外邊還是頗涼,我們進去吧。沈姑娘子單薄,莫要寒了才是。沈姑娘,請。”
沈婠點了點頭,先進了去。
魏子騫剛想跟著沈婠走,卻被裴淵擋在前。魏子騫一怔,裴淵冷颼颼地道:“魏二公子想要先進去麽?”
魏子騫退讓一步,“世子先請。”
待裴淵進去後,魏子騫了腦門,奇了怪了,他到底是哪兒得罪了平南世子。
.
容銘是萬萬沒有想到一醒來,屋裏頭就多了兩個人,裴淵他認得,另外一張生臉孔他就不認得了。沈婠笑瞇瞇地介紹道:“先生,他是威遠將軍府的二公子魏子騫,早已久聞先生大名,特來拜訪。”
容銘明白了,是沈婠帶過來的。
自己的學生總要給幾分薄麵的,容銘笑道:“原是魏二公子。阿潭,去沏壺好茶過來。”
沈婠道:“霜雪姐姐,你也去廚房裏幫幫忙吧。”
容銘今日注定是要勞碌的,沈婠剛來不久,就有急診上門,且聽起來還頗為嚴重,寧風也治不好。容銘隻好急急地拿了醫箱離去,離開前還囑咐沈婠幫忙招待客人。
於是乎,屋裏頭隻剩下沈婠還有裴淵以及魏子騫三人。
阿潭與霜雪在廚房裏做著糕點。
◆本◆作◆品◆由◆思◆兔◆網◆提◆供◆線◆上◆閱◆讀◆
沈婠對魏子騫道:“沒想到今日先生有急診。”
魏子騫連忙道:“沒事,等哪日神醫沒有急診時再過來就是。神醫的事要,想要與神醫結識,也不在這一天半天的。”
沈婠笑了笑,眼角的餘不經意瞥到裴淵,驀然發現裴淵的腰帶上還掛著前些年輸給他的香囊,沈婠眼神微微一深。
Advertisement
許是注意到沈婠的目,裴淵開口說道:“沈姑娘,記得上回你與我對弈,輸了我好些什,此香囊便是其一。沈姑娘的紅極好,囊中的香料亦是奇特,不過如今時日久了,香味也淡了。我一直記掛著要與你再來一局,好贏多一個香囊回去。”
沈婠淡淡地道:“世子過獎了,我所做的香囊不過爾爾,想來平南侯府裏通紅的人定然也不。”
“原來沈姑娘早已與世子相識。”魏子騫打從進來後便一直覺得裴淵不對勁,除了對自己有敵意之外,看沈婠的眼神也頗是怪異,甚至還有幾灼熱。本來魏子騫是不解的,可現下一聽,饒是魏子騫再懵他也明白了。
裴淵此刻麵上正赫然寫著敵二字。
魏子騫眼神頓變,他拳掌的,隻道:“在下曾聽聞世子的武學師父是當年赫赫有名的曾泉,早已想與世子切磋一二,不知世子是否賞臉。”
裴淵道:“威遠將軍之子定然也是武藝高超,二公子請。”
.
沈婠在屋外的小庭院裏看著兩人施展拳腳,一時間有些反應不過來。剛剛好端端的,這下就打起來。說是切磋武藝,可怎麽瞧一招一式都似帶了殺氣一般。
霜雪端著糕點出來時,見到此般場景,嚇了一大跳。
“大……大姑娘,二公子和世子爺怎麽打起來了,要……要是鬧出人命來了……”
沈婠聽到“人命”二字,目立馬掃向裴淵,心想著若是魏子騫一不小心打傷了裴淵,也算是暫時替狠狠地出了口氣。
不過想歸想,要是裴淵在這兒出事了,容銘也難以得了幹係。
沈婠收起心裏的失,隻道:“霜雪姐姐大可放心,他們都是有分寸的人,僅僅是切磋武藝而已。”
阿潭捧著托盤出來。
恰好此時魏子騫的拳頭直勾勾地揮向裴淵,裴淵側一躲,往前一躍,正要來一招無影時,將阿潭嚇得手重重一抖,托盤上的茶壺和幾個杯子掉落下來,碎了一地。
阿潭慘一聲。
魏子騫側目一,就在魏子騫分神的這一刻,勝負已定。
魏子騫老老實實地挨了一記無影,整個人跪倒在地。
“二公子!”
沈婠驚呼一聲。
魏子騫連忙對沈婠擺手,“我沒事。”他忍著痛意,站起來對裴淵一拱手,“世子果真武藝超群,子騫教了。”
裴淵心中得意,他笑了笑,隻道:“承讓了。”
魏子騫的臉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814 章
醫妃逆天:腹黑鬼王猛纏妻
她,21世紀的天才鬼醫,一刀在手,天下任她走。一朝穿越,成了宰相府人人可欺的廢材大小姐。 他,鐵血無情的戰神王爺,亦是行走在生死邊緣的黑暗之王,卻因功高震主而被害成殘廢。 一場算計之下,她被賜給雙腿殘廢的王爺,成了整個北齊茶餘飯後的笑料。 初見,她一臉嫌棄:“玄王爺,我爹說你不舉,莫非你軟到連椅子也舉不起來?” 再見,他欺上她的身:“女人,感受到硬度了?” 感受到身下某物的變化,慕容千千嬌軀一顫:“王爺,你咋不上天呢?” 夜景玄麵色一寒:“女人,本王這就讓你爽上天!”
171萬字8 51238 -
完結1833 章

惡後歸來:陛下,娘娘又動手啦!(半支菸頭)
“陛下,娘娘已關在後宮三天了!”“悔過了嗎?”“她把後宮燒完了……”穆王府嫡女重生。一個想法:複仇。一個目標:當今四皇子。傳言四皇子腰間玉佩號令雄獅,價值黃金萬萬兩。穆岑一眼,四皇子便給了。傳言四皇子留戀花叢,夜夜笙歌,奢靡無度。穆岑一言,四皇子後宮再無其他女子。於是越國傳聞,穆岑是蘇妲己轉世,禍害江山社稷。穆岑無畏,見佛殺佛,見神殺神,利刃浸染仇人鮮血,手中繡花針翻轉江山社稷,光複天下第一繡房。眾臣聯名要賜穆岑死罪。四皇子卻大筆一揮,十裡紅妝,後座相賜。後來,世人皆知。他們的後,隻負責虐渣,他們的王,隻負責虐狗。
320.6萬字8 34351 -
完結600 章

娶妃后,我有了讀心術
【異能】大雍十三年六月,雍帝選秀,從四品御史之女顧婉寧,使計想要躲過選秀,原以為計謀得逞能歸家時,其父因扶了當今圣上一把,被賜入六皇子府為繼皇子妃。夫妻二人大婚之后相敬如冰,直到六皇子中了藥被奴才送回正妃院中。隔日,六皇子竟是能聽到別人的心…
110.2萬字8 15504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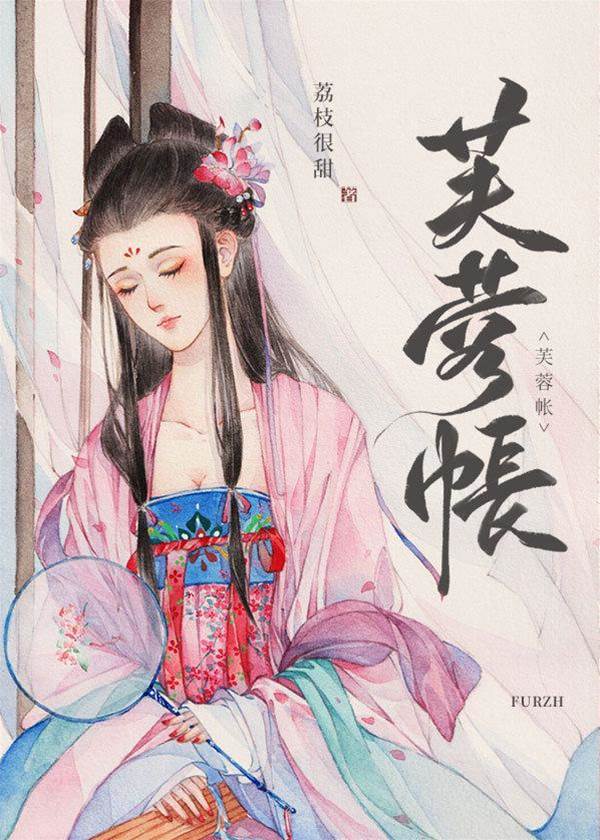
芙蓉妝
文案:錦州商戶沈家有一女,長得國色天香,如出水芙蓉。偏偏命不好,被賣進了京都花地——花想樓。石媽媽調了個把月,沈時葶不依,最后被下了藥酒,送入房中。房里的人乃國公府庶子,惡名昭彰。她跌跌撞撞推門而出,求了不該求的人。只見陸九霄垂眸,唇角漾起一抹笑,蹲下身子,輕輕捏住姑娘的下巴。“想跟他,還是跟我?”后來外頭都傳,永定侯世子風流京都,最后還不是栽了。陸九霄不以為意,撿起床下的藕粉色褻衣,似笑非笑地倚在芙蓉帳內。嘖。何止是栽,他能死在她身上。-陸九霄的狐朋狗友都知道,這位浪上天的世子爺有三個“不”...
37.3萬字8 29264 -
完結191 章

新婚夜,瘋批太子奪我入宮
【強取豪奪+追妻火葬場+瘋狗男主】十六歲前,姜容音是嫡公主,受萬人敬仰,貴不可攀。十六歲后,姜容音是姜昀的掌中嬌雀,逃脫不了。世人稱贊太子殿下清風霽月,君子如珩
34.6萬字8 3881 -
完結121 章

假千金和真少爺在一起了
薛瑛在一次風寒後,意外夢到前世。 生母是侯府僕人,當年鬼迷心竅,夥同產婆換了大夫人的孩子,薛瑛這才成了侯府的大小姐,受盡寵愛,性子也養得嬌縱刁蠻。 可後來,那個被換走的真少爺拿着信物與老僕的遺書上京認親,一家人終於相認,薛瑛怕自己會被拋棄,作得一手好死,各種爭寵陷害的手段都做了出來,最後,父母對她失望,兄長不肯再認她這個妹妹,一向疼愛她的祖母說:到底不是薛家的血脈,真是半分風骨也無。 薛瑛從雲端跌落泥沼,最後落了個悽慘死去的下場。 一朝夢醒,薛瑛驚出一身冷汗,爲避免重蹈覆轍,薛瑛乾脆一不做二不休,重金僱殺手取對方性命。 缺德是缺德了一點,但人總得爲自己謀劃。 誰知次次被那人躲過,他還是進了京,成了父親看重的學生,被帶進侯府做客。 薛瑛處處防範,日夜警惕,怕自己假千金的身份暴露,終於尋到一個良機,欲在無人之際,將那人推下河,怎知自己先腳底一滑,噗通掉入水中,再醒來時,自己衣衫盡溼,被那人抱在懷中,趕來救人的爹孃,下人全都看到他們渾身溼透抱在一起了! 父親紅着老臉,當日便定下二人婚事。 天殺的! 被迫成婚後的薛瑛:好想當寡婦啊。
31.3萬字8 11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