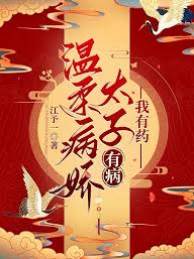《她的信息素有毒》 第30章 32 發燒
這一覺睡得並不安穩。
準確來說,開始時樂殷南睡很迅速,但很快做了個夢。
夢裏在茶山梯田向下眺,雲淡風輕,但很快,腳底的茶樹開始瘋長,藤蔓般將纏繞,被尖銳的倒刺與濃鬱的茶香裹挾,猛拽,纏住氣管,無法呼吸。
樂殷南在滾燙的窒息中驚醒。
隨即意識到,自己的確被一片茶香包圍。
茶是滾燙的。
嚴笑不知道什麽時候了小小一團滾進了樂殷南懷裏,攥著的袖,眉頭皺。
樂殷南探了探嚴笑的額頭。
那熱氣無孔不,順著的皮喧囂塵上。
驚心魄的燙。
“嚴笑,醒醒。”樂殷南試圖將推醒,“你發燒了。”
嚴笑著樂殷南袖袖口,整張臉都皺在一起,眉眼著不安。
樂殷南推了好幾次都不奏效。
了頸後已經有反應的腺,覺得自己再待下去恐怕要失控。
長歎了口氣,想把嚴笑的手從服上拽下來,找阿萱或者伊麗莎白來理這件事。
但低估了嚴笑的手勁。
輕輕一推本推不開。
而且這一推一合的空檔,那熱氣已經順著袖口攀爬而上。
樂殷南覺得自己呼吸也跟著不對勁了起來。
“嚴笑,鬆手,我得給你去找醫生。”樂殷南決絕有力地一拔開嚴笑拽住的手指,生怕再次合攏,連忙將自己從嚴笑手中出來。
靠得很近。
舉止過於親。
們幾乎十指相扣,從嚴笑邊離開時,樂殷南長發發梢甚至劃過嚴笑大半臉頰,近乎上的。
一個細微的作。
樂殷南就已經出了一汗。
很難說是驚到的還是熱出的。
“誰?”
就在樂殷南礙手礙腳從床上下來時,的胳膊突然被嚴笑猛地攥住。
Advertisement
樂殷南懊惱地閉上眼睛。
就在想該如何解釋時,後又傳來紊的呼吸。
嚴笑隻是條件反地防備了一下,並未清醒。
樂殷南悄悄鬆了一口氣。
不願再做出更加親的舉。
思來想去,樂殷南還是湊近嚴笑,悄悄釋放出一點點信息素。
咖啡的苦味澆濃鬱的茶香,有種黑褐中草藥的味道。
alpha的信息素能夠很快地緩解omega的不安,恐慌。
嚴笑在樂殷南的包圍下很快舒展了皺的眉頭。
拉的力氣也鬆了一些。
——但也極其容易引ao失控發。
所以樂殷南趁嚴笑鬆手的瞬間就把自己關在門外,閉大門,頸後腺已經徹底蘇醒,呼吸中都帶著灼氣。
在鎖骨掐出一片紅痕,平複了許久,才重新睜開眼睛。
樂殷南急找到了阿萱,阿萱立即了伊麗莎白過來。
“沒事,隻是早上喝了墮胎藥,緒波有些大,再加上一天沒怎麽吃東西,春夏之就是這樣的,天氣忽冷忽熱,所以才著涼了。”
伊麗莎白檢查完又開了一些藥,看向樂殷南。
“不過現在燒已經退了一些,剛流完產,十分虛弱。”
伊麗莎白講“十分”咬得特別重。
“我留下來照顧小姐。”阿萱連忙說。
伊麗莎白提議:“其實如果有匹配的alpha,alpha待在邊能讓病人恢複得更快。”
“這什麽道理!”樂殷南懷疑嘀咕了一句。
“氣味會影響心,心有助於恢複。”伊麗莎白懶得和樂殷南廢話專業語,強調,“不過你不願意也沒關係,就是病人會恢複得慢一點。”
樂殷南沉聲道:“我守到天明,盡量等醒來。”
“很好。”伊麗莎白合上醫藥箱,將藥遞到樂殷南手上,“醒來記得讓按時吃藥。”
Advertisement
“對了,友提醒,生病期間止任何標記行為,這樣隻會幹擾恢複。”伊麗莎白聞到空氣中殘留的咖啡香,微妙一頓,“我是指‘任何’可能發生標記的行為,明白嗎?”
樂殷南垂下眼眸:“不會的。”
“那隻是為了讓放鬆警惕鬆開手。”
“最好這樣。”伊麗莎白微微頷首。
說完,便起準備打道回府。
“你為什麽要給我送那封信?”樂殷南見伊麗莎白就要離開,忍不住開口詢問。
伊麗莎白腳步一頓。
“我原想讓你勸勸,無論如何,那畢竟是條生命。”
但沒想到嚴笑態度如此堅決,手速度竟然那麽快。
“讓你千裏迢迢趕來一趟,實在抱歉。”伊麗莎白說完便離開了。
樂殷南和阿萱麵麵相覷。
縱使阿萱滿臉寫著懷疑,但在樂殷南的視下還是妥協了。
伊麗莎白說得不無道理。
匹配度高的alpha哪怕什麽都不做,是站在這裏,就足以讓omega到安心。
雖然的腺被切了,現在同beta幾無二致,但多多還是能知到一點點alpha的信息素,等級越高越明顯。
無論如何,都不宜在這久留。
“那就勞煩樂小將軍了。”阿萱微微扶行禮,“有任何需求請務必我,我就在隔間候著。”
樂殷南略略點頭,目送阿萱離開。
嚴笑仍在沉睡。
伊麗莎白開了些藥,的麵稍微好轉了一些,但仍然虛弱,蒼白到近乎明。
樂殷南覺得自己的心也跟著糾結。
又想起之前差點口而出的那句“我喜歡你”。
說實話,這四個字自己都覺得很意外。
按理說不應該對嚴笑如此上心,們隻是合作關係,哪怕合作的容從“三年尋”擴展到“火接”乃至“度過發期”,也僅僅隻是合作關係。
Advertisement
樂殷南都說不準從什麽時候嚴笑本人開始大篇幅地占據注意力。
乃至聽到嚴笑說懷孕時,樂殷南第一個反應竟然是生下來之後該怎麽辦?
避孕的說辭曆曆在目,可真的有了個孩子,樂殷南竟然荒唐地本沒考慮“墮胎”的可能。
甚至有些害怕知道自己真實的想法。
究竟是一開始的虛偽。
還是潛移默化的轉變。
樂殷南找不到答案。
也畏懼找到答案。
如果牽扯的人過多,關心的人過多,如果更在意的是嚴笑而非樂行檢——
樂殷南不確定自己是否就敢這樣毀掉過去十幾年來的努力。
於是又回到嚴笑之前問的問題。
——現在已經為了什麽?
“我該拿你怎麽辦?”
樂殷南坐在嚴笑床頭,著的睡眼,喃喃自語。
一夜無夢。
次日清晨嚴笑醒來的時候,房間裏已經沒有人。
睜開眼,險些被亮白的線刺得不過氣,仿佛墜烈日下的海麵,頭頂白得發驚呼明的波浪深淵。
房間裏沒有人,空氣裏還殘留著一若有若無的咖啡苦香。
很安靜。
嚴笑勉強起,發現桌麵上擺著水,還留了碗青菜瘦粥,粥是溫的,碗底押著一封信,沒有信封,遒勁有力的字跡暴在視線裏。
是樂殷南留下的。
上麵仔細寫著伊麗莎白的藥囑,並聲稱自己臨時有事得回家一趟,離開前釋放了一些信息素助眠安神。
但空氣裏濃鬱的信息素暴了離開不久的事實。
嚴笑很快就能猜到樂殷南是不知道怎麽麵對所以才在醒來之後悄然離開。
垂下眼。
也好。
昨晚發生的事太多了,們都需要時間冷靜想想。
嚴笑打定主意,喝了水,舀了勺粥放在裏,表微妙。
Advertisement
這不是檀香閣後廚的手藝。
樂殷南這家夥還會做飯?
這個念頭剛在嚴笑腦閃過,便釋然了。
也是,樂殷南一個軍人,在外麵風餐宿的多都會接一點,更何況之前還是奴隸出,會點這些小伎倆並不在話下。
但總歸還是意外的。
嚴笑忍不住又舀了一勺。
‘還好吃的。’想。
……
嚴笑在床上躺了一天燒就退了。
能走路後,就馬不停蹄地帶上曾山與阿萱前往樂殷南提供的奴隸點,挨個排查。
“雖然你燒降了,但你還很虛弱,我不太建議你這麽快就投工作中。”伊麗莎白不滿皺眉。
嚴笑聽了隻是隨意笑道:“時不我待。”
“你為什麽這麽著急?”伊麗莎白不解。
嚴笑邊回答邊確認下一個地點:“朝廷要有新作了,很快,舉國上下便會步水火。”
說到這裏,抬頭深深看了伊麗莎白一眼,提醒道:“我個人建議你最近不要出江北商行,商行來往外邦人眾多,所以治安相較而言更加複雜,即便是朝廷也不太好手,目前還能偏安一隅,但其他的地方,恐怕有些人不會因為你拿著西秦的通關文牒就對你高看一眼。”
嚴笑一頓:“畢竟你還是個omgea。”
伊麗莎白若有所思。
世上沒有不風的牆。
朝廷要懲辦omgea的消息不脛而走。
這幾天大街小巷的確彌漫著一山雨來的危機。
甚至昨天在梁記粥鋪附近就出現了一起omgea奴隸逃跑事件。
雖然那奴隸最後還是被府抓了回來,當街死以儆效尤,但愈來愈多的主人都到自己的財產蠢蠢。
無數奴隸omega在路上肩而過,都閉口不言,道路以目。
……
因為老金一直活躍在江北這帶,而能夠買得起奴隸的達顯貴大多在共治界都有資產,所以嚴笑排查起來十分迅速。
循著賬簿挨個找了過去,又通過許多奴隸口口相傳的線索更新了最新方向,在排查到第十六人時,得到了線索。
“我知道你們上都是數字刺青,但有沒有一個人背後刺著彎鉤的模樣?”
嚴笑在宣紙上畫出記憶中的模樣,一個個地追問。
“彎鉤,或者倒刺,大概類似於這類尖銳的刺青?”
“這我真沒見過。你確定是過去金皮手下的人?”
那omega拿了嚴笑的銀元,知無不言,十分熱。
“確定。有人告訴過我,當年在花樓街活躍的隻有他。”
“那奇了怪了……不過,有沒有可能你看錯了?”omega小心建議道,“或者你要找的是長得像鉤子的數字?你還記得你要找的人當年的代號嗎?”
“我和倒是沒說過話。”嚴笑搖頭,話鋒一轉,“那你記得十七現在在哪兒嗎?我和他也有故。”
omega聽到“十七”兩個字,表一愣。
還沒開口,卻聽有腳步聲悄聲走來。
“誰?!”
嚴笑自然也捕捉到了靜。
那腳步一頓,接著傳來三聲布穀鳥的聲響。
omega連忙也取出哨管,回了一串鳥鳴。
那人放心地繼續靠近。
“那是誰?”嚴笑驚訝omega的不設防。
omega小聲在耳邊反笑:“你不是要見十七麽?”
來人是個男omega。
他穿著賬房先生的長袍,懷裏夾著算盤,架著一副金邊眼鏡步伐匆匆。
“他就是。”
嚴笑將信息素藏得很好。
十七沒想到他與同伴約定的見麵地點還有旁人。
看到嚴笑,他麵震驚。
“十七。”嚴笑站在原地回頭,“好久不見。”
作者有話要說: 樂樂:竟然背著我去見了別的omega?!
——————
謝遲遲扔了1個地雷投擲時間:2021-08-1121:22:59
讀者“林鹿”,灌溉營養22021-08-1215:25:23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482 章

皇後天天想和離
他是手握重兵,權傾天下,令無數女兒家朝思暮想的大晏攝政王容翎。她是生性涼薄,睚眥必報的21世紀天才醫生鳳卿,當她和他相遇一一一“憑你也配嫁給本王,痴心枉想。”“沒事離得本王遠點,”後來,他成了新帝一一“卿卿,從此後,你就是我的皇后了。”“不敢痴心枉想。”“卿卿,我們生個太子吧。”“陛下不是說讓我離你遠點嗎?”“卿卿,我帶你出宮玩,”
139.7萬字8.33 514932 -
完結250 章

愛卿,龍榻爬不得
魏無晏是皇城裏最默默無聞的九皇子,懷揣祕密如履薄冰活了十七載,一心盼着早日出宮開府,不料一朝敵寇來襲,大魏皇帝命喪敵寇馬下,而她稀裏糊塗被百官推上皇位。 魏無晏:就...挺突然的。 後來,鎮北王陶臨淵勤王救駕,順理成章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攝政王。 朝中百官紛紛感嘆:奸臣把持朝政,傀儡小皇帝命不久矣! 魏無晏:好巧,朕也是這麼想的。 慶宮宴上,蜀中王獻上的舞姬欲要行刺小皇帝,攝政王眸色冰冷,拔劍出鞘,斬絕色美人於劍下。 百官:朝中局勢不穩,攝政王還要留小皇帝一命穩定朝局。 狩獵場上,野獸突襲,眼見小皇帝即將命喪獸口,攝政王展臂拉弓,一箭擊殺野獸。 百官:前線戰事不明,攝政王還要留小皇帝一命穩定軍心。 瓊林宴上,小皇帝失足落水,攝政王毫不遲疑躍入宮湖,撈起奄奄一息的小皇帝,在衆人的注視下俯身以口渡氣。 百官:誰來解釋一下? 是夜,攝政王擁着軟弱無骨的小皇帝,修長手指滑過女子白皙玉頸,伶仃鎖骨,聲音暗啞:“陛下今日一直盯着新科狀元不眨眼,可是微臣近日服侍不周?” 魏無晏:“.....” 女主小皇帝:本以爲攝政王覬覦她的龍位,沒想到佞臣無恥,居然要爬上她的龍榻! 男主攝政王:起初,不過是憐憫小皇帝身世可憐,將“他”當作一隻金絲雀養着逗趣兒,可從未踏出方寸之籠的鳥兒竟然一聲不吭飛走了。 那便親手將“他”抓回來。 嗯...只是他養的金絲雀怎麼變成了...雌的?
40.5萬字8.18 12559 -
完結23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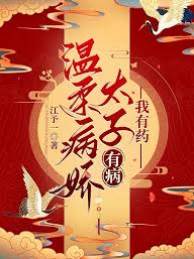
溫柔病嬌太子有病,我有藥
【古言甜寵 究極戀愛腦深情男主 雙潔初戀 歡快甜文 圓滿結局】 謝昶宸,大乾朝皇太子殿下,郎豔獨絕,十五歲在千乘戰役名揚天下,奈何他病體虛弱,動輒咳血,國師曾斷言活不過25歲。 “兒控”的帝後遍尋京中名醫,太子還是日益病重。 無人知曉,這清心寡欲的太子殿下夜夜都會夢到一名女子,直到瀕死之際,夢中倩影竟化作真實,更成了救命恩人。 帝後看著日益好起來,卻三句不離“阿寧”的兒子,無奈抹淚。 兒大不中留啊。 …… 作為大名鼎鼎的雲神醫,陸遇寧是個倒黴鬼,睡覺會塌床,走路常遇馬蜂窩砸頭。 這一切在她替師還恩救太子時有了轉機…… 她陡然發現,隻要靠近太子,她的黴運就會緩緩消弭。 “有此等好事?不信,試試看!” 這一試就栽了個大跟頭,陸遇寧掰著手指頭細數三悔。 一不該心疼男人。 二不該貪圖男色。 三不該招惹上未經情愛的病嬌戀愛腦太子。 她本來好好治著病,卻稀裏糊塗被某病嬌騙到了手。 大婚後,整天都沒能從床上爬起來的陸遇寧發現,某人表麵是個病弱的美男子,內裏卻是一頭披著羊皮的色中餓狼。 陸遇寧靠在謝昶宸的寬闊胸膛上,嘴角不禁流下了悔恨的淚水。 真是追悔莫及啊~
42.5萬字8.18 7922 -
完結212 章

將軍她又美又颯,權臣甘拜裙下
【女扮男裝將軍vs偏執權臣】人人都說將軍府那義子葛凝玉是上趕著給將軍府擦屁股的狗,殊不知她是葛家女扮男裝的嫡小姐。 一朝被皇上詔回京,等待她是父親身亡與偌大的鴻門宴。 朝堂上風波詭異,暗度陳倉,稍有不慎,便會命喪黃泉。 她謹慎再謹慎,可還是架不住有個身份低微的男人在她一旁拱火。 她快恨死那個喜歡打小報告的溫景淵,他總喜歡擺弄那些木頭小人兒,還次次都給她使絆子。 起初,溫景淵一邊操著刻刀一邊看著被五花大綁在刑架上的葛凝玉,“將軍生的這樣好,真是做人偶的好面料。” 后來,溫景淵將她圈在懷里,撥弄著她的唇,“姐姐,先前說的都不作數,姐姐若是喜歡,我來做你的人偶可好?” 葛凝玉最后才知道,昔日心狠手辣的笑面虎為了自己賭了兩次,一次賭了情,一次賭了命。 排雷:1、女主穿越人士,但沒有過多的金手指,情感線靠后 2、作者起名廢 3、架空西漢,請勿考究
39.9萬字8 6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