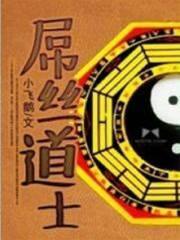《嫁龍作夫》 第94章 我們順路
他完全不給我們兩個拒絕的機會領著我們去了他停在路邊的車前。
打開門,我們坐了進去。
劉悅姑姑家在城南,跟道士家并不順路。
靈囿走到一半,忽然停下來,轉頭沖劉悅說道:“你在這里打車吧,我車沒多油了。”
我坐在副駕駛上,瞥了一眼儀表盤上滿格的油表,暗道這人真是無恥至極。
剛剛還說怕我們兩個小姑娘跑出事,這會兒又開始睜著眼說瞎話,把劉悅支下去。
劉悅愣了一下。
但也沒說什麼,怯怯的說了一句,“謝謝顧老師。顧老師再見。”
立刻打開車門下去了。
看下車,我也順手打開副駕的車門,打算一起下去。
結果我扳了半天的門把手,車門就是打不開,不僅如此,靈囿還重新把車啟了。
我不解的看向他,他目視前方,淡淡說道:“我們順路。”
“……”
順路個屁呀!
道士的別墅,比劉悅姑姑家要偏的多,他這麼扯,誰信啊?
心里吐槽歸吐槽,我也沒吭聲。
靜靜的靠在車窗邊,看向外面快速閃過的寂靜夜晚。
不知不覺間,車緩緩停了下來。
到地方了。
“謝謝顧老師,到這兒就行了,我自己進去。”
我沖他笑了笑,手就去開車門,卻聽見一聲清脆的落鎖。
接著聽見他不疾不徐的說道:“不安全,讓你家里人出來接你,我總要把你送到你家長手里。”
我家里人現在在哪兒你不知道?!
你怎麼不直接給我送回龍門村去啊?
繼續裝吧你就!
“這兒是我親戚家,他可能都已經睡了,我不太好意思打擾他……”我出一抹笑。
“那今天晚上你先去我那里吧,我明天再送你回來。”
Advertisement
我:“???”
眼看他手就要去擰鑰匙,我慌忙去抓他的手,到他指尖的溫度,我趕把手收了回來。
他側頭看向我,那雙琥珀的眸眼似笑不笑,里面分明藏著戲謔。
我又氣又惱。
立刻掏出新買的手機,撥通了道士的電話。
一接通,我就聽見道士扯著嗓子喊了聲,“繼續喝!”
車里特別安靜,道士這一嗓子喊出來我尷尬的要命。
電話那邊有點吵,似乎還有別人在說話,道士“喂”了一聲,“怎麼了白邪?有事兒趕說!我忙著幫人家捉鬼呢!”
剛說完,又聽見他不知道跟誰說了一句,“我再喝一瓶你就再一件服好不好?小姑娘你上這鬼氣太重,不貧道看不清啊……”
那聲音,簡直猥瑣的不能再猥瑣。
“我在大門口,你出來接我一下吧!”
迅速說完,我趕掛了電話,生怕他再給我說什麼語出驚人的話。
靈囿倒是沒說什麼,我瞄了一眼他,他一只手隨意的搭在方向盤上,整個人懶洋洋的半倚在座位上。
那只手指如蔥白,骨與骨之間勾勒分明,指尖也修剪的干凈整潔,仿佛一個藝品。
我的目緩緩往上移,他那條下顎線立骨,很薄,角微微翹起一抹弧度,鼻梁高,架著一副致的金眼鏡
他的睫很長,微微垂著,半遮半掩那雙獨特的琥珀眼睛——
這擱誰誰不迷糊?
也怪不得白天那個李老師要死要活的纏著他。
正忽然,那雙眼睛了,不不慢的往我這邊看,“好看嗎?”
問看自己男人被抓包是什麼覺?
當然是理直氣壯啊!
“好看。”我認真的點點頭。
Advertisement
靈囿什麼也沒說,只是又把頭轉過去,但我注意到他角笑意漸濃。
大概又過了幾分,還是不見道士的影子,我暗罵他不靠譜,打算再給他打個電話。
旁邊靈囿突然開口,抬手指了指,“那個是不是你親戚?”
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過去,正見道士上歪七歪八的穿著背心短黃道袍,醉醺醺的摟著兩個穿著暴的小姐,罵罵咧咧的往外走。
從他的型上,我能猜出來他大概是在背后嘟囔我。
靈囿看我一眼,挑著眉,“這就是你親戚?”
我咬牙切齒,“是!”
明知故問!
這狗男人還演上癮了?!
要不是我想看看你到底要演到什麼時候,我一定了你的皮!
我跟靈囿都下了車。
我沖著道士喊了一聲,“老頭兒!”
道士怔了一下,歪歪扭扭的往我這邊走,手上時刻不離兩個小姐的腰。
他走到我跟前停住了,瞇著眼使勁兒打量靈囿的車,里喃喃,“豪車啊……”
我正要開頭,他突然眼睛一亮,走上前來使勁兒拍了拍我的肩膀。
語重心長的對我說道:“白邪你總算是開竅了!你終于知道勾搭有錢人養我了啊!”
“……”
我能覺我的眼角在搐。
勉強出一抹笑,看向靈囿,“不好意思顧老師,我親戚他喝醉了,麻煩您了,您先回去吧。”
“好。”
靈囿淡淡應了一聲,轉回去。
等到他離開,我立刻攆走了那兩個小姐,對著道士就是一通拳打腳踢
“白邪!白邪!你個小沒良心的!打人不打臉!”
道士酒瞬間就醒了,從地上站起來,連滾帶爬的往回跑,我還是在他屁上踹了一腳。
回到家里,他翻出碘酒和鏡子,對著臉用棉簽涂抹傷口,一下傷口他就倒吸一口涼氣。
Advertisement
他埋怨我,“你還真手啊?”
我坐在沙發上,吃起桌子上的果盤,瞥了他一眼,“不然你酒能醒?你業務還真夠廣泛的,那是來家里找你抓鬼的?一來來兩個?”
道士被我堵的沒話說,癟癟,小聲嘟囔,“你還是沒開竅的時候可。”
說著,他又問我,“你不是在學校嗎?怎麼突然回來了?”
“學校出事了,死了六個人。”
我咬了一口蘋果,“人工湖里面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了一大坨黑氣,人就是被那東西給弄死的。”
我看向道士,一字一句的說道:“死狀跟張玉一模一樣。”
“剛才我又去了一趟,跟那東西了手,它不怕符箓,有好幾雙手臂,沒有臉,只有一張……”
我向道士詢問,“會不會是魃?可是湖里的水并沒有干,它還一直藏在湖里。”
道士沉默了一下,隨即站起來從他那一堆破爛里翻出一本書,找到其中一頁仔細看了看,然后把書遞給我。
他認真說道:“你說那東西,可能是‘水魃’。”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