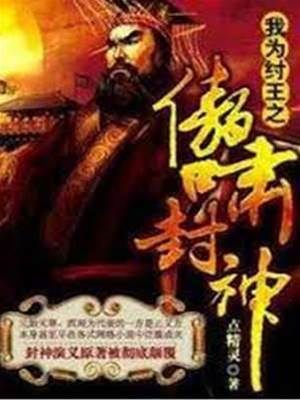《我不做妾》 第63章 第63章
裴慎每日里早出晚歸,沈瀾又吃了藥,日里昏昏沉。就這麼過了幾日,裴慎突然收拾行李。
“要走了?”沈瀾懨懨地飲了盞水,“沒什麼好收拾的。若缺什麼,屆時去山西添置便是。”
裴慎笑道:“不去山西了。”
見沈瀾頗為驚詫地過來,裴慎低聲解釋道:“我原是山西巡,如今被平調為浙江巡,改道去杭州赴任。”
沈瀾微怔,半晌,抬起頭道:“可是因為南京城倭寇一事?”
裴慎挑眉,頗為驚詫反應靈敏。復又點頭道:"不錯。"
共計五十三個倭寇,從浙江高埠登陸,一路過杭州、淳安、歙縣、江寧,打到南京城下,其中僅江寧鎮死傷士卒就有三百余人, 秣陵關守軍干余人甚至棄城而逃, 國朝面俱喪。
若不是他將這些倭寇于龍江驛擒獲,任由其流竄下去,只怕丟臉更甚。
因此一事,浙江巡鄧豪、南京兵部尚書范意之被罷,其余林林總總被罷免的吏另有數十人。
裴慎也因為擒拿倭寇有功,轉為浙江巡,清繳倭寇。
“什麼時候走?”沈瀾問道。
裴慎溫聲道:“明日便走,從龍江驛坐船,先至姑蘇驛,再轉松陵、平、嘉興驛到武林驛。”
沈瀾應了一聲,又問道:“平山和潭英如何了?”
“已能起了。”裴慎笑道:“你且安心。”
無事便好。沈瀾心里稍稍好些,便抬頭道:“我先去收拾。”雖無需帶什麼大件,但日常換洗的總還是要帶幾件的。
第二日一大早,辭別了裴府眾人,裴慎帶著沈瀾,只坐船往杭州而去。
船上的日子頗為無趣,目唯有茫河面、瑟瑟江風、兩岸蘆葦罷了。
Advertisement
已至十月,天氣越發寒冷,有些淺窄的河道已結冰,兩岸纖夫著單,晝夜不停地破冰,糲的麻繩磨破肩膀,紅腫青紫。
沈瀾見了,頗為不忍,卻又無能為力,只是越發沉默下去。
子骨不好,裴慎不出船艙風,也樂得見不出去,只窩在艙中烤火。
十月中旬,裴慎和沈瀾終至杭州武林驛。一下船,裴慎只將沈瀾安置在巡衙門后院,便徑自出了門,去會見同僚下屬。
沈瀾實在沒什麼要添置的,也沒興趣擺弄這些。興致不高,只清掃了一番后院便住了。
誰知方才將行禮規整好,便有丫鬟來報,只說杭州知府的夫人前來拜訪。
許是長時間吃藥的緣故,又或者是見多了生民疾苦卻無能為力,沈瀾近來格外疲憊。
那是一種神上的倦怠,像是溺水的人,手腳掙扎得太久了,難免乏力。再后來,疲憊到呼救聲也越來越小,直到被淹沒。
“不見。”沈瀾搖搖頭:“若有事,相公去尋裴慎。”語罷,沈瀾解了便要去歇息。
幾個丫鬟都是陳松墨新采買的。裴慎赴任浙江,陳松墨和林秉忠自然也從京都、山西趕來。
見沈瀾說不見,幾個丫鬟也不敢違逆,一人出去拒了,另幾人便忙著鋪床疊被,泡茶燃香。
沈瀾剛服過一劑藥,又昏昏沉沉睡去。
冰梅紋窗格嵌著琉璃,清干凈,此刻略開了半扇,出庭前廊下三兩梧桐,窗前櫸木束腰靈芝紋禪香案上擺了個首博山爐,正隔水蒸熏四棄香,淡淡的香氣逸散在空氣里。
沈瀾睡了一會兒,醒來,拂開雪景寒林紙帳,方見裴慎坐在黃花梨束腰璃紋榻上,正端著一盞建州茶,悠閑啜飲。
Advertisement
沈瀾奇道:“這才酉時你便回來了?不需接一二,再見見你的下屬嗎?”
裴慎只起,將從帳中抱出來,室已燃起了火盆,熱烘烘的。
“已是十月中旬,冬了,河面上行船漸漸困難起來,便是倭寇這段日子都滋事了。”裴慎只拿薄被蓋了,將摟在懷里,又笑問道:"白日里杭州知府的夫人來見你,怎麼不見?"
沈瀾雖睡了一覺,可心思深重,人照舊懨妖的,聞言只搖頭道:"若有事,必定會來尋我第二次。若無事,見了也沒必要。”
見像只小貓似的,馴服地窩在自己懷里,裴慎心里熱烘烘的,便低頭笑道:“你近日來神頭不好,我特意叮囑了杭州知府,只他夫人來與你說說話。沒料到你竟不愿見。”
聞言,沈瀾怔忡片刻,瞥他一眼道:“人家好端端一個正室,恐怕是不想來拜會我這個做妾的,你偏要來做甚。”
裴慎被說得發怔,笑道:“你這傻子,宰相門前七品言,你是我的人,來拜見你本就是應當的,若能哄你開心,在自家夫君面前,都能多得幾分臉面。"
沈瀾明白這是所謂的夫人外,可被一幫人吹捧諂,再說些虛頭腦的廢話,能有甚趣味呢?
“好沒意思。”沈瀾搖頭道:“還不如放我出去閑逛一二。”
裴慎瞥一眼,見眉眼似皎皎霜雪,素冷凈白,沒幾分。想來是在裴府剛養出的那點氣,都被舟車勞頓消耗干凈了。
“這會兒出去做甚?”裴慎攏了攏薄被,將裹得嚴實些,“你子原本就不好,且好生吃藥養著,待過了這個冬季,你子稍好些,我便帶你出去作耍。”
Advertisement
沈瀾心里失,若不出去,哪里尋得到機會。
“你這般忙碌,何時才有功夫帶我出去玩?”語罷,沈瀾只小心試探道:“倒不如我自己領幾個人出去閑逛一二?"
裴慎哪里肯放離開自己視線,又聽再三提起自己出去閑逛,便已是心中不愉,只語帶警告道:“外頭鬧倭寇呢,莫要跑。”
沈瀾心道你方才還說冬季連倭寇都不出來打仗,如今又拿倭寇說事,兩相矛盾。
只是出不去,便懶得與裴慎爭辯,只開口道:“你何時方有空?”
裴慎想了想:“過年罷,臘月二十四府便封印了,屆時總有閑暇的。”
距離過年還有一個多月呢。沈瀾想了想,便點頭道:"只希你莫要騙我。"
裴慎便朗笑道:“我騙你做甚?”語罷,又低聲道:“說來你隨我輾轉多地,當年在山西,戰事吃,我一個人沒心思過年,你又是丫鬟,不好做主,便也囫圇吞糊弄著。”
裴慎說著說著,心下便了一團:“今年是你我頭一回好生過年,打從今年十二月的臘八節開始,到明年二月二龍抬頭,這中間俱聽你的,你想怎麼過,便怎麼過。”
過年啊。
沈瀾神思恍惚了一瞬,忽覺心中酸難當。親朋俱無,漂泊他鄉,這年過的,徒惹人傷心。
“這是怎麼了?”裴慎見神思恍惚,眉間籠著點點清愁,蹙眉道,“可是有人惹你不快?”
沈瀾只將滿腹愁緒強下去,笑著搖搖頭。
又過了一個多月,日子便了深冬。鵝大雪連下三日,干峰松白,萬壑凈雪,天地雪霽無瑕。
沈瀾穿上厚實的妝花織金紅襖,又披上毳,方才得了裴慎允許,開窗雪。
Advertisement
廊下庭中俱覆了紛揚快雪,黛瓦凈白,松柏新雪,出去,院中白茫茫一片,唯余下天上一痕睛藍。
沈瀾呼出的熱氣凝霜霧,化在窗格玻璃上,笑盈盈地去,又呵出一口氣凝霧,再去,反反復復,玩得不亦樂乎。
裴慎看得好笑,只拿書敲了敲腦袋:"可不許多看,當心著涼。"
沈瀾日里喝湯藥,昏昏沉沉睡覺,又被關了許久,早已看厭了庭前梧桐,如今換了新的雪景,難免高興,便笑道:“明日便是臘八了,廚下備了臘八粥,你可要分送給下屬?”
見今日終于有了些神,竟還想到了分送臘八粥,裴慎心也極好,便笑道:“自然是要送的。”
沈瀾瞥他一眼,笑道:“你此前可是說好的,過年便要帶我出去作耍。”
原來提臘八粥是為了提醒他此事啊。裴慎見眼著自己,便忍笑道:“元宵燈會,我便帶你出去頑。”
沈瀾角微翹,轉過去頭,歡歡喜喜地看雪。
難得這般高興,裴慎心里也歡喜,便笑道:“可想去取些雪水來烹茶?”
沈瀾奇道: “這又是什麼習俗?”
裴慎便上前,將摟在懷中笑道:“雪水烹茶天上味,桂花作酒月中香。你若愿意,便丫鬟們取了松柏上的薄雪,貯存在古甕里,封存上一年,去了土腥氣,明年便能拿來烹茶,清冽絕倫,幽香馥郁。”
沈瀾也不知他這是什麼文人癖好,便搖搖頭道:“你不讓我出去玩雪,還要我眼看著旁人玩,好生殘忍。”
裴慎被逗得發笑,只將攬在懷里,允諾道:“待你子好了,明年后年,此后每一年都由得你玩。”
明年后年……這樣的日子何時是個頭?沈瀾垂下眉眼,不說話了。
臘月初八,吃臘八粥。
臘月二十三,祭灶。二十四,掃房。
臘月二十九,上執戈佩劍的門神,拿順紅紙寫了春聯,又四掛上“鴻禧”牌。
年三十,四都懸了羊角燈,床頭又掛上金銀八寶。
裴慎與沈瀾一同了丫鬟小廝們的禮,又賞了金銀銀子,祭祖祀先完畢,兩人偎在一起,正打算吃團圓飯。
“將手過來。”裴慎招手道。
沈瀾頗為驚詫,只將手過去,卻見裴慎從袖中取出一串銅錢,拿紅繩將黃錢串龍,細細地將它綁在沈瀾手腕上。
黃錢、紅繩、白腕,煞是好看。裴慎欣賞了一會兒,方笑道:“給你的歲錢。”
沈瀾微怔,復又笑道:“我又不是小兒,哪里就要你歲錢了?”
裴慎便笑道:“你子不好,辟邪,討個好彩頭罷了。”語罷,又輕鬢發,聲道:“盼你來年順順利利,無病無災。”
檐下掛著芝麻桿,室焚燒著柏枝以煨歲,桌上的屠蘇酒熱氣騰騰,糖纏看果疊了一層層,竹聲劈啪作響。
沈瀾著手腕上凹凸不平的錢幣,在柏木的煙氣里,怔怔顰著裴慎笑盈盈的眉眼,良久,又垂下眼瞼去,默然不語。
裴慎也不知在想什麼,只是角微翹,心愉悅地去拉的手。在眾多丫鬟小廝親衛的笑鬧聲中,喂了一盞屠蘇酒。
辭舊歲,迎新春,新的一年開始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398 章

一品毒妃
二十二世紀毒醫學博士蘇子餘,毒術界的東方不敗,毒醫界的獨孤求敗。不料命運捉弄,竟是一朝穿越到幾千年前的東周,成為了膽小懦弱、呆傻蠢笨的丞相府庶女蘇子餘。身陷囹圄,生母慘死,主母迫害,姐妹下毒,生存環境非常惡劣。本想安穩度日的蘇子餘歎口氣……是你們逼我的!宅鬥?權謀?毒術?醫術?不好意思,讓你們見識一下,什麼叫滿級大佬屠新手村!
231.6萬字8.9 2121853 -
完結49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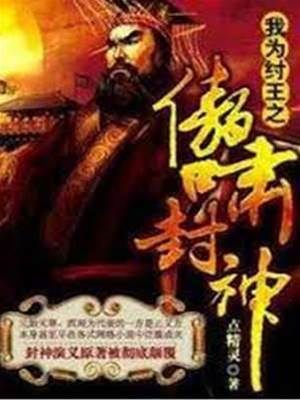
我爲紂王之傲嘯封神
二十四世紀的科學家張紫星在一次試驗意外中穿越時空回到《封神演義》中的殷商末年,以紂王的身份重生,爲改變未來亡國的命運,在超級生物電腦"超腦"的幫助下,新生的紂王展開了一系列跨時代的變革,巧妙地利用智謀和現代科技知識與仙人們展開了周旋,並利用一切手段來增強自身的力量,他能否扭轉乾坤,用事實徹底爲"暴君"紂王平反?楊戩,你的七十二變並不算什麼,我的超級生物戰士可以變化成任何形態!燃燈,你這個卑鄙小人,有我這個敲悶棍的宗師在,你還能將定海珠據爲己有嗎?
190.3萬字8 16803 -
完結1071 章

權寵天下:本候要納夫!
忠遠侯府誕下雙生女,但侯府無子,為延續百年榮華,最後出生的穆千翊,成為侯府唯一的‘嫡子’。 一朝穿越,她本是殺手組織的金牌殺手,女扮男裝對她來說毫無壓力。 但她怎麼甘心乖乖當個侯爺? 野心這東西,她從未掩藏過。 然而,一不小心招惹了喜怒無常且潔癖嚴重的第一美男寧王怎麼辦? 他是顏傾天下的寧王,冷酷狠辣,運籌帷幄,隻因被她救過一命從此對她極度容忍。 第一次被穆千翊詢問,是否願意嫁給她,他怒火滔天! 第二次被穆千翊詢問,他隱忍未發。 第三次,他猶豫了:讓本王好好想想……
102萬字8 40383 -
完結328 章
穿越荒年超市老板五歲半
宋坦坦一朝穿越古代,變成了個五歲半的小豆丁。災荒亂世,四面楚歌,剛來就直面顛沛流離的人生巨變,宋坦坦表示,我還小,我好累。不慌,她自帶空間,大超市+養豬場這雙buff夠不夠?!一來就救下美弱慘的病嬌小少爺,同為穿越人,病嬌綁定雞肋系統,一照面就識破宋坦坦有空間的事實。宋坦坦:我的超市不養廢人。你和你的辣雞系統什麼時候才能有點用,不是號稱能提前預知危險?正在被群狼狂追,宋坦坦回首避開一道狼爪子:就這?葉墨尋:這辣雞系統!系統:嚶嚶嚶,綁錯宿主了怎麼破?開荒,種地,發家,致富……看五歲半小女主,如何在...
63.5萬字8 213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