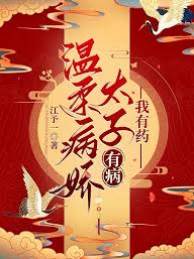《春閨記事》 第517節 攏才
孩子的哭聲,比大人的更人酸。
宋池和宋浣姊妹倆哭得人心裡發,淒厲無比。
宋盼兒原本還想去拉的,被們這麼一哭,自己也哭得止不住了。
胡婕這麼年輕,又是這樣慘死,誰不心痛?這些年,顧瑾之不在京裡,總是胡婕給宋盼兒解悶。若說從前宋盼兒不喜歡胡婕,可這麼多年的來往,也是深厚的。
中堂裡哭得了一團。
胡太太哭了半晌,又去廝打宋言昭。
宋言昭任打,只是在口中訥訥說了聲娘。
直到黃昏時分,這裡已經安頓得差不多了。
胡卓的妻子白氏對宋盼兒和顧延臻道:“今日真是辛苦姑父姑母,時辰不早,你們就先回吧,這裡有我們呢......”
宋言昭家裡人不在京城,宋盼兒就是他的至親。
沒有人家裡死了太太,要太太孃家來送葬的。
宋盼兒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走的。
“我們今天也歇在這裡。明早就是昭哥兒媳婦大殮,我怕來不及了。”宋盼兒道,“昭哥兒父母不在京城,是趕不及的,我就是昭哥兒的親人。這原該是我的本分。”
顧延臻也點點頭。
白氏沒再說什麼,去把這話告訴了他丈夫。
胡卓又問了胡澤逾。
胡澤逾見有個人願意幫襯,是最好不過的。胡澤逾還在刑部任職,現在又是國喪,他明天上午還要進宮哭喪。
兒的喪禮,是大不過先帝的,他分乏
他答應了,讓顧延臻和宋盼兒今天留在這裡。
顧瑾之和朱仲鈞哭喪之後,就去了仁壽宮。
太后這兩日子不舒服。
並沒有什麼大病,只是人老了。又白髮人送黑髮人,心極差所致,志鬱結,顧瑾之和朱仲鈞就在仁壽宮逗留一下午。和太后說說話,給擔憂。
Advertisement
等回來的時候,發現弟弟煊哥兒正在家裡等。
煊哥兒把胡婕的事,簡明扼要告訴了顧瑾之。
顧瑾之腦袋發暈。
似被什麼重重敲了下頭。
“.....爹和娘下午就去了。”暄哥兒對顧瑾之道,“七姐,咱們也去看看吧?”
顧瑾之點點頭。
朱仲鈞見顧瑾之很傷心的樣子,有點不放心,道:“我也去吧。”
他跟著一塊兒去了。
路上,顧瑾之掌心出了一手的冷汗。
難以置信。
怎麼也沒有想到,胡婕會用這種極端的方法來反擊。
煊哥兒又說。胡婕最終沒有殺那個孩子,顧瑾之眼淚奪眶而出。
“當時走的時候,難的,我竟沒有挽留,還趕。”顧瑾之哭著道。“我只是想,夫妻之間什麼大不了的,逃避總不是辦法。哪裡知道,他們竟然弄得你死我活。”
非常後悔。
若是前天沒有趕走胡婕,胡婕只怕不會死。
朱仲鈞輕輕拍的後背。
煊哥兒也勸顧瑾之。
“......在咱們家,一住就是小半個月,足見的固執。”朱仲鈞寬顧瑾之。“你看走的時候,鎮定自若,又讓你哥哥來接,把孩子留在孃家,回家又寬丈夫,讓丈夫放心。這不是一時能想到的。是早有這個計劃了。
沒有手,不過是對丈夫還存了幻想,以爲夫妻之間還有誼,他會來接的。等你告訴他,你報信了。丈夫七日不來,就死心了,才下定決心走到這一步。這不是你的錯,這是他們夫妻之間的問題。”
朱仲鈞分析得特別理智。
可顧瑾之就是難。
Advertisement
人都死了,說這些還有什麼用?
到了宋家,也大哭了一回。
胡婕停靈七日,五月初一出殯。
宋家的祖墳在延陵府,胡婕的不可能運回延陵府,胡澤逾做主,燒了胡婕的,只是把骨灰裝殮,由宋言昭扶靈回延陵府。
宋言昭也辭了,遣了送家裡的下人。
胡婕的葬禮,宋盼兒和顧瑾之了不錢,宋言昭自己沒花什麼錢。他把剩下的錢財盤點,大約還剩下六千兩銀子。
他將這銀子和胡婕的陪嫁,都給了胡家。
他說:“池姐兒和浣姐兒若是願意跟我回延陵府,家裡自然不會輕待他們;若是們不願意,就留在外祖母這裡,等大了些再回去......”
孩子沒有娘,跟著外祖母更心。
宋言昭是爲兒打算。
胡太太自然不願意外孫回去,答應了。
延陵府的宋大太太,是個好人,卻不是個老好人,胡太太曾經和宋大太太也打過道,清楚宋大太太的爲人,不放心把外孫給宋言昭帶回去。
胡婕害得宋大太太的兒子丟了,這輩子只怕再不能進仕途,怎麼會善待胡婕的兒?
胡太太要留外孫。
胡澤逾不同意。
他說:“我這,只怕也保不住了。咱們一大家子,花銷也是難事。讓池姐兒和浣姐兒跟著婿回去。們到底姓宋,不姓胡。”
胡家比較拮據,多養兩個人是爲難的。
最重要的,這兩孩子不姓胡,將來養的不好,宋家要挑刺的。
胡澤逾也有自己的孫兒孫。
世道太艱難了。
胡婕的事,震驚了朝野上下,已經有人在彈劾胡澤逾教無方,需得懲戒,胡澤逾覺得他的路到頭了。
Advertisement
他沒有了俸祿,家道會更難,沒必要讓兩個外孫留在胡家苦,這是胡澤逾的心思。
胡太太哭了一回。
胡澤逾不同意,胡太太也留不住,也沒有再留了。
胡家沒有要宋言昭的錢,胡婕的陪嫁倒是留了下來。由胡太太替池姐兒和浣姐兒保管,以後給們做陪嫁。
宋言昭也沒有堅持,帶著剛剛滿月的兒子和兩個,扶靈回延陵府。
他這一路上。是照顧不過來的。
他就託顧延臻,問他能不能讓煊哥兒隨行,一路上幫襯他幾分。有個人相互照應,比下人靠譜。
他是擔心兒們。
煊哥兒是不會走的,他媳婦快要產子,他還要留下來做父親。
顧延臻卻是想出去走走的。
他和宋盼兒商量,由他送宋言昭回延陵府。
宋盼兒只是道:“回去是可以的。這麼大年紀了,行事要尊重,別聽了琇哥兒和洪姨娘的蠱,把洪姨娘接回來。你也知道我的厲害。我現在可是什麼也不顧了......”
顧延臻很尷尬,道:“我哪有這個閒心?”
到底胡婕的事在前,顧延臻也不敢多想。
胡婕的事,在京裡影響特別大。
那些士大夫,極力抨擊胡婕這種行爲。因爲他們都有妾。他們都怕妻子學樣,也來個家宅不寧,所以詆譭胡婕,甚至寫書辱罵。
這件事,轟了一時,甚至載史冊。
胡婕實在太兇悍了,讓那些想妻妾齊人之福的士大夫驚慌失措。
這種苗頭。必須扼殺,才能保住男人對人絕對的統治地位。
哪怕丁點的反抗,都要鎮,何況是這麼大的反抗?
但是,宅的人們,也有們的明。
Advertisement
一年半載。真有那怕死的,真的浪子回頭了。
想來也諷刺。
胡婕這條命,就換了這麼個結果。
五月初六,二十七天的國喪終於過去了,孝宗的梓宮移居皇陵。弘德帝除服理政。宮裡那些裹了的白紗,都除了去,顯出黃。
國喪的蕭條肅穆就減了大半。
國喪後第一次開朝,史就彈劾胡澤逾,甚至彈劾胡澤逾的族兄永熹侯胡澤瀚。
永熹侯爲了自保,放棄了胡澤逾。
胡澤逾丟了。
他原本還想,再混幾年,將來若是能得個政績三年優,給兒子蔭蒙一個。
如今,都了泡影。
他們在京裡是住不下去了。
胡澤逾丟之後,胡太太又氣了一回,整個人奄奄一息的。
朱仲鈞上門拜訪,問胡澤逾:“廬州是鄉下地方,民風卻好。若是胡先生無意在京城,想換個地方整頓整頓,廬州倒不錯。我們不日也要回去。胡先生若是能跟我回去,我激不盡……”
他之前就看重胡澤逾。
胡澤逾是有大才的。
他是既沒有人脈,也沒有機會。
胡澤逾則笑道:“我這一家老小,哪裡丟的下?”
“都帶過去。”朱仲鈞笑道,“聽說令郎沒有考試運,每次科考都要生病,卻擅長心算,又通書籍。我廬州王府,正是缺人才的時候。先生和令郎若是願意屈尊,本王送你們宅子和五百畝在廬州附近的良田,保證您一家老小不會著……”
胡澤逾猶豫了下。
他在京裡,著實是活不下去的。
京裡米珠薪桂,有俸祿的時候都過得,何況沒了俸祿?
他是不得不走。
但是他不想表現得如此急迫。
他對朱仲鈞道:“王爺容在下考慮考慮……”
“先生儘可從容。”朱仲鈞笑道,“我們啓程,也有半個月。”
胡澤逾送走了朱仲鈞,把這話告訴了胡卓。
胡卓是讀了很多書,也有很多見解的。
他酷研究兵法,這是其他人不知道的。
他想去從軍,怎奈父親不同意。
廬州雖然不是邊防,也有護衛軍啊,說不定真的能一展抱負。況且廬王說他擅長心算,也是真的。
“爹,咱們去吧。”胡卓道,“留在京裡,您想要起復,就得看永熹侯的臉。爹,咱們別低聲下氣了,他本把咱們家當下人。況且,妹妹的事,娘心一直不好。若換個地方,也許好些,咱們也節省些花銷。廬州什麼都比京城便宜啊。“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611 章

攝政王的嬌寵毒妃
長公主之女,無比尊貴的身份,可落在將軍府中,卻是個人人嫌棄的廢物郡主。 可無人知這個名滿京城的廢物,其實滿腹錦繡,實為絕世風采。 但她深愛著雲一言,甚至甘願為他嫁給了明止。 她手裡捏著刀同明止博弈,助雲一言登上皇位,最終卻換來他毫不猶豫的背叛。 臨死她才知道明止是那樣愛她,死前都要保全她。 重來一世,她斗渣男欺庶女,勢要活出個錦繡前程。 她這虐渣之旅,該有個攝政王作陪才算圓滿。 可這個攝政王有點小傲嬌。 「明止,我心悅你已久」 「郡主,你已有婚約,不合適」 雲輕煙跺腳,「我馬上退婚,你娶我」 等她真住進王府,才知他早已下套。 「明止,你這個大騙子」 明止輕笑,「求愛這事,不算騙」
238.2萬字8 23920 -
完結355 章
神醫毒妃:妖孽王爺枕上寵
玄門第三十六代門主,醫毒雙絕,一身奇脈,竟穿越成了寧侯府癡傻嫡女楚玥安。 親娘慘死,親爹不疼,刁奴欺辱,繼母虐待,姐妹算計,還有一位將她當做奇貨的祖母! 她楚玥安豈會任人拿捏?奇葩親人陰謀陷害?談笑間送去地獄! 未婚夫渣男嫌她貌丑? 驚艷容貌閃瞎他的雙眼! 擋我者,打! 虐我者,殺! 辱我者,誅! 本該在彪悍的人生道路上狂奔,卻不料惹上了幾朵爛桃花,神秘莫測的密境少主,毒舌厚顏的丞相公子,還有那位傳說被女人掏空了身子的王爺……
87.2萬字8 28531 -
完結23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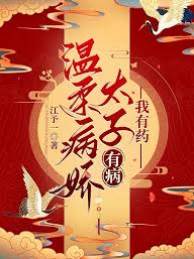
溫柔病嬌太子有病,我有藥
【古言甜寵 究極戀愛腦深情男主 雙潔初戀 歡快甜文 圓滿結局】 謝昶宸,大乾朝皇太子殿下,郎豔獨絕,十五歲在千乘戰役名揚天下,奈何他病體虛弱,動輒咳血,國師曾斷言活不過25歲。 “兒控”的帝後遍尋京中名醫,太子還是日益病重。 無人知曉,這清心寡欲的太子殿下夜夜都會夢到一名女子,直到瀕死之際,夢中倩影竟化作真實,更成了救命恩人。 帝後看著日益好起來,卻三句不離“阿寧”的兒子,無奈抹淚。 兒大不中留啊。 …… 作為大名鼎鼎的雲神醫,陸遇寧是個倒黴鬼,睡覺會塌床,走路常遇馬蜂窩砸頭。 這一切在她替師還恩救太子時有了轉機…… 她陡然發現,隻要靠近太子,她的黴運就會緩緩消弭。 “有此等好事?不信,試試看!” 這一試就栽了個大跟頭,陸遇寧掰著手指頭細數三悔。 一不該心疼男人。 二不該貪圖男色。 三不該招惹上未經情愛的病嬌戀愛腦太子。 她本來好好治著病,卻稀裏糊塗被某病嬌騙到了手。 大婚後,整天都沒能從床上爬起來的陸遇寧發現,某人表麵是個病弱的美男子,內裏卻是一頭披著羊皮的色中餓狼。 陸遇寧靠在謝昶宸的寬闊胸膛上,嘴角不禁流下了悔恨的淚水。 真是追悔莫及啊~
42.5萬字8 79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