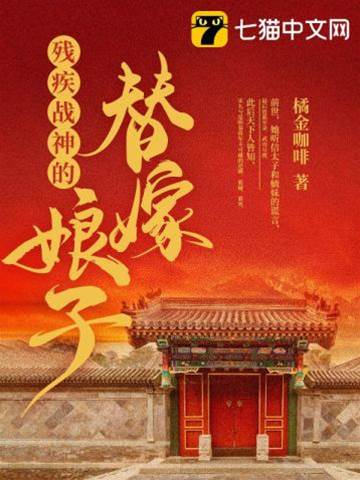《魚水沉歡》 第一百一十章 虐她(2)
聞言,一雙紅的拳頭恨恨的攥了攥,丁小魚終是咬著脣向著韓諾走去。
只是,當好不容易窘紅著臉走近韓諾時,卻是腦袋一片凌、混沌:寬,他竟讓要爲他寬。
丁小魚深呼吸一口氣,彆扭的手,卻是不知道該從那裡下手。
“先解腰帶!”
看著丁小魚杵在原地似無從下手的樣子,韓諾邪惡的吸了吸鼻子以後,衝著丁小魚指揮道。
“……哦。”
一顆小心臟沒有規則的跳了跳,丁小魚有些艱難的、再次強行吞下了一口唾沫。
最終,終是的出雙手不自然的探到了韓諾的腰間,試圖去解開他腰間的那條錦腰帶。
只是令丁小魚到崩潰的是,折騰了好大一會兒,韓諾腰間的那條錦腰帶像是跟有仇似的依舊安然無恙的束在他的腰間,使得怎麼倒騰就是解不開。
越是解不開,丁小魚便是越急;越急,反而越忙;越忙越,越越解不開。
沒過一會兒,丁小魚巧的鼻尖上已是冒出了細的汗珠,連著一張俏臉也越發變得的嫣紅起來。
韓諾終於沒有了耐,囂張的用目剮了丁小魚一眼,他譏諷道,“丁小魚,虧你有逃跑的能耐,此刻竟然連一條腰帶都對付不了。”
而說話間,他只是將雙手在腰間隨便的弄了一下,他腰間的那條錦腰帶便是很聽話的被他解了下來。
明明知道韓諾這是在蛋裡挑骨頭、明著爲難於,但這麼簡單的事都不會,這真是明著找罵。
丁小魚悻悻然的咋了咋舌,卻只得咬著牙忍著韓諾的冷嘲熱諷。
“去,拿些花瓣來。”
Advertisement
然而在一下秒,韓諾所說出的話卻是差點令丁小魚驚死。
自古以來,只有人在沐浴的時候才用花瓣來增加香。可是,他是一個男人啊!
“還不去?難道你想與本蕊子來一個鴛鴦浴?”
看著丁小魚又窘又,韓諾突然心大好,揶揄的冷喝一聲,他突然猛的敞開他上寬鬆的袍,又惡作劇般的在丁小魚的面前即刻了去。
此刻,面對韓諾的、健碩的充斥著*的膛,丁小魚只覺得臉頰滾燙滾燙的。
無比的憤然轉過,連忙應道,“我這就去。”
急急的衝出房屋,丁小魚靠在牆壁之上直氣。
又是鴛鴦浴!
他屢次要挾於……
丁小魚在此刻恨不得幾句口,但卻終是不能違背韓諾的命令,只得接過門口侍衛提前準備好的合*歡花花瓣向室走去。
此刻,韓諾已然跳進了浴桶之中。
由於尷尬、惱,丁小魚彆扭的將眸移向別,然後紅著臉以最快的速度將**花的花瓣,灑進了浴桶之中。
“你怎麼不問問,本世子爲什麼要用這合*歡花沐浴?”
霧氣氤氳的浴桶之中,韓諾一邊舒坦的靠在浴桶的邊巖上,一邊慵懶的問道。
而在水氣的映下,韓諾泡在水中那模糊唯的形、異常完的倒影在浴桶之中,更是將他的渡上了點點晶亮的彩,從而生生將他一張倜儻的臉頰映襯的越發如罌粟般令人到蠱。
這般蠱的男人,使丁小魚在偶然間只撇了一眼,便是再也不敢盯著他仔細看下去。
“不知道。”
說多了都是錯,丁小魚索直接說了“不知道”。
Advertisement
聞言,韓諾笑了起來,“合*歡花晝夜開放、香飄四溢。合*歡花的花,寓意也好。象徵著兩兩相對、永遠恩、是夫妻好合的象徵。”
“……啊?”
聞言,丁小魚失聲“啊”道。
他還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似乎將丁小魚激怒讓他有很大的就,卻見韓諾朝著丁小魚睥睨著眸子繼續笑道,“如今在你面前用了**花的意思是,本世子想與你兩兩相對、郎妾意。”
丁小魚,“!!!”
韓諾的話差一點將丁小魚震死過去。
誰要與他兩兩相對、郎妾意?
他這是在明著調*戲於。
手中攥著的**花花瓣被丁小魚掌心的力度的枯萎破碎:如若不是王蕭與大憨掌握在他的手中,誓死也不會在此地伺候於他。
韓諾泡的舒舒服服,丁小魚卻是在一旁搞的彆彆扭扭。
還好韓諾並沒有再對丁小魚出言譏諷,這倒是令安心不。
伺候韓諾沐浴完畢。
丁小魚的手中又多出韓諾的一大堆服。
無奈之下,只得又將韓諾的服任命的拿到水井旁去洗。
洗完了服,已是下午,此刻韓諾已經駕著馬兒再次向楊都郡的難民聚集地疾馳而去,由於一天滴水未盡,丁小魚幾乎完全虛。
可是,要進食的要求卻被侍衛犀利的拒絕,且在韓諾走後,他還特意命兩個出手敏捷的侍衛寸步不離的跟著丁小魚。
丁小魚原本想從他們的裡知道些王蕭與大憨的消息,但兩名侍衛卻只是冷著臉嚴肅的跟在丁小魚的側,對王蕭與大憨的況本隻字未提。
後面跟著這麼兩個瘟神,使得丁小魚做什麼都覺得彆彆扭扭的。
Advertisement
“我想出去走走。”丁小魚抗議的說道。
“不行。”兩名侍衛果斷的拒絕。
“我要去見王蕭與大憨。”
“不行。”
“那我要吃飯。”
“對不起,世子爺吩咐了,丁士子要上三天三夜。”
丁小魚,“!!!”
真的有一種天天不靈、地地不應的悲慼覺。
“我要去茅房!”無比憤恨的喝道,“難道這個你們也不許嗎?”
“這個可以。”
聞言,丁小魚冷哼一聲,轉就走。誰料,後的兩名侍衛卻是立即又跟了上來。
“難道去了茅房你們也要跟著嗎?”丁小魚惱道。
“是的,丁士子。”
“你們……”
“我們會等在外面的。”就在丁小魚氣的對兩名侍衛怒目相向之時,兩名侍衛應道。
“你……你們……”
聞言,丁小魚氣憤的跺了跺腳,繼而轉向昨夜關了閉的房間憤恨的走去。走進了房屋,無比氣憤的、“咚”的一聲重重的將房門關上。
再看那兩名侍衛,則是忠於職守的、像兩個門神似的把守在了的門外。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51 章

醫判
【医生+探案】【双C冤家】在山里养病十年的叶四小姐回家了,所有人都在等她的笑话。才子郭允肯定要退婚了,毕竟叶四小姐蠢丑。叶老太爷要撵她父女,因为不养闲人。叶家虎狼们准备“吃”了她,解决分家产的孽障。可怎么着,要退婚的求婚了、撵人的变黏人的、孽障反吃了虎狼了呢?“有不服的?一起上!”叶四小姐道。沈翼打量叶文初:“给我治病的神医,是你吧!”“您有证据吗?没有的话咱们就继续谈生意好吗?”叶文初道。
122.2萬字8 42476 -
連載1915 章

王爺,聽說你要斷袖了!
傳聞,冥王殿下戰功赫赫,殺人如麻,令人聞風喪膽!傳聞,冥王殿下長相絕美,乃是東陵國第一美男子!傳聞,冥王不近女色,有斷袖之癖,看上了蘇家廢材大少爺!都說那蘇九男生女相,卻是個又軟又弱,任打任罵的廢物。只見某人搖身一變,恢復女兒之身,傾國之姿...
196.5萬字8 29382 -
完結52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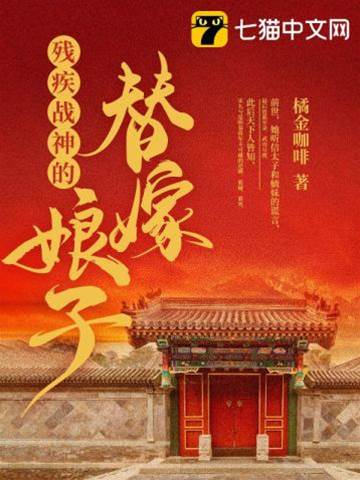
殘疾戰神的替嫁娘子
【重生+男強女強+瘋批+打臉】前世,她聽信太子和嫡妹的謊言,連累至親慘死,最后自己武功盡廢,被一杯毒酒送走。重生后她答應替嫁給命不久矣的戰神,對所謂的侯府沒有絲毫親情。嘲笑她、欺辱她的人,她照打不誤,絕不手軟。傳言戰神將軍殺孽太重,活不過一…
97.6萬字8.18 35390 -
完結63 章

長燁無月
【和親公主vs偏執太子】【小短文】將軍戰死沙場,公主遠嫁和親。——青梅竹馬的少年郎永遠留在了大漠的戰場,她身為一國公主遠嫁大晉和親。大漠的戰場留下了年輕的周小將軍,明豔張揚的嫡公主凋零於大晉。“周燁,你食言了”“抱歉公主,臣食言了”——“景澤辰,願你我生生世世不複相見”“月月,哪怕是死,你也要跟朕葬在一起”【男主愛的瘋狂又卑微,女主從未愛過男主,一心隻有男二】(男主有後宮但並無宮鬥)(深宮裏一群女孩子的互相救贖)(朝代均為架空)
20.9萬字8.18 17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