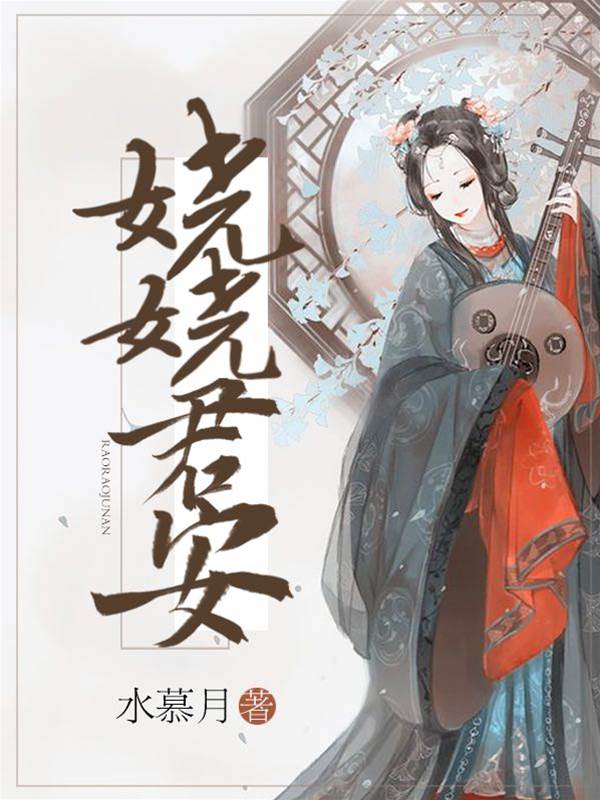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繼室難為》 第61章 第 61 章
一個奏摺,一篇文章,並置於桌案之上,沈蘭溪逐字逐句的看過,手指輕叩了那案桌一下,果斷道:「這兩篇,不是一人所書。」
三人皆鬆了口氣,許有才求知若的問:「敢問如何見得?」
沈蘭溪在那摺子上挑了幾個字出來,又引他去比對那文章上的幾個字,「字形結構相同,但明顯書寫筆順不同,所以只是達到了形似而已,你再看,這篇文章的這幾個字,它的落筆下與收筆上提的作並不流暢,這是在對抗自己的書寫習慣,再有,你用這個鏡看,這個摺子的筆力較重,起承轉合之尤為明顯,但是這文章的卻不然,筆形相似,力道迥然不同。」
「誒,是這樣」,許有才一臉驚嘆的仰頭,招呼道:「來,祝大人一同來瞧?」
祝煊深吸口氣,不著痕跡的開旁邊這異常熱之人,接過鏡,在那青蔥細指著的地兒仔細看。
經沈蘭溪一說,先前疏的皆被摘了出來,鏡放大字,確能看出所說的幾點不同來,先前便覺得缺了些什麼,如今才察覺,九分的形似,但因這些細微不可察的不同,缺了神似。
「那、那……」向淮之著手,激開口。
沈蘭溪到他灼熱的視線,立馬打斷,「今日我只是來送了湯,別無其他。」臉上掛著微微笑,說著起,「避雨至此,便不多打擾各位大人辦案了,先行告辭。」
世間沒有普度眾生的神佛,沈蘭溪更不是救世主,提點一二是為良知,但也僅此罷了。
沒有安全保證的朝代,樹大招風之理比後世更甚,想好好活著。
祝煊隨之起,「風大雨急,我送你出去。」
「多謝郎君。」沈蘭溪與之一笑,聽出了其中袒護之意。
Advertisement
不願意,他只會護著他,昨夜的話,倒是沒浪費口舌,沈蘭溪兀自歡喜。
出了府衙,沈蘭溪踏上馬車,把油紙傘給了祝煊,「染風寒了?早些回來,給你煎藥煮湯。」
有人牽掛,心裏熨帖的,祝煊笑著應,「好。」
元寶落後把依依不捨的兩人幾步,呲著牙嗤嗤的笑,毫不收斂。
哪裏有這般說不完的話,家娘子真麻~
馬蹄聲清脆,沈蘭溪先把元寶送回了鋪子裏,思索一瞬,跳下馬車,從雨霧裏衝到傘下。
「娘子?」元寶一驚。
沈蘭溪一雙眸子濃如墨,「澄哥兒的墨錠用完了,我順道給他買些。」
兩句話間,兩人走到了門口,沈蘭溪催促,「你去忙吧,不必陪我,買完我便回府了,今日落雨,你也早些回來。」
被關心著,元寶笑得喜滋滋的,「是,娘子。」
隔壁鋪子,用了一個冬的棉簾子被拿掉了,一推門,便瞧見那掌柜的與之前那般趴在櫃枱前打瞌睡,似是畏寒,上還套著一襲灰藍的棉袍子,出的一截手指青白。
沈蘭溪上前,屈指在櫃枱上輕叩兩下,驚醒了那夢中人。
「嗯……喲,夫人大駕臨啊……」袁禛抬起頭,瞧著那錦金釵之人,笑說一句,慢吞吞的了酸困的脖頸。
沈蘭溪打量他一瞬,收回視線,「家裏小孩兒的墨錠用完了,順道從你這兒買些,掌柜的不介紹一下?」
這人,從初識便未曾瞧清楚過。
鋪子裏依舊燃著敬神的沉香,卻是嗅不到了那松煙墨香。
聞言,袁禛從櫃枱後站起來,綳著手臂了個懶腰,踏足那擺滿墨錠的一塊兒地,一一介紹過又道:「夫人來錯地兒了,我這兒都是尋常墨錠,小郎君金尊玉貴的,怕是用不慣。」
Advertisement
沈蘭溪視線一一掠過那擺放整齊的墨錠,無一例外
,都是油煙墨。
「雖是金尊玉貴,但那孩子毫不氣,便是便宜的也用得」,說了句,忽的側頭,「怎的不見松煙墨?」
袁禛垂在側的手一僵,視線與對上。
幾個轉瞬便明了,這哪是來買墨錠的?
他扯笑了下,揶揄出聲:「我這鋪子挨著夫人的『黃金屋』,自是要靠文房四寶賺銀子,松煙墨不比油煙墨有澤,價格略低,做生意嘛,自是要賣貴的才賺銀子不是?」
他眼中神轉瞬很快,但沈蘭溪還是鋪捉到了。
這話是在裝糊塗,也不破,隨手拿了兩塊讓他結賬。
沈蘭溪出了屋子,順手幫他把門闔上,鋪子裏靜了下來,仿若方才的一切都只是他沒睡醒的夢。
袁禛怔怔的盯著那木門愣了片刻神,轉掀開了牆上掛著的一幅山水圖,慢吞吞道:「被發現了,叔叔,你依舊不同意嗎?」
聲音迴轉在這生意清淡的鋪子裏,又瞬間遠去。
--
臨近清明,淅淅瀝瀝的小雨下個沒完,沈蘭溪被府中清明祭祖的事絆住手腳,沒個清閑,瞧著那雨便覺心煩意,夜裏對著祝煊也沒個好臉。
平白了這炮火的祝煊,翌日告了假,幫理府中雜事。
難得一個飽覺,沈蘭溪睡得日曬三竿才起,想起昨夜自己惡劣的態度,有些歉意的蹭過去,趴趴的伏在他背上,「郎君~」
「醒了?」祝煊肩背筆直,著那重量,「今日沒有落雨,用過飯,我帶你去郊外跑馬,可好?」
沈蘭溪睡得紅撲撲的臉頰蹭了蹭他的肩背,「你今日不用上值嗎?」
祝煊『嗯』了聲,就見阿芙出現在了門口。
在府中憋悶多日,沈蘭溪自是歡喜,踩著鞋風風火火的跑去梳洗。
Advertisement
「進來。」祝煊瞧著門口的婢道。
阿芙這才進了屋子,恭敬稟報:「郎君,事都吩咐下去了,也差人去知會了三娘子,來人回稟說,三娘子明日一早回來。」
「知道了,午後我與娘子出府,若是還有旁的事,便尋母親邊的曹嬤嬤說,會看著辦的。」祝煊囑咐一句。
「是,婢子記下了。」
用過午飯,沈蘭溪換上了一束袖的袍子,沒挽髮髻,梳了高馬尾,瞧著甚是英姿颯爽,只那糟糕的騎,卻是對不住折裝扮。
祝煊無奈扶額,出了城便與共乘一騎,馬蹄揚起塵土,把那隨行的幾人甩在了後。
從未這般暢快的跑過馬,雖是顛的屁疼,但被人圈在懷裏的沈蘭溪依舊覺得快意,整個人都輕飄飄的,微涼的春風拂面而過,帶走了臉上的熱意,後抵著的卻是越來越熱。
微微回首,眨著眼戲謔道:「春衫薄,郎君這般,不怕被人瞧見失儀?」
祝煊面端方,只那滾燙的耳暴了他的窘迫。他的娘子在懷,又怎能坐到心如止水,不為所?
他垂首,含住那的白玉耳垂,在顛起之時又鬆開,只氣息滾熱的道:「那便再快些,讓他們追不上。」
正是春明的時節,綠茵茵的草地是憋了一個冬的人的所,行進深,幾人視線相對,皆是一震。
沈蘭溪瞧著那被在樹榦上被迫親吻的人,眼珠子險些掉出來。
背大刀的子果真生猛啊!
褚睢安瞧見那馬背上的兩人,霎時一張臉紅,趕忙推了下著的姑娘,『唔唔』出聲。
丹掀起眼皮瞧他面上的飛霞,又吸了下那被親得紅艷的,這才著齒鬆開他。
馬蹄聲疾,早就聽到了,只是不在乎被人瞧見罷了。
Advertisement
京城眾人皆知丹縣主心屬梁王
,擔了這名兒,自是得嘗些甜頭才算不虧。
「慫貨。」輕嗤一聲。
褚睢安深吸口氣,掐了下的細腰,惱火道:「名聲不要了,臉面也不要了?」
哪有這般把閨房之樂示之於眾的?!
丹冷笑一聲,仰頭迅速在他滾的結上咬了一口,留下兩排牙印,眼瞧著那小球滾得愈發的快,反問:「如今誰還有臉面?」
要臉面做甚?左右這輩子都要與他糾纏,嫁不得人,他娶不了妻,做得什麼清白人?
沈蘭溪直脊背看得正爽,卻是不防被人捂了眼睛,後之人在耳邊輕聲語,「別學。」
沈蘭溪輕哼一聲,才不會與他說,會的可多啦!
褚睢安故作鎮定的整了整皺皺的裳,勉強撿起碎渣渣的臉面,走出那棵大樹的庇蔭,倒打一耙道:「讓我給你們帶孩子,你們倆倒是玩兒得開心啊。」
祝煊輕笑一聲,眼睛裏的調笑明晃晃,「不及梁王樂陶陶。」
褚睢安被他堵了一句,忽的瞇眼,哼笑道:「坐在馬上做甚?下來啊。」
瞧見那樣脈僨張的一幕,任誰都不會沒有反應,祝煊面上神淡淡,手臂圈著前面乖乖坐著的小娘子,含笑道:「就不打擾二位了,我們夫妻先告辭了。」
他說罷駕馬而去,把那惱怒的人那句甩在後。
「呸!祝二郎你就裝!」
「澄哥兒也在這兒嗎?」沈蘭溪側首問。
「這兒離校場不遠,許是褚睢安帶著澄哥兒和英哥兒出來跑馬了,那倆估在前面。」祝煊答,忽的那邦邦被細指點了下。
「為人父喲~」幸災樂禍得不要太明顯。
話音剛落,沈蘭溪箍在腰間的手臂忽的收,撞上他的腰腹,男人的嗓音仿若含著巖漿,「很好玩兒?」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229 章
帝凰之神醫棄妃
大婚當天,她在郊外醒來,在衆人的鄙夷下毅然地踏入皇城…她是無父無母任人欺凌的孤女,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鐵血王爺.如此天差地別的兩人,卻陰差陽錯地相遇.一件錦衣,遮她一身污穢,換她一世情深.21世紀天才女軍醫將身心託付,爲鐵血王爺傾盡一切,卻不想生死關頭,他卻揮劍斬斷她的生路!
448.5萬字8.38 388648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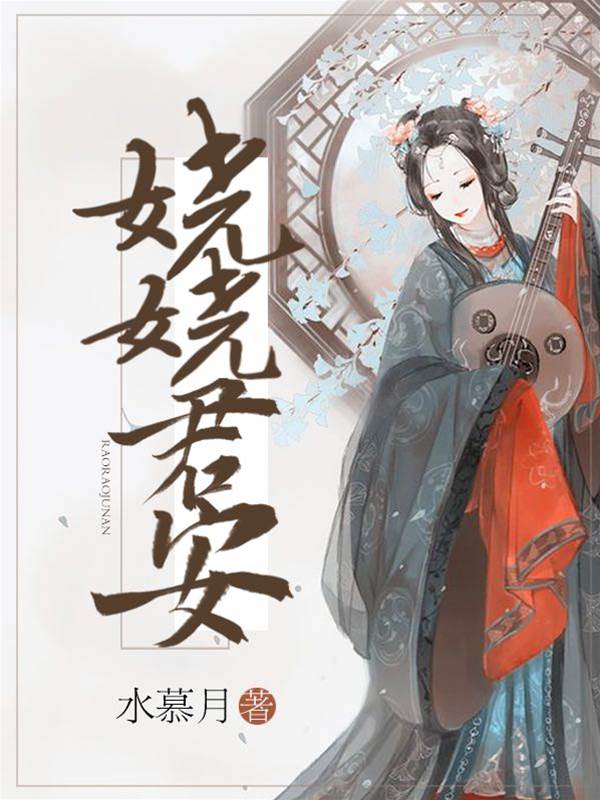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
完結648 章
重生后,我成了渣男他皇嬸
因道士一句“鳳凰棲梧”的預言,韓攸寧成了不該活著的人。外祖闔府被屠,父兄慘死。太子厭棄她卻將她宥于東宮后院,她眼瞎了,心死了,最終被堂妹三尺白綾了結了性命。再睜開眼,重回韶華之時。那麼前世的賬,要好好算一算了。可慢慢的,事情愈發和前世不同。爭搶鳳凰的除了幾位皇子,七皇叔也加入了進來。傳說中七皇叔澹泊寡欲,超然物外,
116.3萬字8.18 58167 -
完結242 章

教不乖,佞臣替人養妹被逼瘋
【傳統古言 廢殺帝王權極一時假太監 寄人籬下小可憐 倆人八百個心眼子】少年將軍是廝殺在外的狼,窩裏藏著隻白白軟軟的小兔妹妹,引人垂涎。將軍一朝戰死沙場,輕躁薄行的權貴們掀了兔子窩,不等嚐一口,半路被內廠總督謝龕劫了人。謝龕其人,陰鬱嗜殺,誰在他跟前都要沐浴一番他看狗一樣的眼神。小兔落入他的口,這輩子算是完……完……嗯?等等,這兔子怎麽越養越圓潤了?反倒是權貴們的小團體漸漸死的死,瘋的瘋,當初圍獵小兔的鬣狗,如今成了被捕獵的對象。祁桑伏枕而臥,摸了摸尚未顯孕的小腹。為了給兄長複仇,她忍辱負重,被謝龕這狗太監占盡了便宜,如今事得圓滿,是時候給他甩掉了。跑路一半,被謝龕騎馬不緊不慢地追上,如鬼如魅如毒蛇,纏著、絞著。“跑。”他說:“本督看著你跑,日落之前跑不過這座山頭,本督打斷你的腿!”
42.7萬字8.18 157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