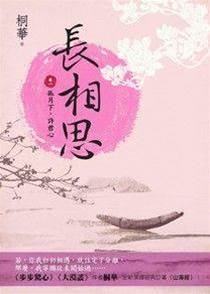《庶門風華:皇室小悍妻》 第452章 離開
「豉苗?天吶,你居然變金了?你吃了多蠱蟲啊?」
豉苗得意地轉圈,最初的圓蟲,變了中指長短的長蟲。
寶昕迅速將它握在手裏,轉到無人,這才打開手心:「豉苗,他來了是不是?他待人衝擊城池,只是想引開法堯王對不對?你帶我去找他吧。」
豉苗點點頭,其實在寶昕看來,豉苗分不出頭尾,都差不多細。
眼睛也不明顯。
寶昕佝僂著子,在豉苗的指引下,往集市外面走,必須立即找到秦恪,否則,等宮裏發現跑了,次妃、太后絕對不會阻攔那些人出兵查找的,因為,太后要顧忌母子,次妃還想更進一步,還想抓住這個男人的心。
看慣了西梁人的強壯勇猛,法堯王無疑是儒雅俊的,秦雅姜為他心,可以理解。
希如意吧,看在幫襯自己的份上。
Advertisement
豉苗把寶昕帶到一安靜之所,看起來倒像城中比較貧困的地方,來到一低矮的石屋前。
「這裏?」
寶昕覺得相信一隻蟲,還是邪門的,可是只能相信這隻蟲。
鼓起勇氣敲門:「姑且相信你一次,錯了,別人也認不出我的。」
門應聲而開,寶昕對上彭信笑嘻嘻的臉。
「彭信?你也來了?」
彭信實在沒臉見寶昕,為護衛,居然把弄丟了,太丟臉了。
「哎呀,不怪你們,我以為不出天擎關就沒事,怪我。」
彭信乃是江湖俠客出,自然有許多路子,難怪秦恪他們在西梁如此順利。
「還有我。」
說著話,阿多走了出來,還有嘟著的小豬。
寶昕上前捶了阿多一下,又達渥部的阿多帶路,秦恪他們必然是如無人之境啊!
「阿多,謝謝你!」
「我們需要這麼客氣嗎?」
「姐姐!」
Advertisement
「小豬,辛苦你了!」
秦恪帶笑,從屋子裏出來,寶昕衝過去,一頭撞進他懷裏,摟住他的腰。
秦恪手一,寶昕覺得不上氣來,連忙推開,想了想,開口說的話卻是:「阿哥哥,我是清白的。」
秦恪想笑,卻更心疼,將臉埋在寶昕脖子邊,寶昕覺得頸子一涼,心裏又酸又痛,的阿哥哥哭了?
「沒時間細說,先出城,安全了再說其他。」
彭信催促著,阿多立即去做安排,寶昕這才想起自己抹了薑黃的,咦,這樣阿哥哥也不嫌棄?
「別,這樣才不會引起注意。」
這裏的平民子都不好,大多黑中帶紅,薑黃倒是不惹眼。
跟著達渥部的人,很快出了城,城外接應的唐斗、邵子坤迎了上來,寶昕他們立即換裝,阿多選了近路,遠離阿愈陀。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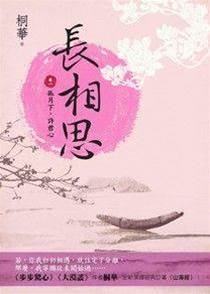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57 -
完結96 章

和冷硬將軍奉旨成婚後
新皇登基第二年,把他親姐趙明臻、驕奢淫逸的長公主,打包嫁給了泥腿子將軍燕渠。 一個是嬌貴的金枝玉葉,出門要坐轎、沐浴要牛乳;一個是草莽出身的糙人,餐風伴飲露、落牙和血吞。 衆人皆道不配,下注賭這對怨偶幾時分手的盤口開遍了賭莊。 衆說紛紜之際,長公主殿下大手一揮,拍下亮閃閃的一錠金,大放厥詞:“我賭三年。” “三年內,我一定把他踹了。” —— 她與燕渠的結親是利益權衡、是政治聯姻,趙明臻很清楚這一點。 新婚第一夜,她在喜牀上畫下楚河漢界。 “左邊是我的,右邊也是我的。” “那你畫個屁。” 新銳將軍翻了個白眼,自覺裹了個地鋪。 —— 新婚第三天,趙明臻勒令他簽下不平等契約。 “不許並肩、不許牽手、不許對視超過三秒……” 她勾着腳尖踢他:“籤不籤?不籤今天就離。” 燕大將軍磨了磨牙,哼了一聲,把“燕渠”二字簽得奇醜無比。 —— 新婚第三個月,趙明臻誤中迷香,拍着桌案大叫:“什麼男人還要本宮親自去睡?去,把他給我捆過來——” 被捆來的燕渠:…… —— 新婚第三年。 帳中,融融的燭影輕曳,趙明臻驀然驚覺什麼,朝面前男人蹬了一下。 肩寬腿長的燕渠半蹲在牀邊,眼疾手快地一把握住她溼漉漉的足踝。 “怎麼了?我的殿下,不是你要我給你洗腳?” 趙明臻神色一晃,有些彆扭地別開了目光。 ……放在三年前,她簡直無法想象。 威名赫赫、位極人臣的燕大將軍,會在溫暖的燭光下,目光柔和地爲她濯足。
30.2萬字8 146 -
完結412 章

大明:我朱允熥,隨機復活親人
老朱要立朱允炆?復活奶奶馬皇后,怒罵朱重八!呂氏以側妃上位?復活母親太子妃常氏,正位東宮! 朱元璋倚老賣老?復活朱五四,嚇得朱重八直呼親爹! 淮西勛貴不團結?復活外公開平王常遇春,整頓武勛! 朱允炆自稱嫡系?復活大哥朱雄英,我倆面前你老幾! 皇子們各有心思?復活太子朱標,都他麼是一群弟弟! 常氏:“我兒,有娘在,沒人可以欺負你!” 朱標:“允熥,給爹一個機會彌補虧欠吧?” 馬皇后:“天冷了,好孫兒,把這身龍袍穿上吧!” 朱五四:“允熥,我以太上皇的名義,求你當太孫吧!” 朱重八:“你跪下,爺爺求你件事,咱以后死了,你能把咱復活不?” ……
89.7萬字8.18 1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