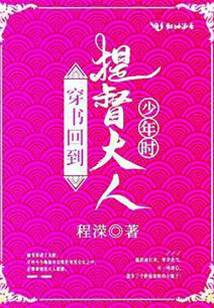《侯夫人與殺豬刀》 第145章 第 145 章
午后的明得有些刺眼,樊長玉仰著頭著坐在高墻上的陌上年郎,微微失神了一瞬。
聽得謝征的問話,又升起幾分心思被撞破的微窘。
落著一圈日輝的長睫小扇子似的撲閃了兩下,因為繞大理寺走了一圈,日頭又烈,白皙的面頰上也出幾分淡,其間細小的絨都清晰可見,卻負手于后做出一副穩沉模樣:“你怎在這里?”
謝征笑笑,從墻頭一躍跳了下去,正好落于樊長玉跟前:“在雁翅塔上看到有人繞著大理寺墻走,似想做賊,過來看看是何方小賊。”
聽著這調侃的話,樊長玉一只手不自覺握了拳,暗含警告地瞪向謝征,大有再拿說笑就武的意思。
謝征很懂見好就收,轉而問:“你想夜探大牢?”
樊長玉想到自己的計劃,四下瞥了一眼,哪怕確認了附近沒人,保險起見,還是靠近謝征兩步,湊近他耳邊低語道:“那個假冒俞淺淺的人,聽說后邊還要審,我怕供出隨元淮沒死,打算去劫獄。”
嗓音得極低,說話時清淺的吐息就噴灑在謝征耳廓,麻得像是有蟲子沿著耳際爬過。
謝征配合地微傾了下子聽樊長玉說話,面如常,耳尖卻已開始泛紅,背在后的一只手,指節也不自覺,似在強行忍耐什麼。
樊長玉半點不覺,說完了還抬起頭看謝征:“你覺得怎麼樣?”
如今在外人面前為了立威,慣會做一副冷臉了,可同親近的人說話,一雙澄澈明凈的大眼里還是著幾分老實的憨氣,像是胖貓一般在雪地里打滾的猛虎。
結合說的話,當真是又呆又兇。
謝征黑眸靜視著跟前這滿眼晶亮的,費了些力氣才將眸從微干的上移開,綁在手腕上的那條發帶似在發燙,殘存的那點理智勉強他理清了話中的意思。
Advertisement
他道:“劫走三司會審的朝廷重犯,你不怕被查?”
樊長玉一片坦的大眼眨了兩下:“要懷疑,不也應該懷疑到魏嚴頭上麼?兵法上管這……禍水東引!”
謝征沒忍住扯輕笑出聲,“你自創的兵法麼?”
樊長玉愣了一下,也是一時想不起來該管這計謀個什麼名字,才胡謅的,被謝征這麼一說,頓時生出幾分窘迫。
干咳兩聲道:“反正就這麼個意思。”
謝征背靠墻半垂著眸子,緩緩道:“大理寺外的守衛申時便接換崗,大牢守夜的獄卒只有十八人,但只要發現有人劫獄,值防的獄卒便會敲響金鐘,牢所有出口都會落鎖,牢外的兵也會里三層外三層圍一個鐵桶。”
樊長玉呆了一呆,頭疼地抓了一把頭發問:“意思就是,劫獄不了?”
謝征眼皮淺淺一:“劫。”
樊長玉:“……”
-
夜寒重,不知何傳來一兩聲犬吠,驚得枯樹枝頭寒飛起。
亮著兩盞昏黃燈籠的大理寺,在夜幕中好似一座靜靜聳立的墳塋。
大牢深的壁龕里著火把,松脂味兒混著大牢里經年不見日產生的霉味,飄散在空氣中,熏得人昏昏睡。
大理寺牢房呈“十”字形布局,每一個岔口進的都極深,往里約莫有二三十間牢房,四名獄卒分為兩人一組,便在這一條單道里來回巡視。
中間四條道□□匯,設了刑房和值守室,牢頭和副牢頭通常都是候在這里,便于接待前來牢里審訊犯人的大,若是有劫獄者,一旦聽到靜,也能及時敲響值守室的大鐘。
這一夜牢頭和副牢頭坐在方桌前,不知打了多個哈欠。
Advertisement
“不,我得去洗把冷水臉醒醒神。”副牢頭打著哈欠起。
牢頭撐著手肘也是昏昏睡,道:“給我也打盆水來,這嚴冬臘月里,可真容易犯困。”
副牢頭應了聲,便出去打水。
牢頭睡眼惺忪又打了個哈欠時,半睜眼間卻發現有一團高大的黑影籠罩了自己。
牢頭心中一凜,但還沒來得及回頭,便被一手刀砍在后頸,兩眼一黑徹底昏死過去。
兩名巡視走到岔道口的獄卒正要出聲,耳際似乎也有風聲近,隨即頸后一痛,趴趴倒地,約還有骨節錯位聲響起。
謝征打暈了牢頭,回首一看,便見樊長玉著一夜行,正蹲在地上給一名獄卒正骨。
面對他投去的不解的目,樊長玉尷尬道:“沒注意,下手重了點,把人肩膀給砍臼了。”
手臂接回去的剎那,劇痛讓獄卒轉醒,只是一聲痛呼都還沒來得及發出,就又被人一掌給拍暈過去了。
端著一盆冷水回來的副牢頭瞧見這一幕,驚得手中木盆掉落,張便要大呼有人劫獄,怎料立在牢頭邊的那名黑人,形有如鬼魅般瞬間近,以手為劍指在他間一點,腳尖再抵著下落的水盆往上一挑。
副牢頭只覺間一痛,歇斯底里大喊也再發不出任何聲音,而那險些掉落在地的水盆,也那黑人輕輕松松接住,就連顛簸浪出去的水,都被他一滴不剩地接回了盆里。
副牢頭心中大駭,拔還想跑,趕過去幫忙的樊長玉一個箭步躍起,肘關擊在他后頸,白眼一翻暈了過去。
樊長玉淺淺吐出一口濁氣,輕聲道:“最后一個。”
來這值守室前,們已從窗戶潛,劈昏了牢巡邏的其他獄卒。
Advertisement
謝征從牢頭上取出一串長短不一的鑰匙,說:“隨家人關押在甲九間。”
樊長玉跟著謝征往標了“甲”字跡號牌的牢房甬道走去。
夾道每隔數丈就有火把照明,們無需提燈。
隨元淮的妾室和獨子作為重要欽犯,被單獨關在了一間狹小的牢房。
牢房門上拴著的鐵索有嬰兒手臂,謝征只能挨個試那一大串試鑰匙,細微的鐵鏈響聲驚醒了旁邊大牢里關押的犯人。
只是他們都不敢出聲,因為不確定來的人是要殺他們的,還是要救他們的。
被單獨關押的那對母子,人比起樊長玉初見時,更蓬頭垢面了些,用力抱著自己懷中的孩子時,單薄的料繃,瘦得幾乎能看到后背凸出的骨節。
看著牢房外的謝征和樊長玉,眼底沒有希翼,只有驚恐,就連抱著孩子的手都在不住地發抖。
未免節外生枝,樊長玉也沒出聲,只在夾道前方替謝征放風。
怎料對面一間牢房里,一個頭發花白的老頭突然歇斯底里大喊:“劫獄啦——殺人啦——”
靠近牢房頂用來氣的幾個蛋大小圓孔,出一片攢的火,顯然老頭的聲讓大牢外的守衛聽到了。
謝征眸一冷,樊長玉也是瞬間張起來。
原本們靠著投放輕劑量的迷香,神不知鬼不覺打暈了大牢里的獄卒,時間是很充足的,現在因為那老頭的那一聲,整個大理寺的出口很快就會被圍起來了。
挨個試鑰匙的時間也不夠了。
樊長玉一咬牙,在謝征還在冷靜繼續試鑰匙時,沖過去道:“讓我來!”
嬰兒手臂的鐵索扯不斷,但是蠻力十足的幾腳踹在牢房的柱子上時,那幾拳頭的木柱還是被應聲踹斷了。
Advertisement
樊長玉仗著男形上的優勢,進去拎小仔似的,將牢里的人和那孩子兩手各拎一邊給拎了出去。
在牢房參差不齊的缺口,將那被嚇傻的小孩往謝征手上一塞,自己扛起那人沖謝征道:“快走!”
謝征看著被塞到自己手上的小崽子和樊長玉肩頭扛著的人,想說他去扛那人,但念及那人上只著一件單,到底還是沒出聲,只單手拎著那小孩跟著樊長玉快速往出口掠去。
那老頭看到樊長玉們劫走隨元淮的“妾室”,不知是真不知那對母子的假冒的,護主心切,還是因為別的,緒格外激,兩手攥著牢房的木柱,一直再大喊:“來人啊!劫囚啦——”
謝征眉頭微皺,在快離開時,朝后方投去冷冷一瞥。
-
大理寺外的守衛在聽到牢里傳出的呼救聲后,便一窩蜂往牢里趕,待進了大牢,發現獄卒都被放倒了,更是大呼不妙,徑直往關押隨家人的牢房走去,發現隨家下人和落網的部將一個沒,只是隨元淮的妾室不見了時,額角已是冷汗涔涔。
守衛頭子大喝:“守住所有出口,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給我找出來!”
可借著火把的芒,瞧見牢房那幾被徑直踹斷的不規則木柱時,心中不免還是驚駭。
此等神力,這劫獄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
白天勘測過地形,樊長玉扛著那人,很快就找到了防守最薄弱的那圍墻,形矯健翻了出去。
謝征提著孩子,隨其后躍了出去。
到了外邊,怕那人認路,樊長玉從懷里掏出一早就準備好的麻袋,直接給那口中塞了棉布的人兜頭套上了。
隨即又掏出一個小的遞給謝征,“給那孩子也套上。”
作之練,讓謝征微默了一息。最近轉碼嚴重,讓我們更有力,更新更快,麻煩你小手退出閱讀模式。謝謝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22 章

咬定卿卿不放松
這是聰慧貌美的元小娘子,一步步征服長安第一黃金單身漢,叫他從“愛搭不理”到“日日打臉”的故事。 元賜嫻夢見自己多年后被老皇帝賜死,成了塊橋石。 醒來記起為鞋底板所支配的恐懼,她決心尋個靠山。 經某幕僚“投其所好”四字指點,元賜嫻提筆揮墨,給未來新君帝師寫了首情詩示好。 陸時卿見詩吐血三升,怒闖元府閨房。 他教她投其所好,她竟以為他好詩文? 他好的分明是……! 閱讀指南:類唐架空,切勿考據。主言情,輔朝堂。
36.4萬字8.33 22384 -
完結2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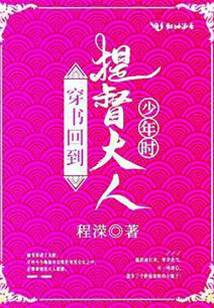
穿書回到提督大人少年時
她書穿成了女配,可憐兮兮地混在公堂的男男女女中,正等著知縣大人配婚。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按照劇情她注定是炮灰,超短命的那種。 她不認命,急切的視線在人堆裡可勁兒地扒拉,終於挖掘出他。 夭壽呦,感情這小哥哥,竟是男二! 連女主都無法覬覦的狠人! 這位爺有秀才功名在身,卻被至親算計,入宮成為殘缺不完整的太監。 他生生地熬過種種苦難,任御馬監掌印太監,最後成了人人敬畏的提督大人。 他曾顛沛流離,人人嫌惡,也曾位高權重,人人討好。 成為看盡人生百態,孑然一生的權宦。 但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壽終正寢! 只要她抱緊他的大腿兒,定能擺脫螞蝗般的至親,待日後做了大宦官之妻,更是吃香的喝辣的,還不用費勁巴拉的相夫教子。 小日子簡直不要太美好,撿大漏啊! 他一朝重生,再回少年時,尚未入宮,更未淨身。 眼下,他還是小三元的窮秀才,父暴斃而亡,母攜家資再嫁。 他浴血歸來,渾身戾氣,可一時善心,就多了個嬌嬌軟軟的小娘子! 說啥他這輩子也不淨身了,好好地考科舉,走舉業,給她掙個誥命夫人做,再生幾個小崽子玩玩兒……
44.7萬字8 23543 -
完結498 章
頂級綠茶的穿書攻略
萬蘇蘇,人送外號綠茶蘇,名副其實的黑綠茶一枚。她寫了一本虐文,傾盡茶藝寫出絕婊女二,不出所料,評論下都是滿滿的優美語句。她不以為恥,反以為傲。然鵝——她居然穿書了!!穿的不是女二,而是活著悲慘,死得凄慘的女主!!事已至此,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可,她卻發現逃不出原劇情,難道……她只能乖乖地順著原劇情發展了嗎?開局一巴掌,裝備全靠綠茶保命攻略,且看她如何靠著一己之力反轉劇情,走上人生巔峰。宴長鳴
89.8萬字8 7026 -
完結1654 章

神醫棄妃:邪王,別纏我!
別人穿越吃香的喝辣的,蘇半夏穿越卻成了南安王府裡滿臉爛疙瘩的廢柴下堂妻。吃不飽穿不暖,一睜眼全是暗箭,投毒,刺殺!冷麵夫君不寵,白蓮花妾室陷害。蘇半夏對天怒吼。「老娘好歹是二十一世紀最牛的解毒師,怎能受你們這窩囊氣。」從此,她的目標隻有一個,誰不讓她活,她就不讓那人好過!誰知半路上卻被個狂傲男人給盯上了?那日光景正好,某人將她抵在牆角,笑意邪魅。「又逢初春,是時候該改嫁了。」 ... 《神醫棄妃:邪王,別纏我!》是小容嬤嬤精心創作的女生,微風小說網實時更新神醫棄妃:邪王,別
171萬字8 977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