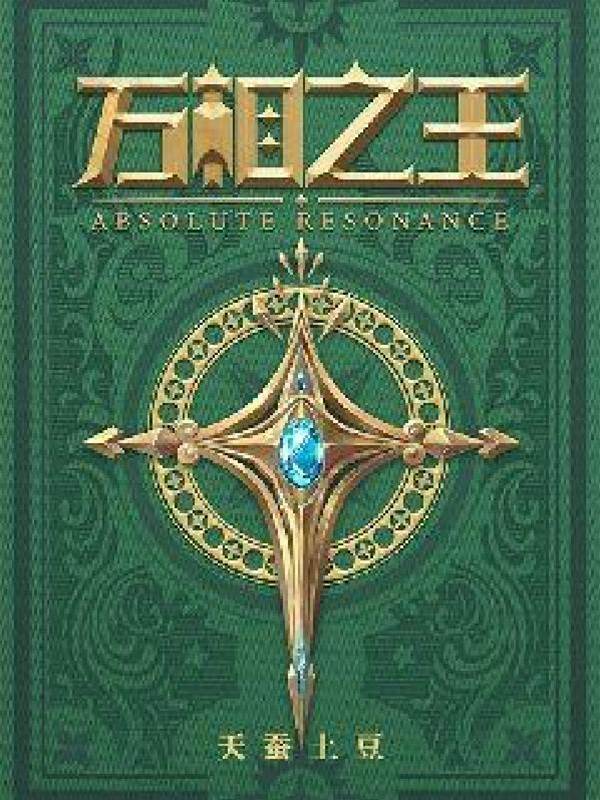《財神春花》 第 115 章 餐松飲澗
“方才,是你在說話嗎?”
年盯著春花,良久,搖了搖頭。
春花背上麻麻地起了一層皮疙瘩。
“你……從前見過我?”
年毫無表地搖了搖頭,看不出任何破綻。
“連啞都能聊上幾句,不愧是春花老板。”
紅道姑手持拂塵,含笑踏舍,聲音如玉魄般冰涼。
樂安真人看上去不過二十出頭,眉目間頗有剛毅堅韌之,貌而冷,令人心折。
“陳大掌柜的皮傷沒什麼大礙,但白猿掌上有些妖毒,還須以法力清理。如今妖毒已盡去,陳大掌柜稍后便會醒轉,春花老板可將他帶回去,好生休養。”
春花上前兩步,深深拜下:
“多謝樂安真人救了阿葛命。今日來得急切,未準備謝禮,稍后著人送來。長孫春花有恩必報,他日樂安真人但有差遣,盡管開口。”
樂安真人越過,在上方的太師椅坐了:
“春花老板大名如雷貫耳,能賣您一個人,也是樂安的幸事。”垂眸微微一笑,“不過,樂安只是投桃報李罷了,我表哥長思還托庇在你門下,多承照顧。”
春花一愣,倒沒想到,樂安真人和祝十還有這層關系。祝十份不為外人知,倘若泄,恐生事端。撇了一眼那不知真啞還是假啞的年,默然片刻,終是道:
“春花……不明白真人的意思。”
樂安真人笑了笑:“春花老板口風很嚴,這是好事。”順著目看向那年,了然道:“小啞,你且出去,我與春花老板有話說。”
小啞順地點了點頭。
樂安真人目送他出了門,才道:“這孩子是個啞兒,春花老板不必擔憂。”
倚在那伏羲投江的壁畫下,面目竟和畫上的伏羲有幾分相似,更添了詭異。春花心中不生出些不安。
Advertisement
“那孩子,真不會說話麼?”
“他從小就被我撿回來,養了好幾年。也曾請過大夫來看,都說是天生的廢嚨,救不得了。”
春花道:“真人是修道之人,難道沒有什麼法,能讓天喑之人開口?”
樂安真人不明白為何將話題轉到這上頭,微微有些不耐煩,但仍道:“法沒聽說過,倒是有一種人,名喚‘窨者’。”
“何為‘窨者’?”
“傳說是前世死得極為孤苦之人,心中有執念不肯去,便在地府求判放他下一世得償所愿。怨魂不喝孟婆湯,帶著前世記憶轉世投胎,出生便是奇丑無比、一世無親,口不能言,是為‘窨者’。‘窨者’一生只能說三句話,說完便死,但這三句話,都一定會真。”
春花面一暗:
“真人怎知那孩子不是‘窨者’?”
樂安真人微怔,旋即大笑:“‘窨者’只是個傳說,我從沒見過。何況抱執念轉世者,若不是有大仇要報,便是貪功名富貴。這孩子從未說過一句話,沒有殺過人,也沒有什麼功名富貴沾,怎麼可能是‘窨者’?這世上又丑又啞的苦孩子,多著呢。”
如此篤定,春花也不好再多言,又行了一禮,便要去看陳葛。
樂安真人卻住了:
“春花老板,恰逢這機緣,我有一事不明,還想請教。”
春花只得坐回去:“不敢言教,請真人示下。”
“百姓們都說你是……財神,不知這人間,是否真有財神?”
春花一愣。
“財神之說,純屬謬談。至于世上是不是有財神,我一個凡夫俗子,如何能知?”
“若世上真有財神,春花老板以為,應當是什麼樣子的?”
“若有財神,必然是要使世間錢財公平分配,多勞者多得,有智才者多得,不勞、不智,只占著天時地利盤剝他人者無所得。”
Advertisement
樂安真人以玉手支頤,眸中含笑:
“若財神有了私心,該怎麼辦?若財神自己占著天時地利,盤剝他人,又該怎麼辦?”
這幾個問題問得實在天馬行空,春花心中暗暗納罕,只得應付道:
“私心,自然會腐蝕公正。”
“哦?”樂安真人挑眉。
“但紅塵之中,誰沒有私心呢?所以,這人間,本不該有財神。”
樂安真人神一凜,似乎進了神游中,久久沒有說話。春花喚了一聲,仿佛從夢中驚醒,收起臉上的笑意,站起來。
“時候差不多了,陳大掌柜也該醒了,請隨我來。”
春花點點頭,跟在后出門。
樂安在門前站住,半側過:
“春花老板說得甚好。人間,本不該有財神。”
陳葛的傷勢確實不重,那白猿在他肩背上留下一個烏青手印和幾點刺傷,五臟六腑倒是無礙。
陳葛由小啞扶著坐起,春花隨著樂安真人踏房中,連忙喚他,他卻避開了春花的目,垂首不語。
“阿葛,你怎麼了?”春花手去他額頭,他卻猝然向后一,躲開了的。
樂安真人在一旁道:
“陳大掌柜中了妖毒,神還有些錯,認不出人也是有的。”
春花怔愣了一瞬。
樂安真人再道:“春花老板不必擔憂,接回去慢慢調養幾日,也就恢復了。”
春花點點頭,心道,回去還是要請羊大夫來瞧瞧。手要扶他起,陳葛向側一躲,險些摔跌,還是小啞眼明手快地將他扶起。
樂安真人嘆了一聲:“他不愿你,就讓小啞送他出去吧。”
回程的馬車上,陳葛將自己一個小團,遠遠地與春花各據馬車一角,春花無奈,只得與他拉開距離,問他許多話,他也不答,更不與他目接。
Advertisement
馬車停在長孫府門口,長孫石渠與長孫衡早收到了消息,一見這場面,立刻撲過來,一個“阿葛”,一個“舅舅”,把陳葛吵得面現痛苦,但那些驚懼的神,卻慢慢地消散了。
“別吵了,我頭疼。”他終于沙啞地開口。
一大一小把陳葛扶廂房中。陳葛卻并不排斥他們兩人的,神也恢復了正常。
春花微微心安,果然還是阿葛。
待要上前說話,陳葛卻又出閃躲之,直往長孫石渠背后。
石渠愣了一愣,沒心沒肺地笑道:“阿葛你怎麼了,這是春花,又不是洪水猛。”
春花收住了腳步,心中一沉。
阿葛不是不認得。分明是認出來了,卻又懼怕。
可是,阿葛有什麼理由要懼怕呢?區區一個弱子,連只都打不過。
羊大夫已候在府中,又將陳葛的傷勢重新檢視了一遍,確信外傷沒有大礙,神也沒有什麼問題,一切都如樂安真人所說。
春花將自己的疑說出,羊大夫道:
“大約真是了驚嚇吧。那白猿是個子,也許和你有幾分相像。”
春花不語了。
不是這樣的。樂安真人亦是子,但陳葛對并未流出恐懼之意。何況,陳葛向來張狂招搖,本不是個膽小的人。
不由得回憶起垂云觀的壁畫,那啞年,那一聲令人骨悚然的話語,還有樂安真人那貌似親切友善,實則暗藏鋒芒的笑容。
春花走出房門,喚過李俏兒:“咱們鏢局的老趙是京城的地頭蛇。你去找他查一查,京郊垂云觀的樂安真人,到底是什麼來頭,有什麼傳聞。”
李俏兒應了是,偏著頭笑嘻嘻道:
“東家,外頭有人找。”
Advertisement
春花一愣。
因為陳葛的事,兵荒馬地忙了這一日,此刻夜幕已是低垂,誰還會來找呢?
“東家忘了,今日本來是約了誰要出門?”
“啊呀!”春花一拍腦袋。
京城戲園子里新出了個生離死別的苦本子,今日本來約了談東樵去看戲的。看完了戲,兩人打算去瞧瞧剛買下的宅子,其中有些布置,還想問他的意見。
這下可好,又忘了個干凈。
急急沖進花廳,青瘦削的男子正襟危坐在堂下,慢條斯理地啜著茶,神中并無不耐或怒意。
“那個……談大人……”囁嚅地靠近。
談東樵挑起眉,放下茶盅。
“嗯?”
“事發突然,忘了遣人去告訴你一聲……”
“哦。”
“是我不對,你若不快,下回也照樣放我一回鴿子。”
談東樵莞爾失笑:
“我怎會不快?你家里出了事,我該及時察覺,過來幫你才對。只是……”
“怎麼?”
他幽幽地嘆了口氣。
“你我都是忙人,今后這樣的失約,恐怕是常事。”
春花撇:“怕什麼。今日不,約明日,總有一日能約上。既然喜歡了你這樣的人,等一等也無妨。”
談東樵神瞬間,輕輕挲頭頂:“我也是這樣想。”
春花綻出笑意,今日所的驚嚇和不安如云霧般裹著腳不沾地,此刻終于落到了實。緩緩手抱住眼前人的腰,將自己埋進他口。
“今天可真是漫長。”
談東樵將下擱在發心,低聲道:“今后遇上事,記得用鐲子喚我。”
春花仰頭:“沒遇上事呢?”
“……也隨時候命。”
將腦袋埋回他襟,吃吃笑起來。
談東樵有些無奈,嘆道:“老五混跡凡人,質卻終究異于常人,常有發怒失控之舉,所幸陳葛并無大礙。案子是老樊在審,侯櫻自述,因為陳葛打碎了釀多年的酒壇,才一時控制不住怒意。按律,斷妄司封丹三月,繳納些罰金賠付,關押十日。”
春花薄怒:
“阿葛的傷勢看起來不重,但我總怕有些后癥。”
“若后續發現其他的病癥,可將況告知斷妄司,依律重判。”
“……”
總覺得這罰太輕。但他既說按律如此,春花也不好再說什麼。
這是長孫家在京城酒業的第一宗收購,本該做得風面,卻遇上這麼個煮不蒸不爛的主,欺負到頭上來了。7K妏敩
律法能做的有限,卻不妨在律法之外,用些別的手段。汴陵的梁家,就是侯櫻的前車之鑒。
揮一揮頭,將心思沉回當下。
“談大人,今日去不戲園子,也看不宅子了,咱們改明日去?”
黑眸亮晶晶地著他,談東樵有些不忍:
“春花,對不住。”
“呃?”
“東南海上有惡蛟作,侵擾商船。陛下有旨,命我率人前往鎮,明日一早啟程。”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727 章
不死的我只好假扮血族
方誠被砍下腦袋。被刺穿了心臟。被塞了滿嘴大蒜。被拉到陽光下暴曬。被憤怒的仇敵碎屍萬段。方誠復活了,對仇敵們攤開雙手:“跟你們攤牌,其實我不是吸血鬼!”衆人怒吼:“我信你個鬼!”
187.7萬字8 10409 -
完結493 章
我無敵強者被係統騙了一百年
【魔幻、搞笑、無敵、迪化、係統、穿越】“我把你當係統,你竟然騙了我一百年,原來我不是小辣雞!”終於有一天,林奇發現他根本不是弱者之後,淚流滿麵。於是,在‘沙雕四人組’的帶領下,他出山了。但很快,林奇逐漸發現了不對勁。嗯?啥?我隻是想要搞點錢,吃個豬腳飯,我竟然去打仗去了?什麼?我要統治世界?我怎麼不知道?咦?這個世界有神!“各位神明大大聽我解釋,我冇想把你們拉下神位啊!”
95.3萬字8 9819 -
連載16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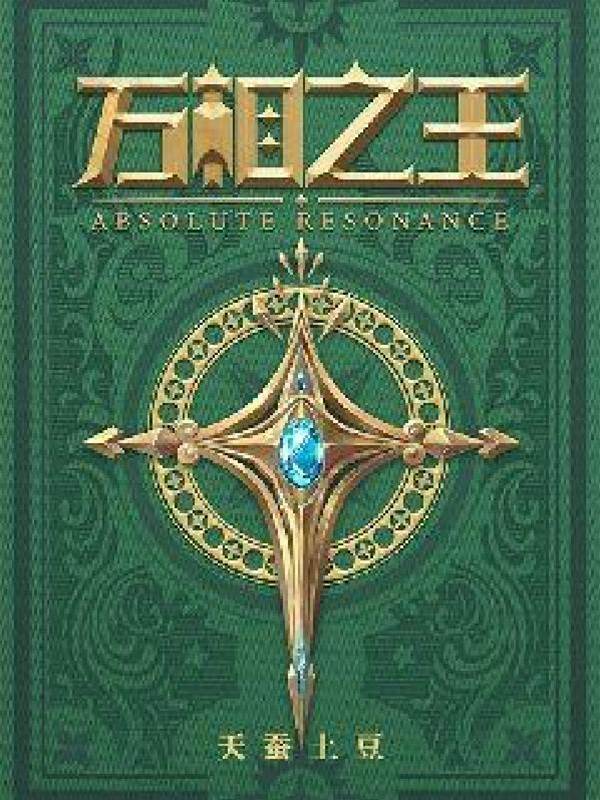
萬相之王
天地間,有萬相。而我李洛,終將成爲這萬相之王。繼《鬥破蒼穹》《武動乾坤》《大主宰》《元尊》之後,天蠶土豆又一部玄幻力作。
370.1萬字8.33 39208 -
連載1218 章

為美好的異世界獻上吐槽
【搞笑+輕松+吐槽】我,云舒,一個穿越者,喜愛和平,擅長吐槽!我的夢想是找一個上得了廳房下得了廚房的黑長直女神安穩的度過一生。但事實上,我除了被一個混蛋系統每日三頓嘲諷外,偶爾還會給我加個餐。于是為了不讓這貨嘲諷我,我開始踏上了成為世界最強的熱血道路。嘛......就當真的聽好了......反正我信了......
253.4萬字8 113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