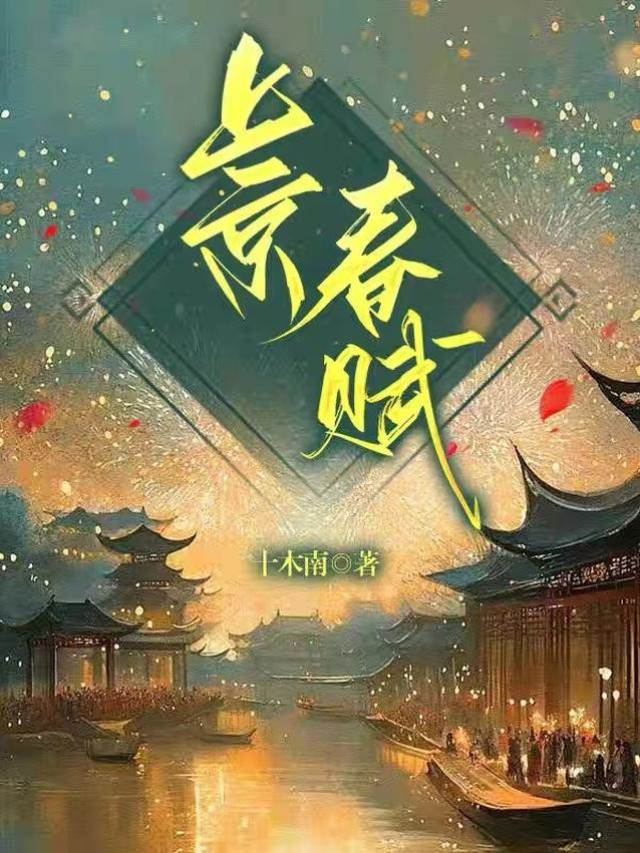《一妃動華京》 第二百四十三章 用刑
“哥哥?哥哥?”
莫久臣反復念著這兩個字煩的穆長縈頭都快炸了。不就是稱穆祥一聲哥哥,哪里注意到那時候莫久臣在旁邊。再者說,這聲哥哥明顯的怪氣,結合上面的對話,毫不親昵的好嗎?可偏偏莫久臣過來的時候沒聽到在這之前的所有話,唯獨聽到了一句“我等你哥哥”,這什麼事啊。
莫久臣把玩著手指上的扳指:“沒想到穆祥要為本王的大舅哥了。”
穆長縈不敢當連忙擺手:“王爺別鬧!沒你想的那麼復雜。”
莫久臣挑眉:“是嗎?”
穆長縈發誓:“絕對!我可以對天起誓,不然我——”
穆長縈看著花園里的滿地鮮花鄭重發誓道:“不然就要被蜂蟄!”
用了這麼大的力氣下決心莫久臣還以為穆長縈會發什麼毒誓。被蜂蟄都能被想出來,這小腦袋也不知道平時裝了什麼。
莫久臣揚袖假模假樣在穆長縈前掃了掃:“蜂不敢過來。”
穆長縈撲哧一聲笑了,雙手抱著莫久臣的手臂跟著他慢慢行走在花園中。
從琉瓔殿出來之后,穆長縈心里依舊在意白黎現在的境。莫久臣為了讓寬心提議陪走走,穆長縈已經很久沒有宮逛逛花園便欣然答應。天氣雖然炎熱但是黃昏之景甚好,穆長縈漸漸放松自己一直繃著的張,正在認真的欣賞經過的花枝,就聽到莫久臣一聲一聲“哥哥”的嘀咕個沒完,這才過來發誓。
穆長縈抱著莫久臣的手臂跟著他走小笑著說:“我這次可是聽的你話了。”
莫久臣說:“本王沒有發現。”
穆長縈不服氣:“阿亭都讓人去通知你了,我是得到你的準許才進宮的。”
Advertisement
莫久臣呵呵兩聲:“你已經到了宮門口,本王若是讓你回去免不了聽你的抱怨。”
他還是第一次在昭殿里到了什麼騎虎難下,這源頭竟然還是在宮門口。
穆長縈吐了一下舌頭,就是故意到宮門口才去請示莫久臣,知道莫久臣不會將趕回去,這樣不僅能夠大大方方的宮,還能有莫久臣的及時趕到。
就像現在。攝政王帶著攝政王府逛花園,周邊都是莫久臣的人,就連宮中的守軍和奴才都用不著。就算是要途徑此的其他人,知道花園里站著攝政王都離地遠遠的繞道而行。
這就給穆長縈提供了十分舒適的環境,既安全又無人打擾。
莫久臣帶著來到涼亭,涼亭下是一池湖水,湖水里的紅鯉游地怡然自得。
“說吧,你找穆祥又什麼歪腦筋?”
穆長縈笑了笑:“······”
還是沒躲過莫久臣的眼睛。
“我——”穆長縈心虛地看著湖水里的紅鯉:“這不是找穆祥救阿黎嘛。”
莫久臣抬手向后不遠的桃溪示意,桃溪退下。
“只要你想要救白黎,本王說句話就是。”莫久臣手扶著穆長縈坐下。
穆長縈依托著莫久臣的力氣坐下雙搭著長椅靠著朱漆紅柱:“是高謙庸將阿黎關在刑部大牢,你救阿黎就要與刑部打照面。我不想讓你現在和高謙庸爭執起來。”
莫久臣挑眉:“為何?”
穆長縈說:“因為高謙庸調查的是先皇之死。”
高謙庸將白黎帶走應該是察覺到白黎與莫帝之死有關系,若是或是莫久臣為救白黎奔走,那麼高謙庸便會將弒君的罪名丟在他們上。
以前的穆長縈無所謂,因為莫帝的死是的想法,大不了當北馳叛軍一輩子東躲西藏的度過。可是現在有孩子了,不可能讓的孩子為“罪人”的后代,跟著一直飽罵名。還有莫久臣。莫久臣可是掌控小皇帝要登基為帝的人,更不能沾惹到莫帝的死亡,事一旦被高謙庸有意為之的鬧大,這對莫久臣來說便是致命的打擊。
Advertisement
桃溪端著托盤走過來,高謙庸抬手拿過其中一個木碗,揚起里面的魚食落湖中。
“先皇駕崩之后太后一直在暗中調查,本王怠慢,太后找到高謙庸來調查,無可厚非。”
穆長縈疑地嗯了一聲:“你知道高謙庸在調查先帝之死的目的?”
莫久臣輕輕一笑:“本王還知道是高謙庸用真相來換太后手中的印。”
穆長縈皺眉說:“你怎麼什麼都知道?”
莫久臣又揚了一把魚食:“本王派去夢蘭殿的人可不僅僅是守衛。”
還有他在眼線,皇宮再大也逃不出他的監尉司耳目。穆長縈早該想到莫久臣的耳通八方,是想的不周全了。
“你就默認高謙庸調查?”問。
莫久臣說:“是本王調查不到,太后讓高謙庸行事屬是正常。調查先帝死因是太后唯一的執念,本王阻止不得。”
穆長縈心里嘆氣。莫久臣知道先皇之死與白黎有關,若是他直接告知太后真相,那便是直接將白黎以及白黎后的芳草閣還有穆長縈往死路里。莫久臣不在乎芳草閣,但是他在乎穆長縈。
“王爺。”穆長縈的手指摳著手心:“你應該會恨我吧。”
莫久臣出“為什麼這麼說”的表。
穆長縈抬頭說;“我恨先帝,雖然他不是死于我手,但確實是我的殺心。”
莫久臣輕笑一聲又揚了一把魚食:“為母報仇天經地義。本王是先帝胞弟,但是最主要的份是他的臣子。臣子看戲,是要站在之外縱觀全局。全局之中,他的罪過得以讓他有這般下場。”
心狠莫過于莫久臣。他就是喜歡將自己從局勢中摘出來,將整個局面看的清晰,最后算無策。穆長縈真想問問他,面對他自己的之局是否也看的如此清晰,不過在的經驗來看,即便莫久臣有失控的地方,還是能夠穩住局面及時,反反復復甚至樂此不疲。
Advertisement
神經!絕對神經!
莫久臣余看到穆長縈皺著眉眼不知道在想什麼,不過看一副在說壞話的表,就知道自己在心里又被罵了幾遍。
“給你。”
穆長縈抬頭就看見裝著魚食的木碗,看了一眼旁邊笑的桃溪,努了努。剛才就想問了,走的半年來桃溪還真是做了個合格的丫鬟,都能夠輕易的被莫久臣支使了。
莫久臣一擺手桃溪就知道退出去,莫久臣一抬手桃溪就知道去拿魚食。這默契使得穆長縈都開始懷疑小桃溪被莫久臣收買,為莫久臣在邊的小細了。
“我不喂魚。”穆長縈視線挪到湖邊,拒絕莫久臣的喂魚邀請。
莫久臣拿著木碗的手停在半空又遞了一下無奈道:“這不是魚食。”
穆長縈這才仔細看莫久臣手里的木碗,發現里面裝的竟是餞!裝魚食的碗則被放在自己的腳下。莫久臣什麼時候換的碗?不是!桃溪什麼時候還拿來了餞?為什麼裝魚食的碗要和裝餞的碗一樣?
莫久臣說:“你已經快兩個時辰沒吃東西了,不嗎?”
不說還好,一說還真有點。
穆長縈雙手接過來放在自己的肚皮上,向桃溪眨了一下眼睛夸贊準備的好,再一顆一顆的自己吃下去。
莫久臣看吃的開心自己也跟著歡愉,說話的時候語氣不自覺提高了一些。
“你讓穆祥去救白黎,可就是讓穆祥與高謙庸之間矛盾升級了。”
穆長縈吃著餞,含糊不清說:“升級就升級唄。”
莫久臣讓南舊亭和桃溪先退下,看到二人停在不遠守著涼亭,說:“他自認你的哥哥,現在把他供出去會讓高謙庸對他的份起疑。”
穆長縈想起剛剛穆祥對自己說的話,他說他真把當妹妹看想要真誠相待,不知道穆祥的話是真是假,他們是兄妹,可是互不了解,誰又能猜誰的心思。
Advertisement
穆長縈慢慢的將里的餞咽下說:“小皇帝的份快瞞不住了。”
莫久臣詫異。
穆長縈問:“你可否仔細看過小皇帝的長相?”
莫久臣說:“看過。像高家人,確切來說像他的舅舅高謙庸。”
穆長縈無可奈何地笑了:“是啊,眉宇間很像高謙庸。可是他笑起來有酒窩,淺淺的圓圓的,像極了我母親笑的時候。脈這東西還真是神奇,原來的我繼承幾分我母親的長相,可是特殊的樣子卻被的孫子給繼承了。等著小皇帝越長越大模樣日漸清晰后,這孩子可就藏不住了。”
莫久臣不以為然道:“能藏住。”
穆長縈;“嗯?”
莫久臣說:“人一死,就什麼都藏住了。”
穆長縈一口餞差點卡在嗓子里,嘖了一聲:“我的王爺啊,你不會要對一個小孩子置于死地吧。”
莫久臣輕輕拍著穆長縈的后背給順氣:“本王還沒想好怎麼置他,但是高謙庸定不會留他,還有高太后——”
穆長縈又是差點一個口氣沒有上來,拉莫久臣的袖:“高太后可是他親娘。”
莫久臣提醒:“也是一生最大的污點。”
-------------------------------------
白黎一污的從刑房被架回牢房癱倒在地上。
如高謙庸所說,被以鞭刑,全上下皆被用刑,唯獨雙手完好如初。這雙手救過無數人看似白皙,唯獨殺了一人后臟不耐看。白黎倒是希在的手指上用刑,時刻提醒枉為大夫。
牢房的一放著大大小小不同的藥瓶還有白黎的藥箱。這些都是高謙庸送來的,白黎每次刑之后,高謙庸都允許讓自己醫治傷痕,舊傷和新傷反復拉扯就如同生與死一樣反復折磨著白黎。
這是高謙庸的攻心之,讓白黎在自救和他亡之中不斷懷疑的初心與真誠,讓心甘愿說出真相。
白黎躺在地上一也不想,這些罪責都是該著的,再去醫治有多搞笑。醫者知道自己的外傷況,算著時間自己還能夠接多天的酷刑。不怕疼不怕死,就怕自己昏倒后胡言語,說出不該說的話。
上的傷痕還帶著余痛,每一道刺骨之刑都在提醒必須冷靜,死咬牙關。會承認是毒殺了莫帝,可是不是現在。穆長縈還懷著孩子,還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要生產,必須要堅過去,給充足安逸的準備。
想到這里,白黎緩緩從地上爬起,來到藥瓶和藥箱之前,需要活著必須活著。
-------------------------------------
刑部大牢里是什麼樣的況,南舊亭不知。但他知道高家人再給刑部大牢中源源不斷的送進治療外傷的藥品,能夠讓高謙庸親自派遣的任務,不用多想就知道是給白黎準備的。
莫久臣與高謙庸勢如水火,監尉司與刑部互為相互牽制的死敵。無法派人去探刑部大牢,正如穆長縈所說,莫久臣不敢直面面對刑部調查白黎的事件,以免惹火燒。
今夜穆長縈茶飯不思又是勉強吃了點飽腹的食,這樣下去對子無益。莫久臣不忍看這般,連夜來史臺員。
既然他不能直面面對高謙庸,那就屈尊降貴給穆祥打個配合,纏住高謙庸給他制造點時間。
次日早朝,眾人都嗅到了不一樣的氣味,因為平日里總是準時到朝堂的攝政王今日卻早早而到。當高太后帶著小皇帝上朝的時候都大吃一驚,在后面反復叮囑小皇帝千萬要神起來,不能打盹。
眾臣除了莫久臣和高謙庸外紛紛行禮,早朝便開始了。朝會剛剛開始,一本本的彈劾奏折鋪天蓋地的砸向瞪大眼睛想要趕走睡意的小皇帝。以史臺為首的眾員大肆彈劾地方水利員,彈劾他們中飽私囊私吞國庫白銀。
這些水利員好巧不巧都是高謙庸親自任命并且剛剛去任上就職不久,沒想到會被史臺抓住把柄,勢有將他們悉數定罪的意思。現在工部是華當寧做主,高謙庸從這里面帶自己的人已經非常不容易,現在面對此境遇打地他措手不及。
本來今天無事可做的華當寧一看事涉及到了工部,當下慵懶的樣子來了勁兒,不管他們怎麼鬧,他直接對著前面的高謙庸就是一陣吵,徹底將他拉戰局。
小皇帝嚇地都快哭了,憋著不敢讓眼淚掉下來,因為皇叔在底下看著他呢。母親說,皇叔要是盯著自己千萬不要逃走,一定要安安穩穩地坐在這。
莫久臣懶得聽后眾臣的爭論,毫無防備的時候還被華當寧一嗓子給嚇得一慫。可是他的視線始終盯著小皇帝,終于娃娃的臉上找到了特殊之。
這小家伙還真有又淺又圓的酒窩呀。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59 章

九歲嫡女要翻天
西涼威遠王府。 虎頭虎腦、年僅5歲的小王爺蕭沫希見自家娘親又扔下他跑到田野去了,包子臉皺得都鼓了起來。 小王爺哀怨的看了一眼身邊的爹爹,老氣橫秋道:「父王,你當初怎麼就看上了我那沒事就喜歡往外跑的娘親呢?」 蕭燁陽斜了一眼自家人小鬼大的兒子,隨即做出思考狀。 是呀,他怎麼就喜歡上了那個女人呢? 沉默半晌...... 「誰知道呢,腦子被門夾了吧」 同命相憐的父子兩對視了一眼,同時發出了一聲無奈嘆息。 攤上一個不著家的女人,怎麼辦? 自己的王妃(娘親),只能寵著唄! …… 身懷空間穿越古代的稻花,只想安安穩穩的在田野間過完這輩子,誰知竟有個當縣令的父親,於是被迫從鄉下進了城! 城裡的事多呀,為了在家有話語權,稻花買莊子、種花卉、種藥材,培育產量高、質量好的糧種,愣是輔助當了九年縣令的老爹一步步高升,讓寒門出身的顏家擠進了京城圈子! 這是一個寒門嫡女輔助家族興旺繁盛的奮鬥故事,也是一個相互成就、相伴成長的甜蜜愛情故事! 男主:在外人面前是桀驁的小王爺、霸道的威遠王,在女主面前,是慫慫的柔情郎。 女主:事事人間清醒,暖心又自強!
241萬字8.33 267043 -
完結98 章

給前夫的植物人爹爹沖喜
宋朝夕一觉醒来,穿成书里的同名女配,女配嫁给了世子爷容恒,风光无俩,直到容恒亲手取了她的心头血给双胞胎妹妹宋朝颜治病。她才知自己不过是个可怜又可笑的替身。奇怪的是,女配死后,女主抢走她的镯子,病弱之躯竟越变越美。女主代替姐姐成为世子夫人,既有美貌又有尊贵,快活肆意! 宋朝夕看着书里的剧情,怒了!凭什么过得这么憋屈?世子算什么?要嫁就嫁那个更大更强的!国公因为打仗变成了植物人?不怕的,她有精湛医术,还有粗大金手指。后来国公爷容璟一睁眼,竟然娶了个让人头疼的小娇妻!! 小娇妻身娇貌美,惯会撒娇歪缠,磨人得很,受世人敬仰的国公爷晚节不保…… PS:【女主穿书,嫁给前夫的是原著女主,不存在道德争议】 年龄差较大,前面女宠男,后面男宠女,互宠
50.2萬字8 21788 -
完結155 章
重生后成了皇叔的掌心寵
燕寧一直以為沈言卿愛慕自己才把自己娶進門,直到沈言卿一碗燕窩讓她送了命,她才恍然大悟,自己不是他的白月光,撐死了只是一顆米飯粒。沈言卿的白月光另有其人,清艷明媚,即將入主東宮。重頭來過,燕寧哭著撲進了楚王鳳懷南的懷里。鳳懷南做了三十年皇叔,神鬼皆俱無人敢親近他。僵硬地抱著嬌滴滴依戀過來的小丫頭,他黑著臉把沈家婚書拍在沈言卿的臉上。“瞎了你的狗眼!這是本王媳婦兒!”上一世,她死在他的馬前。這一世,他給她一世嬌寵。
79.5萬字8.18 65138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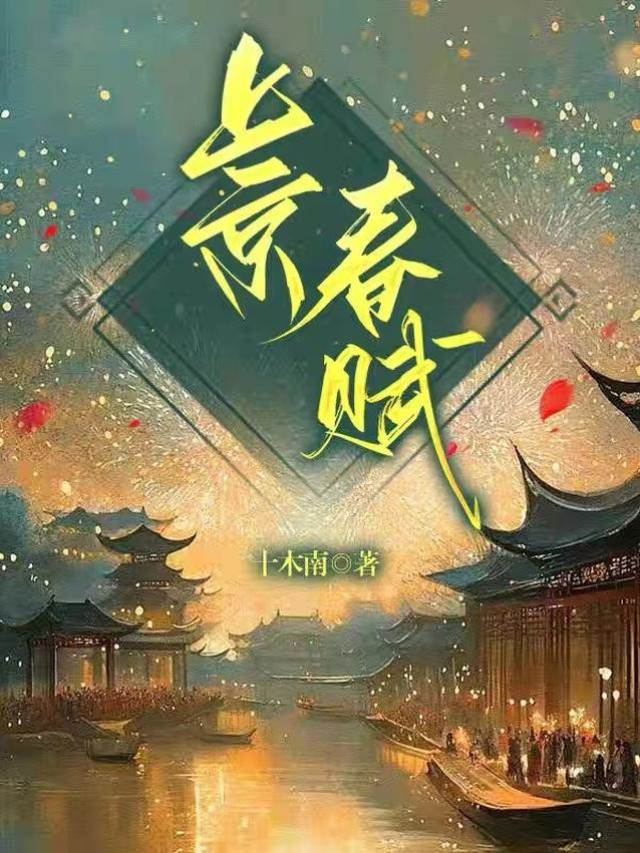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