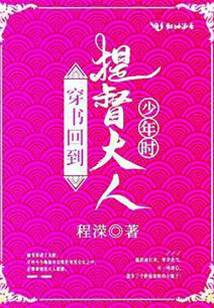《權相養妻日常》 172.震驚
一墻之隔, 范自鴻穿著極不起眼的灰布裳, 盤膝坐在靠窗的一座木床,神冷。
當日刺殺太子不, 他逃出東宮后, 便出京城而往河東。誰知韓蟄出手快, 錦司消息徑直從鐘樓以旗號遞出,在他逃到城門前,便在九門嚴盤查。
范自鴻逃不出去,在京城避了兩日, 費盡心思, 才混在運送皮的車中出京。
出了城門沒走多遠,便又被錦司的眼線盯上,若非范家死士拼死力救, 怕早已落網中,而他在京城能用的人手, 也在那次激戰后折損大半。
這一番較量,范自鴻當然看得出錦司是下死手要將他困住。
以錦司的兇悍,他即便帶著死士都未必能逃,何況邊能用的人已不多
北上的路實在兇險,若躲藏在別被錦司遇到,也是斬不斷的麻煩。
范自鴻滿心惱恨地斟酌許久, 決定到金州試試金州在京城之南, 錦司為了封住他, 人手往北邊調了不, 南邊防范不算太嚴。
更何況,金州還有韓蟄的岳丈傅家,傅家還有出山南的蔡氏。
范自鴻鋌而走險,找上蔡氏,給個藏之,蔡氏果然就范。而錦司各眼線也不敢來韓蟄的岳丈府外搜查攪擾,倒給了他暫時棲籌謀的空隙。
此刻,庫房里線昏暗,范自鴻盯著對面的婦人,笑了笑,眼神鷙。
“給河東的信遞出去了”
“遞出去了。”蔡氏不耐煩,“我幫你藏在此,又遞出求救的消息,已是仁至義盡。”
“仁至義盡夫人可真會說笑。”范自鴻冷笑,緩緩起,撣了撣上灰塵,“當日蔡了我多好,沒能幫我辦事,反蔡源濟喪了命。他如今裝得孝敬模樣安穩無事,若我潛往山南,將他當日跟你二叔那些勾當告訴令尊,夫人還仁至義盡嗎”
Advertisement
秋盡冬初,夜后格外寒涼。
蔡氏瞧著那雙毒的眼睛,忍不住打個寒噤。
蔡跟是一母所生,因蔡源中盛寵的生母,令蔡也生出爭寵之心,將嫡長的蔡穆排打出去,他從蔡源中手里多分些好。
奈何嫡庶畢竟不同,哪怕蔡源中一視同仁,旁人卻仍更尊蔡穆,扶持提攜,擁躉不。
蔡無計可施,正巧范家出招攬之意,便想借此機會放手一搏。
后來范自鴻潛山南時,特地將蔡源濟和蔡綁在一,蔡哪怕明知二叔的野心,卻也被范自鴻牢牢綁在賊船,難以,越陷越深。
蔡源中兄弟為奪權而爭殺鬩墻,元氣大傷,倘若范自鴻將蔡先前的所作所為抖出去,被蔡穆趁機推波助瀾,恐怕蔡源中盛怒之下,蔡再無立之地。
蔡氏怎忍心看親兄弟落那等境地
被范自鴻威脅迫,只能依從,不止安排他在庫房藏,讓親信的老仆每日送飯食,還借著傅家的掩護將范自鴻的書信寄往河東,神不知鬼不覺。
但這顯然是極危險的事。
范通起兵謀逆,范家闔府被查抄,范自鴻已是逆犯之。傅家正辦喪事,來吊唁的人一波接著一波,令容又帶了韓家的人過來,這兩日提心吊膽,生恐泄。偏偏范自鴻急,連著老仆遞了數道口信給,催命似的要來見。
蔡氏怕事泄,才趁此夜之時,借口游園散心過來。
藏在袖中的手凍得冰涼,下意識握拇指大小的信,盯著范自鴻。
范自鴻亦打量,沉聲道:“回信呢河東離金州不遠,夫人前日就該收到了。”
蔡氏眉心一跳,道:“確實是前日送到,因喪事里賓客太多,才拖延至今。”
Advertisement
“夫人盡可派人送來,拖延什麼”
“旁人送來,有些話說不清楚。這回藏著你,我瞞了傅府上下所有人,算是保住了你命。此事之后,瓜葛兩清。你須答允,不可再尋我兄長的麻煩。”蔡氏畢竟是個流,退后半步,神提防,“你藏在傅家的事,也不許向旁人。”
范自鴻笑了笑,沒回答,只問道:“回信呢”
片刻安靜,風聲都停了,唯有黑暗籠罩。
他追著蔡氏,站得離窗邊更近,盯蔡氏之余,忽然聽見窗外似有旁人。
范自鴻心中一,神不變,手臂倏然出,輕輕扼住蔡氏脖頸,另一只手捂住口鼻,拿眼神著蔡氏往窗邊走,口中仍是波瀾不驚地道:“答應你就是,回信呢”
他手指力道不大,但眼神兇狠,似無所顧忌。
蔡氏心驚膽戰,怕范自鴻真的下殺手,既然話已說明白,便將那回信取出。
范自鴻劈手奪過,仍扼著蔡氏脖頸,將回信拆開瞧罷,隨口道:“多謝了。”說話之間,目卻已看向窗外。隔著窗扇,外頭也是一片漆黑,看不清人影,只聽得到那極低的呼吸聲,似頗慌。
蔡氏看出端倪,怕事泄為人所知,也吊著一顆心,道:“但愿范將軍能說到做到。”
屋外,令容雙手捂著口鼻,生恐泄半點靜。
方才會跟過來,是因有飛在旁,哪怕見麻煩也不必害怕。誰知靠在窗邊一聽,里頭藏的竟會是范自鴻
錦司為追捕范自鴻費了太多力氣,令容單是瞧著韓蟄提及范自鴻時皺眉的模樣,便知事頗為棘手。
本以為是范家神通廣大,卻原來是蔡氏從中作祟
私藏逆犯是重罪,更可恨是范自鴻這種人。蔡氏仗著蔡家的軍權無所畏懼,靖寧伯府卻只有傅益撐著。韓鏡本就滿腔偏見,倘若得知是傅家行事不端連累大事,豈不震怒屆時哪怕韓蟄力保,怕也困難重重。
Advertisement
令容震驚之余,忍不住想聽個究竟,推測出再悄悄逃走,好給韓蟄遞消息。
哪料屋里兩人說著說著,竟往窗戶邊靠過來
此時再逃,那靜必然會驚擾范自鴻。飛的本事能對付旁的賊人,跟范自鴻比起來仍遜許多,不敢冒險,加之旁邊有雜書草,蹲時難免鬧出靜,便只能背靠漆柱,飛小心提防。
屋里兩人的聲音低了下去,夜愈來愈暗,周遭安靜得駭人。
令容心里咚咚直跳,聽到蔡氏道別的聲音,繃的神經稍稍松懈,打算等范自鴻走遠再悄悄逃走。
掌心的汗意被風吹得微涼,里頭安靜了半晌沒靜,想必是范自鴻已走遠。
令容躡手躡腳地往旁邊挪,猛聽耳畔一聲悶響,窗扇開之,有個黑影如虎豹般撲出來,迅捷之極。
嚇得一聲低呼,時刻警惕的飛揮臂阻攔,卻被范自鴻重拳搗在口。
在窗邊屏住呼吸站了半天,隔著極近的距離,從外頭挪步的靜,范自鴻能斷定兩人去勢。這一招蓄勢已久,又狠又準,鐵錘般砸在飛口,令腔劇痛,攻勢也為之一緩。
范自鴻勢如虎狼,不待飛息,揮拳疾攻。
飛與飛鸞姐妹合力都難敵他,如今被重創,更難抵擋。
范自鴻怕招來旁人,出手格外兇狠,拼著被飛踢中,亦飛腳踢在飛上。人的子骨如何得住他瘋虎般的重擊
飛忍痛連連后退,范自鴻則撲向正打算人的令容,一手如鐵鉗扣在肩膀,一手牢牢捂住。
激戰只在片刻之間,令容的呼救聲才到一半,便盡數被捂回里。
肩膀的筋被范自鴻按著,酸麻無力,試圖掙扎,卻覺間一涼,有銳抵過來。
Advertisement
令容不用猜都知道那是什麼,保命要,霎時安靜下來。
范自鴻借著昏暗夜一瞧,看出是令容的臉龐,驚愕之余,霎時想起韓蟄種種惡行。仇人相見分外眼紅,范自鴻亡命之徒般東躲西藏、吃了不苦頭,一見令容,眼底陡然出兇,似出手重傷。
令容嚇得大,聲音被捂得含糊,“慢著”說話間竭力往側面。
飛怕范自鴻狗急跳墻,也沒敢擅,只死死盯著,急道:“別傷”
范自鴻作微頓,仍將匕首抵著令容脖頸,道:“我原想暗中離開,不驚擾尊府,是夫人自投羅網,撞到我手里。夫人想必知道輕重,哪怕你韓蟄過來,這一刀下去,你也休想活命。”
“我知道,不會出聲。”令容嚇得聲音抖,心里迅速權衡。
以范自鴻方才出手的迅捷,想必是全須全尾,并未負傷。傅家雖有帶來的護衛,卻無人能敵得過范自鴻。且范家謀逆,范自鴻已是亡命之徒,不擇手段,一旦事鬧得太大,激起范自鴻兇,這小命必然保不住。
且范自鴻是逆賊之子,這回雖是蔡氏私藏,卻是在傅家地盤。若鬧出靜,此事必定為外人所知,屆時傅家這窩藏逆犯的罪名便難推卸。
為今之計,唯有先住此事,拖延保命,再伺機自救。
無長,范自鴻為躲錦司的追捕藏在此
電火石之間,令容忽然想起了當初的長孫敬。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22 章

咬定卿卿不放松
這是聰慧貌美的元小娘子,一步步征服長安第一黃金單身漢,叫他從“愛搭不理”到“日日打臉”的故事。 元賜嫻夢見自己多年后被老皇帝賜死,成了塊橋石。 醒來記起為鞋底板所支配的恐懼,她決心尋個靠山。 經某幕僚“投其所好”四字指點,元賜嫻提筆揮墨,給未來新君帝師寫了首情詩示好。 陸時卿見詩吐血三升,怒闖元府閨房。 他教她投其所好,她竟以為他好詩文? 他好的分明是……! 閱讀指南:類唐架空,切勿考據。主言情,輔朝堂。
36.4萬字8.33 22384 -
完結2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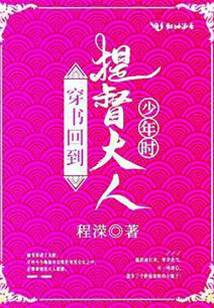
穿書回到提督大人少年時
她書穿成了女配,可憐兮兮地混在公堂的男男女女中,正等著知縣大人配婚。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按照劇情她注定是炮灰,超短命的那種。 她不認命,急切的視線在人堆裡可勁兒地扒拉,終於挖掘出他。 夭壽呦,感情這小哥哥,竟是男二! 連女主都無法覬覦的狠人! 這位爺有秀才功名在身,卻被至親算計,入宮成為殘缺不完整的太監。 他生生地熬過種種苦難,任御馬監掌印太監,最後成了人人敬畏的提督大人。 他曾顛沛流離,人人嫌惡,也曾位高權重,人人討好。 成為看盡人生百態,孑然一生的權宦。 但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壽終正寢! 只要她抱緊他的大腿兒,定能擺脫螞蝗般的至親,待日後做了大宦官之妻,更是吃香的喝辣的,還不用費勁巴拉的相夫教子。 小日子簡直不要太美好,撿大漏啊! 他一朝重生,再回少年時,尚未入宮,更未淨身。 眼下,他還是小三元的窮秀才,父暴斃而亡,母攜家資再嫁。 他浴血歸來,渾身戾氣,可一時善心,就多了個嬌嬌軟軟的小娘子! 說啥他這輩子也不淨身了,好好地考科舉,走舉業,給她掙個誥命夫人做,再生幾個小崽子玩玩兒……
44.7萬字8 23543 -
完結498 章
頂級綠茶的穿書攻略
萬蘇蘇,人送外號綠茶蘇,名副其實的黑綠茶一枚。她寫了一本虐文,傾盡茶藝寫出絕婊女二,不出所料,評論下都是滿滿的優美語句。她不以為恥,反以為傲。然鵝——她居然穿書了!!穿的不是女二,而是活著悲慘,死得凄慘的女主!!事已至此,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可,她卻發現逃不出原劇情,難道……她只能乖乖地順著原劇情發展了嗎?開局一巴掌,裝備全靠綠茶保命攻略,且看她如何靠著一己之力反轉劇情,走上人生巔峰。宴長鳴
89.8萬字8 7026 -
完結1654 章

神醫棄妃:邪王,別纏我!
別人穿越吃香的喝辣的,蘇半夏穿越卻成了南安王府裡滿臉爛疙瘩的廢柴下堂妻。吃不飽穿不暖,一睜眼全是暗箭,投毒,刺殺!冷麵夫君不寵,白蓮花妾室陷害。蘇半夏對天怒吼。「老娘好歹是二十一世紀最牛的解毒師,怎能受你們這窩囊氣。」從此,她的目標隻有一個,誰不讓她活,她就不讓那人好過!誰知半路上卻被個狂傲男人給盯上了?那日光景正好,某人將她抵在牆角,笑意邪魅。「又逢初春,是時候該改嫁了。」 ... 《神醫棄妃:邪王,別纏我!》是小容嬤嬤精心創作的女生,微風小說網實時更新神醫棄妃:邪王,別
171萬字8 977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