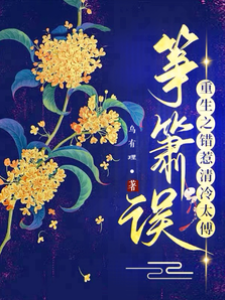《立后前一天狗皇帝失憶了》 第58章 第58章
宮婢手將殿門推開,恭敬不失禮數:“姑娘,請吧。”
斜余輝自后映殿中,因為背著的緣故,打眼一看里面很是暗,花想容的心底莫名升起幾分不安,之前因著周璟的話,太后本打算讓明日就出宮回花府的,只是不知道現在忽然過來,有什麼事,試探問道:“姑母……太后娘娘召見我有什麼事嗎?”
宮婢眼觀鼻鼻觀心,道:“奴婢也不知。”
花想容定了定神,謹慎地了殿門,只見太后如往常一般坐在榻上,向招手:“容容,過來。”
不知是不是花想容多想了,總覺得對方語氣有些古怪,盡管如此,還是緩步上前,向太后行禮,怯怯問道:“姑母侄來,有什麼事嗎?”
太后讓人賜座,花想容挨著繡凳邊沿坐了,一抬頭就對上了太后的視線,那種目與其說打量,倒不如說是審視。
久居上位,花想容被看得有些心慌,垂下頭去,爾后便聽太后笑了一聲,道:“也沒什麼,只是想著你明日要回府了,哀家心里舍不得,想和你好好說一說話。”
端著茶盞,姿態十分優雅,吹了吹浮沫,和悅地道:“哀家這些侄兒里面,就數你最懂事,也甜,從前還想著,若是你來做哀家的兒媳婦,真是再好不過了,然而世事無常,可見咱們還是沒這個緣分。”
花想容的心略微放下來些許,聲音道:“姑母還是容容的姑母,往后姑母若是有什麼事,覺得寂寞了,隨時可以容容宮來,陪您說話解悶。”
太后笑了,著花想容,打趣道:“真是個心的孩子,不如就把你長長久久地留在哀家邊算了。”
Advertisement
這話的意思再明顯不過了,花想容的心砰砰跳起來,垂下頭道:“容容畢竟是、是外眷,皇上也說了,不好久留宮中,恐怕要姑母失了……”
“是呀,”太后慢騰騰地把茶盞放下,意有所指道:“畢竟是外人。”
的語氣變了,花想容一怔,接著便聽太后道:“哀家有件事一直想問個清楚,好孩子,你和哀家說句實話。”
那雙向來慈和的眼變得有些銳利,盯著花想容的表,道:“當初那一枝白玉簪子,是璟兒親手送給你的嗎?”
花想容沒料到突然提起這個,神微變,有些慌張道:“是、是啊,姑母怎麼突然問起這個?”
“這就奇怪了,”太后輕輕搭著扶手,天將上面的翡翠佛珠映得晶亮,折出冷冷的,蹙著眉,輕悠悠地道:“皇上說,他從沒喜歡過你,也沒送過你白玉簪,這和你從前跟哀家說過的話,不太一樣啊。”
像是真真切切地疑,看見花想容神巨變,太后的眼神犀利,道:“這件事究竟是你在說謊,還是皇上說謊呢?哀家都迷糊了。”
然而真正答案如何,其實心中早有定數,所以今天才了花想容過來問話,想通這些,花想容已是四肢冰涼,惶恐不已,立即起跪下,連連道:“姑母,對不起姑母,是我撒了謊。”
說著哭紅了眼眶,膝行至太后面前,抱住的,哽咽著道:“我只是太喜歡璟哥哥了,想嫁給他做妻子,可他不喜歡我,我沒有辦法……”
哭得楚楚可憐,聲道:“那時候娘親和祖母們又商量,說璟哥哥有可能會做皇帝,若是能娶花家兒做妻子,就、就再好不過了,我一時鬼迷心竅,騙了姑母……對不起姑母……”
Advertisement
太后握著圈椅扶手,低頭看著,半晌沒有說話,消息是出去的,是先帝的枕邊人,先帝屬意誰,早就猜到了,故而告訴了娘家,可沒想過自己會被一個小輩騙得團團轉。
比起花想容冒充周璟的心上人,一向疼的侄欺騙自己這件事更令太后失。
這麼多年,從沒疑心過花想容,還每每為惋惜,現在想來,簡直是荒謬!
花想容抱著太后的雙痛哭流涕,看起來十分悔恨,甚至道:“后來侄屢次想對姑母開口道明,可卻又怕姑母失,厭棄于我,便一直不敢說,如今侄過得不好,想來也是命中的報應……不敢奢求姑母的原諒,侄這次離宮之后,就自己去庵子里頭住,余生誦經拜佛謝罪,再不敢來惹姑母的嫌棄。”
太后見哭得這樣凄慘,有些恨鐵不鋼,道:“你真是糊涂,這種事哪里瞞得過呢?”
可是一想,還真的瞞了整整三年,若不是今日周璟親自來問,太后仍舊被蒙在鼓里,以為周璟念念不忘的人就是花想容。
思及此,太后忽然想起什麼,問道:“那簪子既然不是璟兒送你的,又是從何得來?”
花想容了一把眼淚,小聲道:“撿、撿的……”
太后搖首,居高臨下地看著,像在看一個孩子拙劣的謊言:“不對,你若是撿來的,戴著它招搖過市,璟兒看見,必會向你討要,你是從哪里來的?”
這個字刺痛了花想容,瑟了一下,才急急解釋道:“真的是撿的,是、是花五掉的……”
閉了閉眼,臉蒼白,哆嗦著道:“簪子……是花嫵的,我、我騙了璟哥哥,說簪子是花嫵不要,送給我了。”
Advertisement
太后吃驚:“你這樣說,豈不是壞了他們的分?”
花想容不住搖首,流著淚,抱住太后的求道:“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一時鬼迷心竅,姑母,求你別讓璟哥哥知道,他知道了我一定會沒命的!”
畢竟是自己一向疼的侄,這般哀求不止,太后到底心了,重重嘆了一口氣,道:“罷了,事已至此,如今也只能這樣了,你明日回府,往后無事不要宮,免得皇上看見你再想起來什麼。”
花想容臉陡然一白,咬了咬,低聲道:“是,多謝姑母,侄明白,往后再不給姑母添麻煩了。”
……
綠珠捧著一個朱漆雕花的描金托盤在宮道上匆匆行走,眼看天了黑,加快了步子,途徑春寧門時,聽見一個子聲音向人問道:“那個……請問坤寧宮往哪邊走?”
綠珠下意識轉頭看了一眼,天有些暗,只約看見那人穿著一碧的裳,大概是哪個宮的宮婢,新來的吧?連坤寧宮都不會走。
問的那個小太監答道:“順著這條一直走到頭,左轉再右轉,就是坤寧門,你腳程快些,一會該下鎖了。”
他說著,看見綠珠,哎了一聲,連忙笑道:“綠珠姐姐這是要回去吶?”
小太監指著那個婢道:“巧得很,這個姐姐說要去坤寧宮,找不著路,有勞姐姐捎一程。”
綠珠住了步子,上下打量那婢,有些躲閃,形容儀態總有一小家子氣,不太像宮中的人,綠珠起了疑心,問道:“你去坤寧宮辦什麼差?”
那婢忙道:“沒什麼,我、我就是隨便問問。”
這就更奇怪了,綠珠沒再追問,還要趕著回去,沒工夫在這里逗留,于是打了個招呼自己走了,沒走多遠,忽然回頭看了一眼,見那婢竟然跟在后,一副鬼祟的樣子。
Advertisement
桌案上擺著一個白瓷的碟子,里面盛滿了細小的珍珠,潔白圓潤,皆是上品,花嫵用線穿起來一粒,看它骨碌碌滾下去,落在桌上,發出輕響。
綠珠從殿外進來,道:“主子,奴婢方才遇到一個很可疑的人,鬼鬼祟祟地打聽咱們坤寧宮。”
花嫵低著眉眼,認真地串珍珠,隨口道:“怎麼個鬼祟法?”
綠珠道:“就是……閃爍其詞,問做什麼也不肯開口,還說要見您,真是好大的膽子。”
“見我?”花嫵抬起頭,笑了:“讓進來,問一問。”
綠珠去了,不多時,兩個年輕力壯的太監把一個婢推搡了進來,穿著淺碧的衫子,不是宮中的樣式,花嫵看了一眼,略微訝異:“原來是你?”
綠珠看了看那形容瑟的婢,遲疑道:“娘娘認得?”
花嫵道:“認得,花想容的人。”
慢條斯理地串著珍珠,一邊道:“聽說你要見本宮,怎麼,是花想容有事?”
出乎意料的,那婢小聲道:“不、不是。”
像是十分害怕,卻又強自給自己壯膽一般,了背,道:“奴婢是自己來見皇后娘娘的,求、求娘娘救命!”
明月說著,往地上重重磕了一個頭,那頭磕得很實在,砰的一聲,聽得綠珠腦門都疼了,花嫵這次是真的訝異了:“救命?救誰的命?”
“奴婢的命,”明月頓了頓,語出驚人道:“也是救娘娘的命!”
“放肆!”綠珠斥道:“咱們娘娘好著呢!”
花嫵擺了擺手,對手里的珠串徹底沒興趣了,饒有興致地看著那個婢,道:“你詳細說說,發生了什麼事,本宮才好知道怎麼救你我的命啊。”
明月見信了,心中大定,急忙道:“是小姐,小姐要害您。”
這個花嫵半點不意外,托著腮問道:“怎麼害本宮?刺殺嗎?”
明月連連搖頭,四下看了看,小聲道:“是、是蠱。”
這話一出,眾人皆驚,明月繼續道:“從前在晉北遇到一個方士,跟他學了蠱,那蠱十分厲害,真的能咒死人的。”
花嫵聽罷,十分好奇道:“咒死過誰?”
明月答道:“把姑爺咒死了,因為常老夫人待嚴苛,也下了咒,姑爺去后,老夫人也病倒了,沒心思管,才借口回了京師。”
花嫵覺得匪夷所思:“你怎麼知道人是咒死的呢?聽說那個夫君弱多病,興許是自己病死的也未可知。”
明月急急道:“肯定是咒死的,奴婢親眼所見,小姐用銀針刺心法,刺那個小人的心口,而姑爺死的那一天,也一直在喊心口疼,在床上直打滾,他是活活疼死的,死后心口還有一個小點兒,千真萬確。”
這話聽得人骨悚然,綠珠渾都起了皮疙瘩,想起了什麼,驚道:“你方才說,還要害咱們娘娘?!”
“是,”明月道:“用皇后娘娘的和生辰八字,就能下咒。”
花嫵想起早上自己在慈寧宮的傷,恍然大悟,道:“本宮當時還想,慈寧宮的下人怎麼那般疏忽大意,原來是這麼回事兒。”
還以為是太后看不順眼,故意折騰呢。
綠珠急道:“那不是已經拿到娘娘的了麼?都是奴婢的錯,不該把那帕子給別人的。”
明月有些心虛:“是……是奴婢拿走的。”
“你!”綠珠瞪:“你們好大的膽子!”
“只需要本宮的生辰八字和,就能下咒?”花嫵黛眉微挑,道:“這也太輕率了些。”
明月急忙道:“還有,要把那個下咒的娃娃按照五行風水,埋在一個地方,這地方應當距離娘娘的住不遠,這三者缺一不可。”
花嫵聽了,忽然看了一眼,道:“咒的,跟你也沒什麼干系,你為什麼要背叛,反過來告訴我呢?”
明月有些張,聲道:“在皇宮里埋東西,還要據五行風水,太危險了,小姐不會自己去的,肯定指使奴婢去,前面咒姑爺和老夫人的時候,也都是迫使奴婢去的,手里有奴婢的生辰八字,奴婢不敢不聽,可、可這次實在太……奴婢心里害怕,求娘娘救命!”
說著又磕起頭來,十分用力,綠珠都聽得有些不忍心了,看向花嫵道:“娘娘,這個人太惡毒了,咱們去告訴太后和皇上吧?”
誰知花嫵面上若有所思,片刻后,道:“不急。”
看向明月,道:“花想容會把東西給你去埋?”
明月點點頭,不安道:“從前都是給奴婢的。”
“什麼時候?”
明月想了想,道:“還不知道皇后娘娘的生辰八字,說要回府問一問老夫人,但是中秋宴,可能會宮,如果小姐順利拿到了生辰八字,就是中秋宴那一天了。”
花嫵聽了,喚來綠珠,附耳叮囑幾句,綠珠點頭,去而復返,手里拿了一個小香袋,遞給明月,花嫵輕聲道:“中秋宴那一天,本宮會借太后的名義,邀花想容宮,一定會來,你將那娃娃調換一下,把這個香袋放進去,生辰八字麼,也改一改。”
明月攥住那個香袋,像是抓住了自己的救命稻草,趁夜離開了坤寧宮,綠珠親自送回去,半道上叮囑道:“你只要聽咱們娘娘的話,就一定會保你命,可別什麼歪腦筋。”
明月連忙點頭,苦笑著道:“姐姐,我家命都系在娘娘上了,怎麼敢歪腦筋?”
綠珠不語,還是對明月之前了花嫵的帕子耿耿于懷。
眼看慈寧門近在前面了,綠珠順勢停了步子,道:“就送你到這里了,我不方便過去,你自己回去吧。”
說完,轉就走了,借著廊廡上的燈籠,明月低頭看了看手中的香袋,料子是鵝黃|的,質地上佳,最奇怪的是,上面繡的不是花也不是草,而是一個憨態可掬的狗頭,兩只三角形的大耳朵,吐著舌頭,栩栩如生。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30 章

傾世妖妃:纏上精分九千歲
他,是權傾朝野的東廠九千歲,忍辱負重,只為報滅國之仇。 她,是離府煞星轉世,身懷奇絕黃金瞳。 他滅她滿門,她害死他心上人, 他強娶她為妻,她誓要讓他失去一切! 他恨不得她死,她恨不得他生不如死! 這兩人恨透彼此,卻又一起聯手屢破奇案。 她的黃金瞳可以看透世間萬物,獨獨看不透一個他。 他對天下皆可心狠手辣,唯獨一次次欺騙自己不忍殺她!
92.7萬字8 15298 -
完結135 章
無上帝寵
【暫定每天中午十二點更新,如有變化作話、文案另行告知~】《無上帝寵》簡介:京城第一美人烏雪昭,膚如雪,眉如畫。她性子雖嫻靜,不動聲色間卻能勾魂奪魄,媚態天成。只可惜意外被男人破了身子。養妹烏婉瑩聽到流言十分心疼,從夫家趕過來安慰:“姐姐,你別擔心,我挑剩下的男人里,興許還有肯娶你的。”外頭人也一樣,都等著看烏雪昭的笑話。甚至還有人說:“美麗卻不貞,一根白綾吊
41.6萬字8 9699 -
完結487 章

退婚后,修仙女配靠彈幕翻盤了
宋錦抒胎穿到了古代,卻沒想到有一日未婚夫上門退婚,看見他頭頂上竟然有滾動彈幕! 【氣死我了,這一段就是逼婚的場景了吧!】 【惡心的女人,長得都像個狐貍精!就知道天天貼著男人跑!】 宋錦抒:!?? 她怎麼就是狐貍精,啥時候倒貼了,還有這些彈幕憑什麼罵她!? 宋錦抒這才知道原以為的普通穿越,結果竟是穿進一本修仙文里,成了里面的惡毒女炮灰! 不僅全家死光。 哥哥還成了大反派! 宋錦抒氣的吐血,因為一個破男人,竟然會有這樣的結局,真當她傻? 退婚,果斷退婚! 【叮!恭喜宿主激活彈幕系統】 【扭轉較大劇情節點,難度:一般,獎勵極品健體丹×1,黃級雁翎匕(首次獎勵),屬性點:力量+1,防御+1】 擁有了彈幕系統,只要她改變自己和家人的原定命運,系統就會給出獎勵,憑借這個金手指強大自己,追求大道長生它不香嗎? 宋錦抒立志決定,認真修煉成仙,什麼男人都全部靠邊! 然而她卻沒想到,自家性子冷漠的哥哥宋錦穆,卻對她退婚的事耿耿于懷,竟然成天想收刮美男塞給她。 宋錦抒:“……” 球球了,現在她一心向道,真的無心戀愛啊! ps:女主低調,但不怕事,非圣母,慎入
98萬字8.18 18155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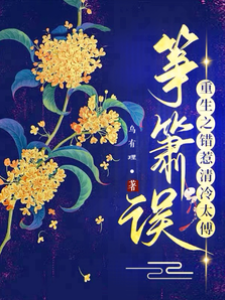
箏簫誤:重生之錯惹清冷太傅
【重生】【1v1雙潔、HE】原名:《箏簫誤》【深情克制“高嶺花”權臣✖️堅韌勇敢“不死鳥”千金】 *** *** 死光了男丁的祝府,窮的只剩花不完的錢。 樹大招風,孤立無援,前世被太子滿門抄斬。 一朝重生,祝箏為了保全全家,順了祖母招婿的美人計,生米煮熟飯,討個平庸的夫婿聊作靠山。 春酒助興下,紅羅帳燈昏,一夜良宵暖…… 但是……等等!哪里出錯了? 誰能告訴她……晨起枕邊人,為何不是祖母的安排? 而是當朝權臣,太傅容衍? —— 深山雪夜,月下梅前。 容衍給祝箏講了一個故事。 癡情的妖君與山神做了交易,換回他的公主死而復生。 祝箏凝眉:“他交易了什麼?” 容衍:“不重要。” 祝箏:“怎麼會不重要?” “公主不知道,所以不重要。”他目光沉靜,淡淡道,“妖君不在乎,所以也不重要。” “那什麼重要?” 容衍抬眼,眸光若皎皎冷月,籠罩著眼前人。 良久,道出兩個字。 “重逢。” - 情難自解,愛是執迷不悟,覆水難收 #非傳統重生文,立意“純愛萬歲,自由萬萬歲” #男追女,究極暗戀、蓄謀已久、甜寵微虐、復仇、沒有火葬場的漫漫追妻路、無雌競、非嬌妻、非女強、非強取豪奪、女主輕微回避型依戀(請自行排雷)
37.5萬字8 1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