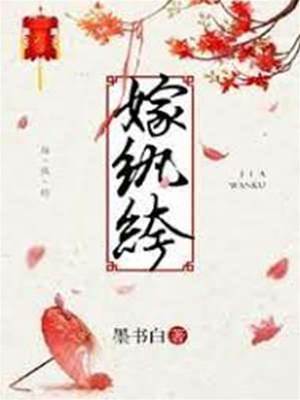《傳聞中的家主大人》 第52章 第五十二章
“不錯,這位小兄弟一看就是聰明毓秀之輩,也只有這樣的人,才配在家主大人跟前服侍啊!”
“看小兄弟天庭飽滿,眸子清正,將來定是大有可為!”
“哈哈,老兄這話說錯了,小兄弟已經隨侍在家主大人邊,這世上可還有哪里比得上嗎?”
佩服佩服。
一位員眼尖,發現了一別人都沒有發現的關竅。他連忙取了雙干凈筷子,雙手捧過來:“小兄弟取食不便,用這雙吧。”
“不用。”說話的不是元墨,而是姜九懷,他拿起自己案上的筷子,擱在元墨捧著的盤子上,眼中約約含著一笑意,“用這雙。”
元墨出一個笑容,“其實,都不用。”
抓起一塊牛,往里塞。
滿堂俱靜,連樂聲都停了。
員們長大了,顯然,即便是以他們沛的馬屁功力,也找不出什麼詞來搭配此種行徑。
“小兄弟、小兄弟真是……”曹方絞盡腦,忽地靈一現,“小兄弟可真是率豁達,大有竹林之風啊!”
元墨終于知道為什麼在場的曹方的兒做得最大了。
只是竹林之風是什麼風?
“所謂竹林之風,是指魏晉之時的七位名士,他們狂放任誕,行世人所不敢行。”像是知道在想什麼,姜九懷低低道,眸子里有細細的,角噙著一笑,“別說用手抓菜,就算是袒腹、不蔽,他們也是毫不在意的。”
所以這到底是夸人還是罵人?
算了,元墨才不想知道這種問題,反正臉都丟了,一塊是吃,一盤也是吃,再次把自己往姜九懷后了,借住姜九懷擋住自己的影,然后稀里乎嚕干了一盤,胃大人終于舒坦了。
Advertisement
而廳上員們依舊聊得十分火熱,話題已經談到了“這位小兄弟可能上輩子就是個大善人做了許多善事今生才會有此福報”。
正是機會!
“家主大人……”元墨湊近一點,悄聲道,“我來是……”
“平福。”姜九懷打斷,代平公公,“帶去洗手,再把人帶回來。”
很明顯,平公公聽到的命令應該是“帶去丟掉,然后永遠不要再回來”。
所以一路上臉非常臭。
洗完手,回來路上,元墨跟他講道理:“平公公,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如果你痛痛快快把銀票給我,我兒就不用混進來,你知道我跑來這里費了多大的勁嗎?”
平公公恨恨地瞪著:“你不要以為瞞得了咱家!你的心思咱家再清楚不過,銀票什麼的本是你故意放在主子這里的,就是想借機會來見主子!”
這真是,天大的冤枉!
“咱們這麼說吧!”元墨一擼袖子,“兩千四百兩,現在還給我,我馬上走人!多留一刻我是你孫子!”
“咱家沒有孫子。”平公公的臉更臭了。
呃,元墨發現自己失言了,“那隨便是什麼好了,反正你給我錢,我就走——”
話沒說完,平公公猛然剎住腳,原本拉長了三尺的臉瞬間春風滿面,恭恭敬敬行了個禮:“三爺,您子還未大好,天正冷著,怎麼過來了?”
一名高瘦男子含笑而來。
他披鶴氅,氣質出塵,步履矯健,足下輕盈,仿佛只有三十歲上下,面容清俊,看上去不會超過四十,但眼神曠遠,仿佛已經閱盡紅塵,像足七八十歲的老者。
一時之間,元墨竟判斷不了他的年紀。
“今日是懷兒襲爵之后第一次面,我想了想,還是替他照看一下,免得有什麼麻煩。”男子說著,目落到元墨上,“這位是……”
Advertisement
元墨連忙行禮,正要答話,平公公道:“他就是奴才跟您提過的那個元二,本以為主子已經把他扔在月心庭了,沒想到這小子又使詭計粘了上來。”
任何時候,平公公才姜九懷的事都是諱莫如深,沒想到在這三爺面前卻像是竹筒倒豆子一般,什麼都說——而且還說!
“三爺您明鑒,小人實在是被無奈才出此下策的。實是平公公欠小人兩千四百兩銀子,小人現今無分文,不得不上門討債。”
哼,難道只有你一個人會胡說八道不?
平公公果然急了,還是三爺打圓場:“此事回頭再說,是非曲直,自然要有個公斷。”
這話說得不偏不倚,十分公正。但平公公是四品太監,久在姜府,而元墨只不過是個外人,份相差懸殊。他還能這樣說話,不由讓元墨心生好。
姜家三爺名長信,人稱“玉翁”,乃是揚州第一風流人。他生在極貴之家,卻是沖淡平和,從不以名利為絆,只以詩書為念,琴棋與丹青皆。
他能與世外高人一起琴,也能與巷頭俗子一下棋,能與大儒研六經,也能為伎譜新曲,這樣的人是姜家這座深宅里的一縷清風,只要有他在,就能讓每個人都賓至如歸。
果然,自他到來,客人們終于不用絞盡腦歌功頌德,坐姿都閑適了幾分,眾人從京中時局談到塞外風,又從塞外良馬談到揚州逸聞,姜長信皆是信手拈來揮灑自如,客人們也興高采烈十分投機。
元墨本就缺覺,如今飽餐一頓,之前喝的幾杯冰雪燒好像終于融進了之中,的腦子有些暈起來,廳上的高談闊論之聲變一片模糊的嗡嗡響,只有膝下的地毯沉實,雖比不上紅茸毯,也夠舒服的了……
Advertisement
姜九懷只覺得后安靜得有些不對勁,回頭看了一眼,只見元墨已經是眼皮打架,跪在地上搖搖晃晃。
忽聽那邊姜長信道:“家主,你意下如何?”
姜九懷父母早亡,是由姜長信一手教養長大,琴棋書畫皆是出自姜長信的調教,姜長信于他而言是如師如父,但在外人跟前,姜長信從不以此居功,永遠喚他作“家主”。
廳上眾人商議冬日正值閑暇,不如舉行一次詩會,想請姜九懷作評審——其實這只是個過場,誰都知道姜九懷不喜歡這些應酬,只待他拒絕,大家便理所當然地推舉姜長信擔任。
“此事……”姜九懷也知道,正要推辭,只是才說兩個字,忽地,背心一沉。
他微微前傾,隨即穩住,幅度很小,外人幾乎看不出來。
背心著暖暖的溫,微沉的份量。
滿廳燈火,仿佛都搖晃了一下。
姜九懷一不。
這反常的停頓讓姜長信抬眼過來,他的席位加在姜九懷旁邊,輕而易舉地,看到那個元二靠在了姜九懷背上。
姜長信怔了怔。
底下的員看不到發生了什麼,但見家主大人長時間沉,不由也都關切地過來,機靈點的如曹方之流,已經在想家主大人可能在為難,自己是不是該說點什麼幫家主大人婉拒呢?
還沒尋思完,姜九懷輕聲道:“——甚好。”
員們都愣住了。
“好!”曹方第一個反應過來,每年的詩會都是州府主辦,姜長信固然是文采風流眾所歸,但家主大人的份放在這里,有家主大人當評審,今年的詩會定然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熱鬧。
眾人紛紛附和,正要舉杯高聲祝頌,姜九懷雙手虛按,眾人連忙噤聲,不由想起之前無論大家怎麼歌功頌德,家主大人好像眼皮都沒有多抬一下,看來不吃這一套?當下都變得安靜了不。
Advertisement
姜九懷向平公公招了招手。
平公公連忙附耳過來。心想這禍害竟然靠到主子上,純屬自己找死,主子最不了的就是有人如此近,哼哼,終于可以名正言順把這混蛋扔出去了……
“取我的斗篷來。”
家主大人如此這般吩咐,聲音是一種從未有過的輕。
元墨做了個很舒服的夢。
夢見自己睡在大片大片的云朵上,上也蓋著的白白的云朵,云朵又大,又,又香。
不知過了多久,一道尖細的嗓音直穿進耳朵:
“安寧公主駕到——”
安寧公主?誰?又不認得……腦子里模模糊糊這樣想,然后才猛然驚醒。
安寧公主!是當今天子唯一的寶貝兒,是本朝子民唯一的一位公主。
這一睜眼,才發現眼前依然一片漆黑,竟然被什麼東西罩了起來。
難道是酒后昏睡,平公公嫌失儀,所以把裝麻袋了?
如此這般想著,揭開一條,探出頭來。
看到一個十七八歲走近,那生得明鮮妍,似一朵帶芍藥,角正含著一朵微笑,盈盈道:“九懷哥哥……”
元墨半夢半醒,懷著純然的心欣賞人,唔,這一的飾可真是華麗啊,人兒也是生得玉雪可,笑起來頰邊還有兩粒小酒窩呢!
人的視線驀地對上了好怕,陡然間發出一聲尖:“啊——”
元墨下意識想堵耳朵。
人的形小,元墨真想不到一小小的軀竟然能發出如此尖利的聲響,簡直要懷疑這位公主修煉過佛門獅子吼神功。
但下一瞬,也想尖了。
因為姜九懷轉過了臉。
被烈酒和睡眠麻痹的大腦終于恢復了正常,元墨三魂掉了七魄,發現自己竟然趴在姜九懷背上,腦袋剛好從姜九懷肩上探出來。
姜九懷這一轉頭,兩人息息相聞,鬢角幾乎要到對方的鬢角。
他的臉在面前放大,毫無瑕疵,潔如玉,長長的睫分明,臉上既不驚也不怒,甚至不像往常那樣冷冰冰,角還約帶著一笑意。
這是夢。元墨冷靜地想。
我一定在做夢。
把腦袋從姜九懷肩上下去,重新回方才給一片黑暗溫暖的斗篷里。
等、等一會兒再睜眼,一定可以用一種正確的方式醒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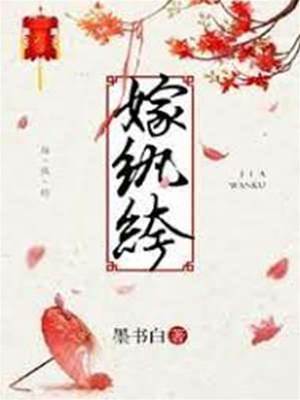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2933 章

領袖蘭宮
入宮了,她的願望很簡單:安安靜靜當個小宮女,等25歲放出去。 可是!那位萬歲爺又是什麼意思?初見就為她 吮傷口;再見立馬留牌子。接下來藉著看皇后,卻只盯著她看…… 她說不要皇寵,他卻非把她每天都叫到養心殿; 她說不要位分,他卻由嬪、到妃、皇貴妃,一路將她送上后宮之巔,還讓她的兒子繼承了皇位! 她后宮獨寵,只能求饒~
449.3萬字8 89937 -
完結1135 章
逆天神妃
她是華夏的頂尖鬼醫,一朝穿越,成了個被人欺辱至死的癡傻孤女。從此,一路得異寶,收小弟,修煉逆天神訣,契約上古神獸,毒醫身份肆意走天下。軟弱可欺?抱歉,欺負她的人還冇生出來!卻不知開局就遇上一無賴帝尊,被他牽住一輩子。 “尊上!”影衛急急忙忙跑來稟報。躺床上裝柔弱的某人,“夫人呢?”“在外麵打起來了!夫人說您受傷了,讓我們先走!她斷後!”“斷後?她那是斷我的後!”利落翻身衝了出去。
141.4萬字8 473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