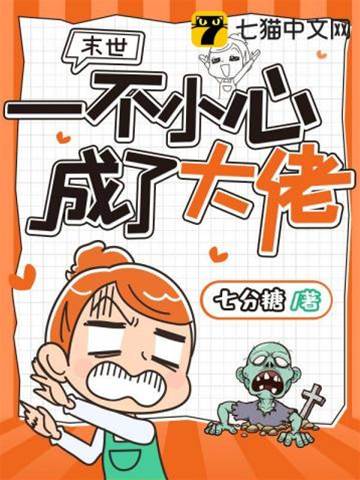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誘餌》 第188章 想我了?
收到短信的男人一字不讀完,也清除掉。
傭人進書房,風雪過后,外面正是艷高照。
屋卻昏暗得很,只依稀窺伺到窗前的一抹人影。
“先生,您不拉簾嗎?”
芬姐要拉開,被陳政制止,“老大回了嗎。”
停住,“我聯絡過大公子,他近期不開。”
陳政擰開醒腦油,涂在指腹,點了點太,“你傳我的原話,他不回,我親自去一趟天府1號,場面不可收拾,怪不得我了。”
芬姐愕然,“大公子不是住陳公館嗎,天府1號是?”
他冷哼,“陳淵出息了,藏了姓喬的九年。”
他猛地一摔手機,機殼四分五裂。
楊姬那條短訊是——喬小姐復活,大公子舊未了。
陳政一萬個不信,在異國他鄉無無依,卻躲過號稱“東南亞頂級殺手”的黑狗搜捕,并且平安無恙活到今日。
很明顯,其中有鬼。
喬函潤家世平庸,沒有后臺,也不伶俐,有道行從陳家的天羅地網中逃,不是陳淵布局護航,又會是誰。
一向敦厚沉穩的長子,在眼皮底下玩一出金蟬殼,陳政簡直始料未及。
“喬小姐沒死?”芬姐也傻了,“那沈小姐...”
陳政臉鷙。
禍水東引,調虎離山。
陳家確實只顧防備沈楨,而忽略了其他人。
陳政從沒見過陳淵為一個人要死要活,下跪求。
喬函潤之外,便是沈楨了。
細琢磨,不像假的。
“支會夫人。”陳政嗑了嗑煙袋鍋的積灰,填充新的煙,“通過給老二施,出姓喬的。”
芬姐哎了聲,退出書房。
他一手抄煙袋,一手撥通黑的號碼,“你在什麼地方。”
Advertisement
“按您的指示,日夜跟蹤沈小姐。”聽筒靜悄悄,有回音,像在地下車庫,“沈小姐從醫院出來了,拎著包裹。”
陳政嘬了一口煙,“你讓手下盯,你撤。”
黑領悟他的意思,“您吩咐。”
“去天府1號,盯喬函潤,有機會綁了。”
他掛斷,愁眉不展。
老二才失勢,老大就暴真面目。
沒了對手,長房在家族獨大,作為唯一的繼承人,肆無忌憚不服管束了。
西院那頭,江蓉得知喬函潤活著,在佛堂然大怒。
“陳淵又犯糊涂!折在手上一次不夠,還要第二次嗎?”
芬姐勸,“二房倒了,二公子也廢了,先生只能重大公子,陳家的產業都是長房的,就算大公子娶喬小姐,先生沒轍。”
“老二是配合調查,不是死了!”江蓉手臂一掃,供桌的果盤糕點灑了一地,“高樓起與塌,在陳政一念之差,他肯救老二,老二照樣。”
“救二公子大費周章,興許竹籃打水,大公子口碑好,出也名正言順,先生何必舍近求遠呢?”芬姐清理著碎片,“夫人安心。”
“幸好何佩瑜那個老狐貍自掘墳墓,被趕出老宅,否則老二不至于為替罪羊,最擅長迷陳政了,有在,倒霉的一定是我兒子。”
“其實...”芬姐言又止,“二房始終屈居您之下,沒有過分折騰,二公子也安分,錯并不在二太太——”
江蓉瞪,芬姐立馬改口,“錯不完全在何佩瑜。”
“錯在我了?”
搖頭,“分明是先生的錯。”
“陳政是我的丈夫,他有千錯萬錯,我怎麼跟他算賬?”江蓉捻著佛珠,“何佩瑜表面假惺惺示弱,是緩兵之策。畏懼我娘家的勢力,因為沒靠山。老二扮豬吃虎,和他親媽一個德行,心思險毒辣。”
Advertisement
芬姐嘆息,陳家上下很發怵江蓉,病態一般執著于正室的地位,稍有風吹草,鬧得天崩地裂。
實際上,連局外人也瞧出陳政沒打算扶正何佩瑜,富誠集團有這份就,江家出過力,相比那些養小白臉又嗜賭的太太,江蓉為人面本分,教子有方,貿然取代,過不了輿論那一關。
終究也有結發之。
可惜江蓉太介懷何佩瑜母子,打散了多年分,也困住自己,令陳淵浮沉在畸形仇恨的教導中,淪為廝殺二房的刀刃。
何佩瑜離開老宅那天,特意到西院,對準佛像拜了拜,“你我皆是可憐人,斗來斗去半生,我不曾擁有名分,你不曾擁有意,我們的青春耗在這個男人上,貢獻了自己最珍貴的,到底值不值呢?”
過時明時昧的香火頭,注視江蓉,“陳淵和崇州也重復我們的無休無止的斗爭,他們又真正歡愉過嗎。”
“你從此罷手,老二放棄家產,各歸各位,自然天下太平。”
何佩瑜哂笑,“江蓉姐,已經斗到這一步了,誰回得了頭呢?你為兒子鋪路,我也要扶持我的兒子,奪回本就屬于我們母子的東西。”
江蓉回憶當時的場景,直勾勾鎖定嵌在墻里的佛像,“蘭芬,你不覺得蹊蹺嗎?”
芬姐說,“您指什麼?”
“我最了解陳淵的脾氣,倘若他藏著喬函潤,對沈楨演不了那麼真。”江蓉在佛堂中央來回踱步,“這九年,他出國有十幾次,連陳政也沒捉住他養人,那他絕對沒有。陳淵不如老二的鬼心眼多,不可能不馬腳。”
“若不是大公子不照顧喬小姐,喬小姐也活不下來啊。”
江蓉皮笑不笑,“你去告訴陳政,這件事十有八九是何佩瑜母子在搗鬼,企圖毀掉陳淵。陳政如果心,將老二放虎歸山,下一個毀掉的,就是陳家。”
Advertisement
芬姐轉述給陳政,他沒有半點反應。
臨近中午,書房門終于打開,陳政站在門口,后面的辦公桌堆積了一摞文件,“蘭芬,請二爺來老宅,我有事委托他出面。”
江蓉彼時在客廳削蘋果,角綻出一笑。
***
薛巖接到喬函潤的電話,正在長安區局對面的街口等燈。
人幾乎魂不守舍,“薛助理,我能坦白嗎?”
“您坦白什麼?”他不疾不徐反問,“坦白在英國注冊結過婚,與丈夫有兒有的事實嗎?”
喬函潤五臟六腑脹得疼,“我不愿瞞他。”
薛巖調頭,駛上南江路,“喬小姐,煎熬的過程和圓滿的結局,您總要二擇一。”
崩潰哭腔,“早晚要坦白,不是嗎?”
“當然。”薛巖意味深長,“不過喬小姐有幾分把握,大公子不嫌棄昔年舊嫁過人呢,畢竟他至今未婚。換位思考,您也會嫌棄他吧?”
喬函潤的哭聲戛然而止,“但沈楨——”
“沈小姐結婚在前,認識大公子在后,沒有兒累贅,離婚也干脆,喬小姐符合哪點?”那端逐漸顯真容,“齊商與大公子不共戴天,您的兒還在他手中,他雖然待您深,前提是您乖乖聽話,破鏡重圓剛一天一夜,您搖到這樣的程度,齊商要是懊惱,您這輩子見不著兒了。”
嚇得聲音發,“他要對揚揚做什麼?”
薛巖笑得森,“送到任意一個國家,母生離啊。您在意大公子的,難道不在意兒思念母親嗎?”
喬函潤呆住。
直到這一刻,徹底明白,陳崇州安排齊商與自己結婚,在籌謀什麼。
齊商的纏綿,溫討好,他面的背后,又掩埋多虛偽和利用。
Advertisement
“我要揚揚。”渾戰栗著。
薛巖滿意笑,“喬小姐既然要兒,應該也懂得二公子要什麼。”
“陳淵對我的...”喬函潤死死地攥著手機,“不復當年了。”
“只要喬小姐用心,死灰可以復燃,男人的憐憫愧疚,是人反制他的最佳武。我需要提醒您,時間不充裕了,您報答二公子越快越好。”
一輛奧迪A8在這時和薛巖肩而過,他視線落在駕駛位的人,急剎住,鳴笛。
人也剎車,同時降下車窗,“薛助理?”
“沈小姐。”他掐斷通話,“你回過富江華苑嗎。”
沈楨松了松安全帶,“還沒。”
薛巖警惕張四周,“陳董涉嫌轉移公款,被上面調查。”
方向盤,“屬實嗎。”
“你認為呢?”他語氣耐人尋味,“憑江蓉和大公子手段,真是二公子所為,早已翻天。”
沈楨深吸氣,“陳淵...”頓了頓,“江蓉或許會。”
“看來,沈小姐很信任大公子。”薛巖關閉音樂播放,“這場飛來橫禍,陳董不是走投無路,他答應娶何時了,何家自會出手。”
沈楨抿,好半晌,“他為什麼沒答應。”
“其一,陳董不是制于人的男人,一旦接何家救助,欠下這筆巨大的人,他日后與何小姐的婚姻,要永遠聽從何家,屈服何家。”
車廂的沙窸窸窣窣流逝,薛巖凝視區局大樓,“其二,在世人眼中,包括沈小姐眼中,陳董并非良人。認定他涼薄寡義,游戲場。至我看到的,陳董從未過與何家聯姻,背叛沈小姐的念頭。”
五指愈發用力抓,汗漬烙在方向盤,烙出一個手印的形狀。
“我知道了。”沈楨踩油門,穿過馬路。
不是初次來到長安區局,之前,周海喬打著出差的幌子在會所嫖,正好被長安區局拘留,要麼通知家屬,要麼通知單位,他選擇了家屬。
簽字罰款,領人回家,沈楨全程臊得不行。
這回,也算二進宮。
同樣探視男人。
比周海喬的罪名還大,還棘手。
沈楨在大堂攔住一名便,“陳崇州在嗎?”
那人打量,“你是?”
著發紺的角,“家屬探視。”
“探視不了,沒審完。”
男人轉上樓,跟著跑,在樓梯口又攔一遍,“你們頭兒同意了。”
“我們頭兒?”他指了指盡頭的局長辦公室,這會兒大門閉,“頭兒去省廳匯報工作,沒提過有人探視。”
沈楨掏出名片,給他。
男人本來沒當回事,一瞥,當即怔住。
是陳翎的名片。
親筆手寫——放行。
陳翎的名片相當金貴,全省99.9%的名流權貴,本拿不到。
上流圈擁有他名片的人,不超過十位。
陳家占了四個,老師占了五個,最后一個,在眼前了。
最關鍵不敢造假,也造不了假,陳翎字跡特殊,收尾的一筆劃得長,大氣磅礴。
像極了他本人的氣勢。
在長安區局,無人不識。
男人鄭重打量沈楨,“你是陳廳的家屬?”
關系不太好介紹。
含糊其辭,“他是...我三叔。”
男人恍然,“恕我眼拙了。”他恭敬歸還名片,“我帶你過去。”
沈楨提著餐盒,“要檢查嗎?”
男人余一瞟,“吃的?”
點頭,“黃燜牛。”
男人樂了,“我們伙食是差點,大老板吃不慣。”
沈楨猶豫一秒,“他挨了?”
“那肯定啊,我們可供不起山珍海味和現磨咖啡。平時加班吃泡面,頭兒比我們盛,吃二十元的盒飯。我們區局是陳廳帶出的下屬,嚴格執行艱苦樸素。”男人在三樓的一扇鐵門前駐足,指紋解鎖,“最多十分鐘,我們組長一點半準時提審。”
審訊室吊著兩排老式管燈,灼白的燈刺得眼暈。
往里走,煙霧濃稠嗆人,視野也混沌。
歪倒的礦泉水瓶和吃剩的快餐盒擺滿審訊桌,空氣冷冰冰,無比抑。
墻下的單人椅,陳崇州坐在上面,仰四四方方的天窗,一張側臉在明亮的影中消沉又寂寞。
像是有所應,他忽然偏頭,看向后。
沈楨在彌漫的白煙里,一寸寸清晰。
陳崇州沒想到會出現。
就像最初,不經意在他的世界掀起浪花,開始這段差錯的故事。
這幾天,他反復回想,自己似乎辜負了許多人。
除了倪影。
他的三十二年有意或無意,踏足過一些人的生命。
在紙醉金迷的夜晚,在意氣風發的白晝。
他甚至不記得們的名字。
可當陳崇州現在回過神,確信沈楨不是虛無的影像,而是真的,他大喇喇笑,“想我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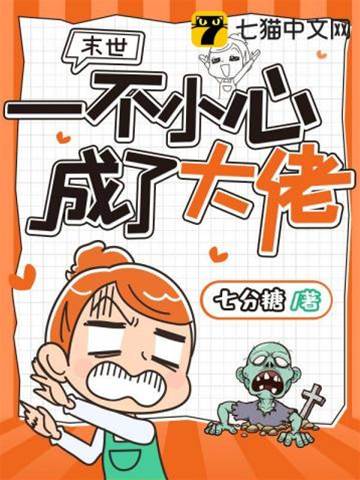
末世一不小心成了大佬
她在末世掙扎五年,殞命瞬間卻回到了末世剛開始,恰逢渣男正想推她擋喪尸。她踹飛喪尸,準備再掀一次渣男的天靈蓋!囤物資,打喪尸,救朋友,她重活一次,發誓一定不會讓任何遺憾再次發生。不過周圍的人怎麼都是大佬?殊不知在大佬們的眼里,她才是大佬中的大佬。
75.3萬字8 11226 -
完結740 章

團寵大佬:真千金又掉馬了
林笙一出生就被扔進了大山里,被一個神秘組織養大,不僅修得一身好馬甲(著名設計師、格斗王、藥老本尊……),本以為有三個大佬級爺爺就夠炫酷了,萬萬沒想到,叱咤商場的殷俊煜是她大哥,號稱醫學天才的殷俊杰是她二哥,華國戰神殷俊野是她三哥,娛樂圈影帝殷俊浩是她四哥。某天,當有人上門搶林笙時:爺爺們:保護我方囡囡!哥哥們:妹妹是我們的!傅西澤一臉委屈:笙笙~我可狼可奶,你確定不要嗎?林笙:我……想要
131萬字8 269482 -
完結1602 章
丑妻逆襲夫人火遍全球了
云綰是被父母拋棄的可憐女孩兒,是她的養母善良,將她從土堆里救了出來。在漸漸長大的過程中,..
142.6萬字8.18 448598 -
連載424 章

咬色
爲了讓她乖乖爬到跟前來,陳深放任手底下的人像瘋狗一樣咬着她不放。 “讓你吃點苦頭,把性子磨沒了,我好好疼你。” 許禾檸的清白和名聲,幾乎都敗在他手裏。 “你把你那地兒磨平了,我把你當姐妹疼。” …… 她艱難出逃,再見面時,她已經榜上了他得罪不起的大佬。 陳深將她抵在牆上,一手掀起她的長裙,手掌長驅直入。 “讓我看看,這段日子有人碰過你嗎?” 許禾檸背身看不到他的表情,她笑得肆意淋漓,擡手將結婚戒指給他看。 驚不驚喜,意不意外?
71.8萬字8.18 13158 -
完結283 章

大佬的白月光又野又狂
不小心上錯大佬的車,還給大佬解除了三十年的禁欲屬性。盛晚寧正得意,結果被大佬一紙狀告,進了局子。她憤憤然寫完兩千字懺悔書,簽下絕不再犯的承諾,上繳五千元罰款……暗咒:厲閻霆,有種你別再來找我!……一年後。厲閻霆:“夫人,你最喜歡的電影今晚首映,我們包場去看?”她:“不去,你告我啊。”……兩年後。厲閻霆:“夫人,結婚戒指我一個人戴多沒意思,你也戴上?”她:“戒指我扔了,有本事你再去告我!”……五年後。厲閻霆:“夫人,老大已經隨你的姓,要不肚子裏的小家夥,隨我,姓厲?”她:“憑什麽?就憑你會告我?”……
72.7萬字8.18 132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