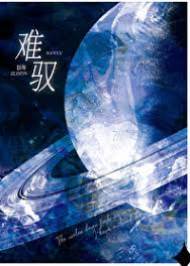《誘餌》 第152章 傷口
長實集團總裁辦,梁澤文甩出一份辭職報告堆在辦公桌,“你簽了,到財務室領取五年的薪水作為補償。”
魏意一怔,“你要開除我?”
梁澤文不耐煩,“你得罪誰不好,得罪沈楨?”
“我不知!”魏意大吼,“你如果早點坦白,我會得罪嗎?”
“我憑什麼向你坦白?你不要忘了自己的份。”梁澤文翹起二郎,偎在沙發,“這些年,梁家帶給你多風,你打著董的旗號,又獲得多不屬于你的特權,一拍兩散你不虧。難道傍上梁家,指全家都犬升天嗎?”
無刻薄的臉令魏意再次怔住,“你耍我嗎?梁澤文,是你當初欺騙我,你和梁太太早已離婚,為了長實的穩定才不分家,我揣著這個忍辱負重,你承諾集團港上市后,公開離婚,娶我過門,那我到底算什麼?”
“行了,在我面前還裝腔作勢。”梁澤文不屑哂笑,“你八面玲瓏,男人有家沒家,你看不破?逢場作戲罷了,有幾個老板為場面上的人拋家舍業?你吃香喝辣生活得太舒服,不舍得放棄我這棵大樹,我挑明又裝無辜,你這種人,活該被耍。”
魏意整個人搐,可無可奈何,與梁澤文云泥之別,梁家碾死,如同碾死一只螞蟻不費吹灰之力。
只得認倒霉,“五年的薪水補償?你未免太黑了。”
梁澤文點煙,睥睨,“你開個數。”
“五百萬。”
“你也配。”他噴出一個煙圈,“我敢掏,你敢拿嗎。”
“梁澤文,你畏懼陳崇州的勢力,迫不及待打發我,省得他怪罪長實。你像一株墻頭草,在陳大和陳二之間搖擺不定,你覺得他們誰會重用你?國貿集團的傅太太和柏華在溫泉池幽會,你派人錄像,又親手給陳二,對嗎?你和傅董是盟友,你為攀附富誠出賣他,假設傅董得知,國貿和長實的實力哪個更勝一籌啊?”魏意俯下,挨近他,“你不是投誠陳大嗎?我不配五百萬的補償,那你這點道行,配得上富誠的間諜嗎?他們倆能玩死你。”
Advertisement
梁澤文叼著煙,火苗閃爍,他獰笑,“五百萬就五百萬,你可千萬封住自己的。”
魏意沒回應,揚長而去。
完手上這煙,梁澤文起,線聯系司機,“昌平街區修公路,近期是不是車禍頻發。”
司機說,“夜里沒路燈,看不清土坑邊緣的施工牌,星期三發生了一起連環撞,傷者差點沒搶救,公路是上面的指標,總不能不修啊。”
梁澤文像彈鋼琴一樣,彈電話線,語氣意味深長,“我知道了。”
他返回沙發,沉思良久,撥沈楨的號碼,提示關機,再打薛巖的電話,同樣沒打通。
他心臟咯噔一跳,預不妙,陳崇州一貫是權貴子弟中最難纏的,不吃,十分記仇。
很明顯,這位陳二公子心不痛快了。
梁澤文萬不得已又聯絡陳淵,是楊姬代他接聽的,瞟了一眼遠,“不巧,陳董在忙。”
梁澤文一時于啟齒,“我的書...是我管教不嚴,醋勁大,平日刁難小沈,下午恰好二公子過來,目睹跋扈,鬧得很僵。”
楊姬客套說,“沈小姐不是斤斤計較背后告狀的子,梁董多慮了。”
“可是二公子惱了,如今大公子失勢,我借二公子搭上富誠的后臺,長實集團蒸蒸日上,以后對大公子也有幫助嘛。”
“我會轉達陳董,請他想辦法。”楊姬正要掛斷,梁澤文回憶起什麼,“沈小姐的背景除了二位公子,還有其他人嗎?”
楊姬一頓,“您發現什麼了?”
“今天接下班的車,是一輛軍綠吉普,尾號4個1,相當富貴有權勢的人啊。”
梁澤文并不認識陳政,不在同一個圈子際,自然不認識他的座駕,而且陳政有七八輛車,吉普只是其中最普通的一輛,不惹眼。
Advertisement
楊姬卻一清二楚,明目張膽掛如此高調的車牌,只有國賓半島第一排那五棟莊園的人。
董事長大選結果完全失控,陳政察覺到陳淵反了,陳崇州亦不是任人宰割的魚,他開始重演喬函潤的悲劇,遏制兩個兒子的反心。
現階段有利用價值的,僅剩沈楨了。
楊姬攥著機殼的手一,“什麼時候。”
梁澤文回答,“六點多。”
結束通話,疾步走向球場的更室。
隔著門,楊姬聽見陳淵在講話,似乎是視頻會議,河濱的項目有變。
“你打點鄭智河,帶頭否決老二將我調回本市的提案,繼續流放我。”
視頻那端的男人很詫異,“二公子流放您去外地,目的是架空您手中的實權,他既然改主意,不是好事嗎?一旦董事局否決,接下來長達一年,您必須負責河濱的工程,商場變數無常,富誠再也不是您的天下了。”
陳淵笑了一聲,“你按照我的指示辦。”
楊姬握著門把猶豫一秒,又退下。
彼時,薛巖駕車泊在國賓半島4號院,他沒下去,揭過后視鏡,著陳崇州摁門鈴。
保姆清理了餐桌,路過玄關,拉開門。
兩位公子回老宅一向提前一天通知,很貿然登門,保姆欣喜不已,“二公子,您回來用晚餐嗎?”
陳崇州默不作聲往里沖,保鏢早有準備,在戶長廊截住他,他本能一躲,保鏢一個勾拳,卡在他肩胛骨,“老董事長目前不方便,您在北院等候。”
“不方便?”他揪住保鏢領,兇猛一摔,保鏢猝不及防,當場掀翻在地。
他偏頭,質問呆住的保姆,“沈楨在什麼地方。”
保姆結結,“沈小姐...”
Advertisement
張理這時走出書房,捧著一本珠寶宣傳圖冊,剛要去花園,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二公子,您這是什麼意思?”
“你們抓了。”
“?”張理一頭霧水,“是誰。”
陳崇州手肘一搪,撞得他踉蹌,“他媽裝糊涂!”
保姆在陳家也工作過一陣,接蘇姐的班,主管西院和廚房。大公子儒雅,二公子斯文,都是溫朗俊秀、知書達理的男人,暴躁到這程度,聞所未聞。
“二公子,您稍安勿躁——”
保姆要攔他,撲了個空,陳崇州跑向南院,“陳政!”
張理橫在前面,“您直呼父親姓名,太放肆了!”
“未經我允許,擅自,你們放肆在先,我再如何放肆,你們也著。”陳崇州發力一拽,幾乎拎起他,“張理,我念在你一輩子為陳家盡忠,容忍你多次,你是好日子過膩了,敢在太歲頭上土。”
“是嗎?陳家的太歲爺。”臺傳出陳政惻惻的腔調,陳崇州廝打的作驟然一滯。
窗紗緩緩升起,漢白玉壘砌的臺階之上,一張紅木茶桌,凹槽放置一壺烹煮的清茶,咕咚咕咚冒著氣泡,白霧彌漫,覆蓋院外的隆冬夜,顯得昏黃而溫暖。
陳政對面坐著一個人,正是完好無恙的沈楨,也一同看向客廳。
“啊。”陳政不疾不徐端起陶瓷杯,觀賞杯壁描摹的花紋,“不是很狂妄嗎,公然我的名字。”
男人打量沈楨,確認沒有傷,“他們綁架你了?”他氣勢強悍,一凜冽的敵意。
“混賬!”陳政扔了茶杯,刺耳的碎裂響,嚇得沈楨當即站起。
陳崇州松開張理,襯包裹的膛急劇鼓起,好半晌才平復,嗓音仍嘶啞重,“你綁干什麼,有鷙的招數朝我來,折磨一個人,陳政,你六十五歲了,越活越不像個爺們。”
Advertisement
“逆子,你有規矩嗎!”
他不顧陳政的呵斥,只顧沈楨,木然搖頭,“陳伯父沒有綁架我。”
陳崇州本不信,陳政有多麼歹毒,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包括陳淵,都不如他了解。
“他沒捆你手腕?”
沈楨依然搖頭,“陳伯父派車接我,說你也在。”
原本是拒絕了,可張理熱懇切,又一把年歲,不得不給面子答應。
車廂吊著不黑的彩帶,到纏繞,也問了張理,他說用來裝扮庭院。
沒想到經過門衛時,被保安當捆綁的繩索。
張理在一旁勸誡,“二公子,您誤會老董事長了。陳家與海外歸國的鄔家是世,鄔世伯的長子娶親,老董事長親自為鄔家的長媳挑選見面禮,那姑娘與沈小姐年歲相仿,因此特意請沈小姐參謀賀禮,您又何必氣。”
陳崇州忽然意識到,陳政在請君甕,探一探他的底。
他盯著周圍的保鏢,“現在陳家的掌權人是我,不是陳政。你們記住,我厭惡別人我的東西,我的人。”
保鏢面面相覷,深諳不能再惹惱他,沒有吭聲。
陳崇州走過去,將沈楨護到后,怒火又撒給陳政,“你有完嗎?”
陳政眉頭蹙,抑制著脾氣。
“當年喬函潤活不見人死不見尸,陳淵急之下,不惜斷絕關系威脅你讓步,你搞不定他,搬出江蓉以跳樓的把戲向陳淵施,他認命妥協。”
陳崇州一手抱著沈楨,一手活泛筋骨,和保鏢搏斗的過程,他出手太瘋,著力也太野蠻,肩膀一收一放掄得狠,臼了一般,淤青腫脹。
“江蓉與我母親表面在陳家養尊優,其實是你脅迫我們的籌碼,生母是我和陳淵的顧忌,在你手里著,無論刀山火海,只要我們保得住這條命,你吩咐我們闖,我們就要闖,為陳家蹚渾水。”
“你終于承認了,故意設局演戲,送你母親逃出陳家,離我的掌控。”陳政輕笑,臉上出一識破他的深意,“老二,你的確最像我,傳了我的心機與格局。”
陳崇州佇立在燈柱下,平靜了一些,“江蓉是陳家名正言順的主人,未來父親兵敗山倒,與陳家共存亡,給您陪葬,是應當的下場。我母親沒討到名分,不該攪進陳家的漩渦。”
陳政微微瞇眼,“你篤定我會敗嗎。”
“晟和集團對接海外的賬戶究竟有什麼門道,父親心里有數。”
片刻的雀無聲。
沈楨到腰間的手臂發剛毅如堅鐵的力量,從沒見過這樣的陳崇州。
野難馴,張揚氣。
一步步,制約著更為高深強大的陳政。
陳政審視他此刻的荒唐不羈,西裝歪歪扭扭,頸間的領帶也扎得凌,晃晃墜在口。
“折騰得夠兇,看出你是真急了。”他撂下杯子,主緩和氣氛,“回房收拾利索再出來,像什麼樣子。”
陳崇州摟著沈楨,目像一匹出籠的野狼,毫不松懈。
陳政明白他的意圖,抬手潑掉沈楨那杯冷卻的茶,“隨你。”
他帶著沈楨一并回客房,推門的一霎,仿佛被干了所有力氣,后背虛虛抵住墻壁,蒼白的面容浮出汗。
沈楨轉過,詢問跟在后面的保姆,“有急救包嗎?”
保姆點頭,“有的。”越過沈楨,瞧屋里,“二公子傷勢嚴重嗎,需不需要醫生?”
“用不著。”陳崇州關了壁燈,打開臺燈,“外傷而已。”
保姆很快拿了藥箱進房間,沈楨接過,用棉簽蘸了藥膏涂在紗布,小心翼翼解開他扣,目之所及,一灘麻麻的淤斑點,凝固在肩窩。
指尖輕輕過那塊傷痕,他瞬間繃直。
沈楨一抖,收回手,“疼嗎?”
陳崇州閉著眼,薄抿。
不單單胳膊疼,脖子的筋脈,腔肋骨抻得也疼。
老宅的六個保鏢,有四個是江蓉娘家親戚,看似尊重二房,實際逮著機會公報私仇。
何佩瑜被逐出南院那天,保鏢把行李砸了,貴重的水晶瓷,和田玉佛,砸得稀爛。尤其那尊佛像,江蓉很喜歡,是十年前陳政去海南出差,在三亞求來的,一共四十九名高僧開過,他卻送給了何佩瑜,何佩瑜又愚蠢,住進老宅后擺在南院耀武揚威,江蓉看在眼里,如鯁在。
陳崇州著眉心,“皮傷,不礙事。”
沈楨的五臟六腑擰了一下,形容不出什麼滋味。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6 章
告白送錯情書之后
阮映暗戀年級第一薛浩言整整兩年,他是她的學習動力,是她的日月星辰。終于阮映準備默默用情書告白,卻意外聽到薛浩言正和別人調侃她:“長得一般般,也沒啥特點,我眼瞎了才會看上她吧。”阮映臉色煞白,轉身離開時撞上年級倒數第一蒲馴然。蒲馴然居高臨下看著阮映,笑得匪氣:“喜歡我?”阮映失魂落魄:“我不……”話還沒說完,蒲馴然一把將阮映手中的情書塞進自己口袋:“不用客氣,明天起我罩著你。”阮映欲哭無淚。蒲馴然,這個在阮映眼中橫行無理,野蠻暴躁的代名詞。那天起,她莫名成了他的“女朋友”。不久后,年級第一薛浩言給阮映發了條短信:[阮映,那封情書原本是要給我的嗎?]蒲馴然正好拿著阮映的手機,得意洋洋代為回復:[你哪位?簡直臉大如盆!]【劃重點】:男主是蒲馴然!!! ***** 小劇場一: 面對蒲馴然的各種自作多情,阮映終于忍無可忍:“你把這一百張試卷做完再跟我說話,記住,要獨立完成。”又一周,就在阮映以為這個世界清凈了的時候,蒲馴然把一百張試卷放在她的桌上,“吶,做好了。” 小劇場二:阮映和蒲馴然吵架冷戰。蒲馴然一連給她發了十幾條消息,最后一條消息是:【給老子一點時間消消氣,等下再來哄你。】阮映看著消息忍不住欣慰一笑,回復消息:【我要抱抱。】#你的出現,溫暖了時光和歲月# [ps:本文中未成年人沒有談戀愛] 一句話簡介:送錯情書,愛對人 立意:積極面對生活
18萬字8 9643 -
完結1068 章

重生校園女神:八零醫妻火辣辣
聽說,帝都的高嶺之花,所有丈母孃眼裡的金龜婿裴尋多了個未婚妻,還是個從農村出來的鄉下妹。掉進檸檬裡的眾人酸了:一定是裴尋口味重,就喜歡土不啦嘰的小村妞!然而,圍觀真人時,卻發現這位村妞膚白貌美,身段婀娜,比城裡喝過洋墨水的鎮長小姐還洋氣!眾人又酸,長得好看又怎樣,也就是個胸大無腦的花瓶!然而,花瓶今天吊打學霸進了帝都重點大學,明天順手治好身患絕癥的大佬,後天還舉辦了個隻有頂級名流才能進的去的茶會。眾人:這到底是哪來的大佬?!他們當然不知道,林音是來自31世紀的真·醫學大佬,重生1980,一路虐渣出村加致富。林音:「嗯?聽說你們看不起我?」正給自家小嬌嬌剝板栗的裴尋冷冷朝眾人瞥去一眼。眾人頓時狂搖頭:「不敢不敢,絕對不敢!」偽高冷帝都學霸x真醫學大佬小村妹,雙學霸,甜爽寵。
193.1萬字8 34466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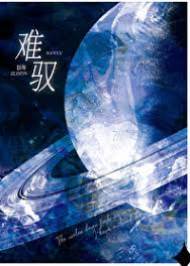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57 11698 -
完結484 章

被逼相親?我帶娃閃婚嫁首富!
楚曦帶着女兒在孃家無處容身,爲了不嫁老頭,跟僅一面之緣的男人領了證。 男人有車有房,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就是職業不太光彩——會所男模。 男模就男模吧,反正用不了多久就離婚了。 誰知婚後男模老公不但對她女兒特好,還超旺妻。 楚曦又是升職加薪,又是沒買彩票也中獎,村裏的房子也拆遷的,都變成富婆了。 正當她準備給財神燒柱香感謝感謝—— “媽媽你快來看!電視裏那個帥氣的霸總跟我爸爸長得一模一樣!” “這是怎麼回事?” 晚上回來,戰總把疑惑的老婆摟在懷裏邊親邊說。 “再給我生個娃就告訴你~”
87.1萬字8.18 27523 -
完結56 章

煙花情書
路西加與付河的初遇,是在那個冬天的園子里,她隔著窗戶看到這個人在花園里抽煙,匆忙套上外套,下樓提醒。 付河在煙霧飄散前看清了來人的臉。那一刻,美夢成了真。 后來,他喝醉了,城市的燈光下,他問:“時間,真的……能治愈一切嗎?” “嗯?”路西加沒聽清。 “那為什麼,沒有治好你。” -------------------------------------------------------------------------------------------------------- 付河X路西加。
17.4萬字8 12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