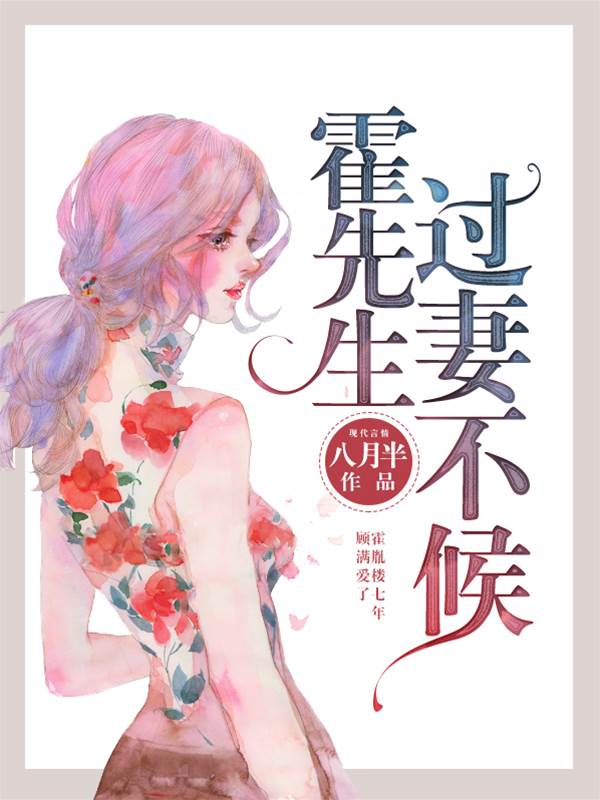《他的替身太太》 第43章 夜夜夜漫長
沈逸矜聞著香走進來, 口里咬著月餅:“今天是要謝謝你的,不然我只有吃個泡面才能睡覺了。”
說得自然,沒覺得不對, 但祁淵聽了,背對著,手里擰著抹布的手更用力了幾分, 似要跟什麼較勁似的。
然而最終他還是下了那份緒,轉對沈逸矜說:“泡面有什麼好吃, 添加劑多,又沒營養, 下次我給你帶些零食來。”
沈逸矜笑:“零食比泡面有營養?什麼零食?”
祁淵角輕勾:“等我帶來了,就知道了。”
沈逸矜朝鍋里嗅了嗅:“快好了吧, 迫不及待。”
祁淵看著笑:“沒呢, 再去吃塊月餅,吃完了就好了。”
沈逸矜搖頭:“不吃月餅了, 我要留著肚子吃螃蟹。”
祁淵說好, 他覺到沈逸矜今晚興致高, 主和他說了很多話, 也沒有像以前那樣對他時時防守,時時抗拒,大概是今晚自己來對了吧, 終于撞上了一個盔甲的時候。
祁淵疏朗一笑, 心好了很多。
冰箱里翻了下,找出一塊生姜,他放上砧板, 從塊切片, 再到, 最后剁碎末,準備伴醋做蘸料。
沈逸矜看著他,吃東西的速度不自覺地放慢了。
燈影與熱氣在男人上匯,低眉垂眸里,染了他一的煙火氣。
總會想,他的價,他的地位,他和這仄的空間格格不,可是他手起刀落,指尖嫻,對待家的廚房似乎比還要悉。
“我是不是很帥?”祁淵抬頭,捉住的目,問。
沈逸矜眸閃了下,語氣奚落:“是啊,不只是帥,臉皮還厚。”
祁淵笑,朝過一只手臂:“幫我把西服了。”
Advertisement
沈逸矜怔了怔:“你自己不會?”
祁淵舉了下刀,理由充分:“不方便。”說著,胳膊了,帶著強勢和催促。
沈逸矜勉為其難地靠近過去,幫他下。
誰知某個臉皮厚的人又得寸進尺,彎下腰,抬起脖頸:“還有領帶也解了。”
沈逸矜:“……”
曾經短暫的婚姻里都沒做過的事,現在男人卻在理直氣壯地做?
沈逸矜將西服搭在自己手臂上,抬手給他解領帶,邊解邊說:“祁淵,我是看在今天中秋節的份上這麼幫你的,你別想歪。”
祁淵穩住聲音,彎下腰配合著:“嗯,我知道,我這不是手沒空嘛。”
領帶解下,他又說:“還有領口的紐扣也給我解兩個。”
沈逸矜:“……”
指尖過去,到頂上那小小一粒,隔著料,都能覺到男人溫燙的溫。
祁淵低下眉睫,濃的眼睫輕輕扇了下,“嘩啦”一聲,沈逸矜手臂上的西服領帶掉到了地上。
沈逸矜彎下腰撿起,頭也不抬地,轉出了廚房。
祁淵靠著流理臺,角勾起,舌尖掃了掃齒貝。
大閘蟹蒸好以后,祁淵去臺看了下,窗外一明月皓亮沉靜,如煙似霧的云穿梭其間。
他和沈逸矜商量著,將小餐桌搬到了臺上,挨著按椅,兩人就在那里,邊賞月邊吃大閘蟹。
沈逸矜找來一個純凈水的塑料瓶,將頭上用剪刀剪去一小截,了幾枝荷花擺到了餐桌上。
祁淵笑著看著,想起他今晚上在老宅吃的飯,泱泱三十多人的大宴席,富麗堂皇的房子,窮奢極惡的菜肴,不抵眼下方寸之一人的語輕笑。
他問沈逸矜:“家里有沒有酒?”
Advertisement
沈逸矜說有,找了一瓶紅酒給他。
那是超市促銷時,拿小票加十元換購的,可祁淵喝了,卻說:“這是我喝過的最好喝的紅酒。”
“那你多喝點。”沈逸矜笑著給他添滿。
沈逸矜不只是喜歡吃蟹,還很有方法,將蟹的上下殼拆開,筷尖挑了蟹黃吃掉,再住蟹爪輕輕一拉一扯,帶著拆下,作溫又優雅,看著不像吃東西,更像做一件藝品。
這是小時候媽媽教的。
“真會吃。”祁淵坐在對面,學著,才知道自己以前都是瞎吃。
“那你呢?”沈逸矜笑,“是真會做?”
“一個會做一個會吃,說明什麼?”
“什麼?”
祁淵眸含笑:“是絕配。”
沈逸矜:“……”
就知道不該接話。
臺上的燈老舊昏暗,錯著房間傾斜投來的,將兩人的影子重重疊疊在墻上。
局促的空間里,燈影,花香,笑語,終不過兩人,卻溫馨而浪漫。
祁淵心愉悅,將自己更往前傾了傾,讓墻上的影子看著更親一些。
他挑起一筷子蟹黃,遞到沈逸矜碗里。
“你自己吃。”沈逸矜謝道。
可祁淵當沒聽見,手里作我行我素,里聊起別的話題,擾的注意力。
祁淵聊起老宅的事,告訴沈逸矜:“老爺子不好,我今天答應他,搬回老宅去住了。”
沈逸矜點頭,心想那和自己沒關系,可是祁淵說話的語氣很己,像和說著不為外人道的私房話。
祁淵又說:“老爺子現在不大認得人了,上次手雖然撿回來一條命,但到底年紀大了,他現在只認得我和老太太,別的人要麼認不出,要麼名字。”
語氣里有種無可挽回的滄桑。
Advertisement
沈逸矜安他:“不管怎麼說,他都因為你有命活下來了。要知道,很多事都沒辦法挽回的。”
是想起了的父母。
祁淵看著,將手里拆下的蟹放到碗里,本想說他會替父母好好照顧的,但又怕反,只好換了話說:“人生苦短,我們要活在當下。”
沈逸矜笑了笑:“別人說這個話多有點悲觀,你有什麼好悲觀的?”
“那可太多了。”
“你那麼有錢。”
祁淵放聲笑:“窮得只剩錢了。”
沈逸矜睨他,覺得他太欠了,隨手抓起一只蟹殼朝他扔過去,祁淵抬手接住,丟到桌上,再一手便將手指上的一抹蟹油抹到臉上了,那作又又壞。
沈逸矜反應不及,了聲:“你壞死了。”越過桌子就想反擊,可怎可能是祁淵的對手,雙手在空中,被祁淵扼住了手腕。
祁淵挑釁:“是啊,你咬我?”
沈逸矜有一刻還真想咬他,可是一個轉念,他們這是在干什麼,調嗎?
掙開手,了下臉,覺自己酒喝多了。
那掌臉上喝了酒紅艷艷的,祁淵了張紙巾,抬手越過桌面給了臉。
那紅潤,滾燙,祁淵指背輕輕刮蹭了兩下,心底似有水翻滾,想再多一下,沈逸矜已經嫌棄地打開了他的手。
兩人不說話,空氣一時陷靜寂與曖昧,窗外圓月悄悄東斜,進煙云里,只留下一團若若現的暈。
正此時,祁淵手機響了,是老爺子祁崇博打來的視頻。
祁崇博大腦里的語言障礙越來越嚴重,已經不太能說話,他一張滿是皺褶的臉盯著屏幕,口齒不清地著祁淵的小名,要他回家。
祁淵握著手機,背轉過餐桌,將自己和沈逸矜框進攝像頭,一言一字放慢語速,對手機里的老人說:“我在矜矜這里,爺爺你困了先睡,不要等我。”
Advertisement
祁崇博耷拉的眼皮瞇一條眼,將沈逸矜看了看,朝招了招手,說:“帶,回來。”
祁淵笑,看著沈逸矜的表替說:“矜矜不肯的。”
祁崇博拍了下桌子,用力吐出一個字:“搶。”可能覺到方式太暴,又拍了拍桌子,改說,“拿錢。”
沈逸矜看著老爺子,白發蒼蒼,年邁虛,抬手舉止間卻仍不失霸權的格,倒有那麼幾分冥頑不靈。
對著鏡頭,禮貌地笑了下,沒介意老爺子的話,但也沒回應,祁淵對老爺子說:“不行的,矜矜很貴的,我們買不起。”
本是隨口一句哄騙的玩笑,誰知道老爺子認了真,盯著屏幕看了好一會,巍巍得從椅子上站起,離開了鏡頭。
沈逸矜朝祁淵遞了個迷的眼神,祁淵也表示不解,老爺子那邊有傭人在,鏡頭里沒人,卻能聽見幾人走的聲音,還有開柜門,保險箱轉的聲音。
祁淵眼皮子狠狠跳了下,預到老爺子干什麼去了。
果然,沒一會,有傭人攙扶著老爺子,坐回鏡頭前,祁崇博手里多了一個紅天鵝絨的大盒子。
他讓傭人打開,將盒子里的東西對向鏡頭,竟是一套鉆石項鏈,整個一個鏈圈都是用鉆石組,而吊墜是一顆鉆,有鴿子蛋那麼大,四周包裹一圈小鉆。
璀璨奪目,而價值連城。
祁崇博拍了拍項鏈,指了指沈逸矜:“拿去。”
祁淵笑了,轉頭對沈逸矜說:“這條項鏈是祁家最值錢的首飾,可以用它換一架私人飛機,多人做夢都想得到它,爺爺現在要把它送給你。矜矜,快謝謝爺爺。”
沈逸矜:“……”
一時愣住,沒敢接。
屏幕里老爺子有點急,又拍了拍項鏈,雙手因激抖個不停,卻努力將盒子端了起來,往鏡頭里送,好像這樣就能送到沈逸矜面前。
沈逸矜對祁淵說:“這樣不好的,快爺爺收起來。”
祁淵看態度堅決,只得朝祁崇博說:“爺爺,你先收好了,我和矜矜談談再說了。”
之后又安了好一會,才把老爺子勸了去休息,掛斷了視頻。
沈逸矜這才松了口氣,想起另外一件事,問祁淵:“老太太那個手鐲,你還給了嗎?”
祁淵挑眉:“還干嘛?”
沈逸矜有點急:“當然要還了,我們都分手這麼久了。”
祁淵:“……”
眸漸漸郁,但凡這種時候,他便氣短,商場上再多厲害的能言善辯在這種時候都理虧詞窮。
沈逸矜沒注意他的臉,叮囑的口吻:“那手鐲在你保險箱里,你有空就還給吧。”
記憶力不太好,容易忘事,可既然想起來了,就想把這事兒辦掉。
祁淵有點煩躁了:“不還,要還你自己去還。”
沈逸矜點頭:“那行,你拿來給我。”
想到那個老太太,慈,慷慨,第一次見面就送那麼貴重的禮,而自己卻還拿去典當行弄出那麼大的一個笑話。
如果和祁淵沒分手也就算了,既然分了手,還是應該還回去,給老太太一個代。
祁淵有時候就覺得拎得太清,與人的分界線劃得太清楚,一個人有原則是好,但這個原則將他排斥在外面,就不好了。
他說:“不拿,想要你就去找我。”
沈逸矜蹙了下眉,一臉看不懂地看他:“我這不是找你了嗎?”
祁淵搖頭:“不是,我今天是來找你的,你要的話,就得去找我才算。”
沈逸矜:“……什麼歪歪理?”
祁淵被的“歪歪理”說笑,終于覺得自己掰回一局了,眉宇里松了松,靠在椅背上,無賴的語氣:“對,我就是歪歪理。”
沈逸矜瞟他一眼,站起,拿手機看了眼時間,說:“你快點回去吧,太晚了。”
這是下逐客令了。
祁淵不聽,拿過一只螃蟹,開始剝殼,將無賴繼續發揮下去:“螃蟹沒吃完,等吃完了我再走。”
沈逸矜手搶過那只螃蟹,連著盤子一起抱進懷里,說:“我吃不下了,還剩四只誒,這些我留著明天一個人吃,沒你的了。”
抱著盤子的樣子像護著寶貝一樣,看得祁淵笑了。
他想起馮玲曾經告訴過他,沈逸矜小時候在蘇家欺負時常常被關在房里,不給吃飯,得面黃瘦,神雙重折磨。
祁淵站起,長手了的腦袋,說:“以后我帶你吃遍全世界的食。”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116 章

大佬甜妻寵上天
十二年前,他救她一命,為了報恩,她決定以身相許,偷生他的寶寶! 誰知睡錯了人,竟和他親大哥一夜錯情。 都說負負得正,她卻是錯錯得對。 N年後,她攜天才萌寶回國,萌寶一心給她找個粗大腿抱,結果第一天母子兩人就被大總裁抵在牆角——「拐跑我的兒子,必須再給我生一個」
372.3萬字8 255273 -
連載1828 章

六年后,她生的三個縮小版大佬炸翻了集團
葉攬希出身不好,被嘲諷又土又沒品位。赫司堯對這場婚姻很不滿,三天兩頭不是當紅小花就是比基尼少女。葉攬希發飆了,“你就這麼不喜歡我?”“別玷污喜歡這兩個字!”“所以你這一輩子不會忠于婚姻?”“只要是你,就不會!”他不會是一個好父親,葉攬希為了肚子里的孩子決定結束這段婚姻,“那我們離婚!”六年后。葉攬希蛻變回國。赫司堯直接將她拉到無人的角落,抵在了墻上。“葉攬希,我的孩子呢?”“打了!說好老死不相往來,這樣斷的干凈!”赫司堯氣紅眼,“那就再給我生一對雙胞胎,這是你欠我的!”說完,直接把她撩到腿軟!...
306.9萬字8.18 202014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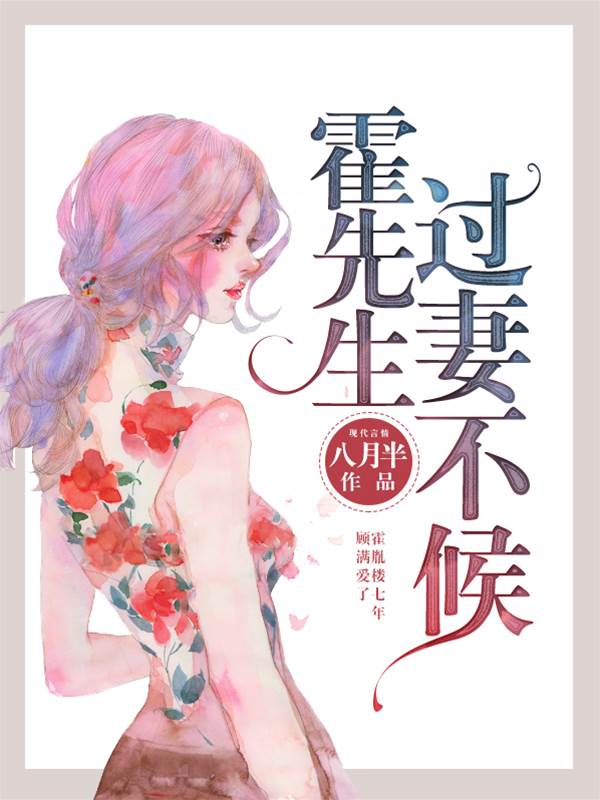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8451 -
連載386 章

協議老公破防後,天天往我被窩鑽
相個親被奇葩男罵是撈女,一氣之下鳳祈喝多了,陰差陽錯進了頂頭上司的房間…… 付浦鈺常年不近女色,殺伐決斷,鳳祈快被嚇死了,努力隱藏自己,以為隻要當一切都沒有發生就能蒙混過關。 可是有一天,付浦鈺卻找到她,提了一個讓她意外的要求——結婚。 一個見錢眼開,一個逢場作戲,為了各自的目的一拍即合。
40.6萬字8 43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