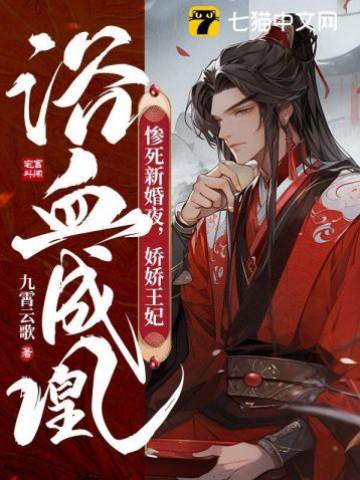《心機太子妃》 第87章 第 87 章
第八十七章
唐韻昨夜睡好了, 太子卻沒睡好。
白綾綁上一陣,是為趣,綁太久,便只剩下了難和麻煩。
昨夜綁了一夜沒取, 眼睛合得太久, 如今大夫一來, 將那白綾剛取下, 眼瞼的瞳仁便被經久不見的亮, 刺得一疼。
太子下意識地瞥開了眼。
大夫心頭一喜,這是眼睛能見了,忙地問道,“殿下, 可瞧得見了?”
剛一問完, 唐韻便答道,“還瞧不見呢。”
大夫一愣, 空歡喜了一場。
“殿下再試試,能不能睜開?”大夫有些張,他不睜開,他也沒法診斷,就怕當真傷到了瞳仁,耽擱了最佳的治療時期。
“孤......”
“還是別勉強了, 先緩幾日,貿然睜眼, 了刺激,豈不是更嚴重。”沒待太子說完, 唐韻再次開口同大夫道, “大夫還是照昨兒那般, 先敷些清明的藥草,繼續綁著便是。”
大夫有些猶豫,還是想堅持看一下太子的眼睛。
適才他那反應,分明是對有應大的......
大夫還想勸勸,但見太子一語不發,似乎任由這位娘娘做主,便也不敢多說,囑咐道,“,那殿下再敷兩日,若是期間有何不適,尤其是疼痛加劇時,定要知會在下,在下這就去備藥......”
“有勞大夫了。”
兩刻后,大夫將藥草碾碎,制了膏泥。
唐韻親手給太子涂上,涂得比昨兒要厚,昨兒大夫只在他的眼瞼上輕輕抹了一層,今日唐韻卻將他的整個眼瞼完全糊上了。
他雖已經復明了,但眼睛過傷卻是不假。
正好也趁著他愿意瞎下去的功夫,多給他敷幾日,就當是修復眼睛,有益無害。
Advertisement
眼瞼被厚重的藥泥一涂,白綾再一綁,太子還真就瞧不見了。
眼睛都睜不開。
太子:......
唐韻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聲道,“殿下這幾日就別試圖著睜眼,安心修養,想要什麼,同我說,我陪著殿下。”
唐韻將白綾在他腦后打了一個結,又喚來了大夫。
后背上的藥昨兒是顧景淵替他換的,唐韻怕自己手生,弄疼了他,加重傷勢,便給了大夫。
大夫換好了藥,唐韻又帶著他去洗漱,洗漱時的漱口水,都是唐韻將碗遞到他邊,喂到了他里,“殿下慢慢來,不急。”
洗漱完,又替他更。
一個早上,唐韻都在忙忙碌碌。
顧景淵送裳過來時,便見太子和唐韻兩人坐在團,唐韻拿著勺子,正一勺一勺地往他里煨著粥食。
“殿下,燙嗎?”
“不燙,韻兒,孤自己來吧,孤總不能讓你伺候......”太子頗有些煎熬,固然是想對自己好些,但如今......似乎有點過了。
再想起昨兒問自己的那句話,太子從早上起來,心頭便一直懸著。
越是對自己好,他越是不安。
“無礙,殿下如今收拾,又眼盲,我伺候殿下是應該。”唐韻說完,又將勺子遞到了太子邊,“殿下張,啊......”
太子:......
顧景淵見到這一幕,眉心兩跳,一雙眼睛險些也被刺瞎。
堂堂太子,他也不怕害臊。
“殿下。”顧景淵忍著鄙夷,走到了太子跟前,同其行了禮,將手里昨兒太子要袍遞了過去,“殿下瞧瞧滿不滿意。”
太子:......
他瞎了,他看不出來?
“給我吧。”唐韻起,趕替其接了過來,回頭笑著道了謝,“多謝顧大人。”
Advertisement
顧景淵看了一眼,目中流出了不忍。
從太子那日來了蜀中,找上了小院子起,顧景淵便知道,這輩子恐怕都無法再擺太子。
無論是他,還是,又怎可能斗得過跟前這位險狡詐,善于偽裝的的黑心太子。
他恨自己無能,更恨太子的驢肝肺。
今日他這般裝著眼盲,明擺著又是在想著法子欺負。
顧景淵心疼地看著跪坐在太子旁,垂目仔細地幫他查看著的唐韻,那眉目之間雖是一子的淡然從容,卻再無在那間小院子時散發出的明亮。
顧景淵口一悶,言又止。
厚厚一層藥泥敷在眼睛上,太子當真是瞎了,此時雖瞧不見,卻知道顧景淵還立在跟前,且心頭有一子異常強烈的預。
顧景淵絕對在看。
太子測過子,同唐韻道,“不用查看了,顧大人辦事,孤放心,定也非是那等趁人之危的小人。”
顧景淵:......
顧景淵落在唐韻上的目,忙地一轉,一刻都不想多呆。
正要轉走出去,太子突然喚住了他,“顧大人既然來了,今日便有勞顧大人再陪孤一日,太子妃昨日伺候了孤一夜,子疲乏得。”
伺候二字本也正常,可此時從太子里說出來,卻讓人品出了別樣的意味。
顧景淵的耳子倒是突然一紅,心下又暗罵了一聲無恥,強地拒絕道,“臣手腳,怕是照顧不周,怠慢了殿......”
“無妨。”
顧景淵:......
太子打斷了他后,又回頭同唐韻道,“寧大爺應該也來了府衙,你此番遭劫,險些丟了命,他豈能不憂心,想必是見不到人不會安心,你先出去報個平安,孤這兒暫且有顧大人照看。”
Advertisement
唐韻看了一眼已經轉過腳尖的顧景淵。
人家似乎并不樂意。
也不知道太子得了什麼病,不喜讓丫鬟伺候,這病也并非是到了蜀中才有的,往日他那東宮,屋就沒見過一個小丫鬟。
若非也在這屋里,太子兒就不會讓丫鬟進屋。
唐韻確實也想去見一面大舅舅,出了這麼大的事,大舅舅心頭定在著急,昨日到今日,怕是一直都沒踏實。
唐韻正想著要不要一個小廝進來先伺候著,見顧景淵的腳步又轉了回來,“唐姑娘去忙吧。”
唐韻這才放了心,起道,“有勞顧大人了。”
顧景淵對點了頭。
適才過來,他是同寧大爺一道,自然也知道寧大爺在等著。
唐韻沒再耽擱,將手里的袍給他擱在了床榻后,走出了小院,去見寧大爺。
寧大爺昨兒一宿幾乎也沒合眼,想著當初唐韻前來蜀中之時,父親給他寫了信,萬番代,定要看顧好。
他竟只顧著自個兒忙,人何時走的都不知道。
如今人在的地兒,出了這麼大的事,他怎麼可能還睡得著,每每一想起前兒的那場截殺,寧大爺心頭就跳得慌。
韻姐兒要是真有個好歹,寧家怕也不會安寧了,父親鐵定不會饒了他。
昨兒雖聽顧景淵說已經醒了,可到底是沒有親眼見人安然無恙,心頭還是不踏實,今日一早又跟著顧景淵走了一趟。
唐韻一出后院,便見寧大爺立在前院的廊下候著,遠遠地招呼了一聲,“大舅舅。”
寧大爺聽到聲音才猛然回頭,見唐韻完好無損地抬步上了長廊,懸著的一顆心,終于落了地。
“韻姐兒可有哪里傷。”經過昨兒一日,太子和是如何在道上遇到的刺客,又是如何被當了鹽販子誤了牢房,他都聽說了。
Advertisement
私下里,府衙的人一說起來,只會添油加醋。
就差將那刺客說得會飛檐走壁,是以,堂堂一國太子,才會在自個兒的地盤之,遭其暗算。
唐韻笑著走上前,立在了寧大爺跟前,“大舅舅放心,我無礙。”
寧大爺瞧了一圈,見確實沒有哪兒不對,也徹底地松下了一口氣,心有余悸地道,“好在你沒事,要是出了事,舅舅這條命怕也得跟著沒了。”
非得被父親一劍抹了脖子不可。
唐韻一笑,心頭多也因自己的不辭而別,有些愧疚,致歉道,“讓大舅舅擔憂了。”
“勝在是虛驚一場。”寧大爺深吸了一口氣,臉上到底是有了些許笑容,“人沒事就好。”
寧大爺也沒去問和太子的關系,在牢房,他看著太子抱著,昨兒夜里,又安置在了一起,什麼關系已經不言而喻,用不著他再問。
但只要一日還沒有進宮嫁給太子,那便一日是他寧家的人,雖說太子的人馬眾多,護衛也多,可風險也大,前日不也遭了劫。
寧大爺今日過來,一是想瞧瞧到底如何了。
二來,便是想打算親自送回江陵。
“你來之前,你外祖父再三叮囑我要照看好你,誰知竟出了這麼大的事,大舅舅的魂兒都快被你嚇沒了,再放你一人回去,我是怎麼也放不下心。”
寧大爺想先問問的意思,“韻姐兒瞧瞧,哪一日起方便,大舅舅將你送回江陵。”
唐韻知道他忙得很,正要婉拒,寧大爺又道,“正好我也回一趟寧府,寧家好不容易有了如今的風,大舅舅還未瞧上一眼呢。”
這話說得倒也合合理。
寧家起來了后,外祖父不知給大舅舅遞了多信兒,要他回去一趟,且三表哥也中了貢士,他這個做父親的,確實該回去一趟。
可太子那......
寧大爺見眼里有了猶豫,大抵也猜出來了的顧慮,直接挑明了道,“韻姐兒如今尚未婚嫁,便仍是我寧家的人,既是我寧家人,我為你大舅舅也理所當然,該為韻姐兒撐起堂面來,不管將來韻姐兒的份有多尊貴,咱們該走的過場,該行了禮,都不該被落下。”
一個小姑娘,既沒有母親替拿主意,也沒有父親給撐面兒,有些事不明白也正常,可他為的親舅舅,不能不管。
不明白,他們這些做長輩就得去提點。
他這番陪著太子,冒了風險不說,也失了名聲。
府衙個個都喚為娘娘,但他這個當親舅舅的卻不知,說句不好聽的,此時跟在太子邊,就是無名無分。
寧大爺并不知道和太子之間的糾葛,但他清楚,唐韻如今還是個未許親的姑娘,既沒同太子定親,也沒納彩,這般不明不白地跟在他邊,實屬不妥。
若傳了出來,即便將來當真了太子妃,也會被別人背地里脊梁骨。
吃虧的還是。
唐韻:......
確實如此。
怪,這幾日,被太子一會兒發瘋,一會兒矯,攪得腦子都了,倒沒有想到這一點。
且,前兒若非自己跟著,以他的武功,也不會傷。
分開走,是最好,也不會拖累了他,唐韻便也應了下來,“大舅舅打算何時起?”
“明兒吧。”越早越好。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97 章
首輔大人最寵妻
前世她是繼母養廢的嫡女,是夫家不喜的兒媳,是當朝首輔強占的繼室……說書的人指她毀了一代賢臣 重活一世,靜姝隻想過安穩的小日子,卻不想因她送命的謝昭又來了 靜姝:我好怕,他是來報仇的嗎? 謝昭:你說呢?娘子~ 閱讀指南: 1.女主重生後開啟蘇爽模式,美美美、蘇蘇蘇 2.古代師生戀,男主做過女主先生,芝麻餡護犢子~ 3.其實是個甜寵文,複仇啥的,不存在的~ 入V公告:本文7月7日V,屆時三更,麼麼噠 佛係繼母養娃日常 ←←←←存稿新文,點擊左邊圖片穿越~ 文案: 阿玉穿成了靠下作手段上位的侯門繼室,周圍一群豺狼虎豹,閱儘晉江宅鬥文的阿玉表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奈何,宅鬥太累,不如養包子~~ 錦陽侯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明明是本侯瞧不上的女人,怎麼反被她看不上了? 阿玉:不服?休書拿去! 侯爺:服……
52.4萬字8 32349 -
完結2123 章

醫妃獨寵俏夫君
21世紀的暗夜組織有個全能型殺手叫安雪棠,但她穿越了。穿越第一天就被賣給了一個殘障人士當妻子,傳聞那人不僅雙腿殘疾還兇殘暴戾。可作為聲控顏控的安雪棠一進門就被那人的聲音和俊美的容貌蠱惑住了。雙腿殘疾?冇事,我能治。中毒活不過半年?冇事,我能解。需要養個小包子?冇事,我養的起。想要當攝政王?冇事,我助你一臂之力。想要生個小包子?呃…那…那也不是不行。
363萬字8.5 1190101 -
完結134 章

棄婦覺醒后(雙重生)
前世蘭因是人人稱讚的好賢婦,最終卻落到一個被人冤枉偷情下堂的結局。 她被蕭業趕出家門,又被自己的家人棄之敝履,最後眼睜睜看著蕭業和她的妹妹雙宿雙飛,她卻葬身火場孤苦慘死。 重生回到嫁給蕭業的第三年,剛成為寡婦的顧情被蕭業領著帶回家,柔弱的女子哭哭啼啼, 而她那個從來冷漠寡言的丈夫急紅了眼,看著眼前這對男女,蘭因忽然覺得有些可笑,她所有的悲劇都是因為這一場不公平的婚姻。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了。 和離後的蘭因買宅子買鋪子,過得風生水起,反倒是蕭業逐漸覺得不習慣了, 可當他鼓起勇氣去找蘭因的時候,卻看到她跟朝中新貴齊豫白笑著走在一起。 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蘭因居然也能笑得那麼明媚。 蘭因循規蹈矩從未對不起誰,真要說,不過是前世那個被冤枉跟她偷情的齊豫白, 他本來應該能走得更高,卻被她連累,沒想到和離後,她竟跟他慢慢相熟起來。 齊豫白冷清孤寂,可在黑夜中煢煢獨行的蘭因卻從他的身上感受到久違的溫暖和疼愛, 他和她說,你不是不配得到愛,你只是以前沒有遇對人。 大理寺少卿齊豫白冷清克制,如寒山雪松、月下青竹,他是所有女郎心中的檀郎, 也是她們愛慕到不敢親近的對象,所有人都以為像他這樣的高嶺之花一輩子都不可能為女人折腰。 不想—— 某個雪日,眾人踏雪尋梅路過一處地方,還未看見梅花就瞧見了他與和離不久的顧蘭因站在一處, 大雪紛飛,他手中的傘傾了大半,雪落肩頭,他那雙涼薄冷清的眼中卻含著笑。 齊豫白活了兩輩子也暗戀了顧蘭因兩輩子。 這輩子,他既然握住了她的手,就再也不會鬆開。
59.3萬字8 47762 -
完結6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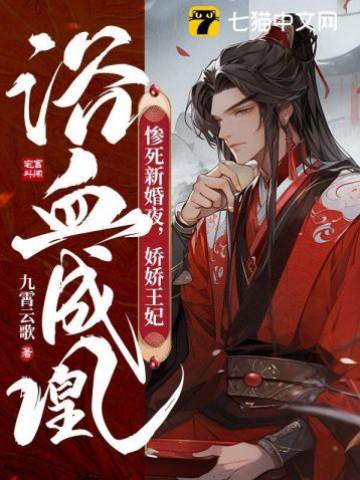
慘死新婚夜,嬌嬌王妃浴血成凰
葉沉魚身為被抱錯的相府假千金,被自己最在乎的“親人”合謀欺騙利用成為毒殺攝政王的兇手,含冤而亡。一朝重生,她回到了真千金前來認親的那一日。 葉沉魚決定做回自己,她洗脫自己的污名,褪下一身華服,跟著鄉野出身的父母離開了相府。 本以為等待她的會是艱苦難熬的生活。 誰料,她的父母兄長個個都是隱藏的大佬,就連前世被她害死,未來權傾天下的那位攝政王,都成了她的……小舅舅。 葉沉魚一臉的郁悶:“說好的苦日子呢?” 蕭臨淵:“苦了誰,也不能苦了本王的心尖尖。”
109.2萬字8.18 144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