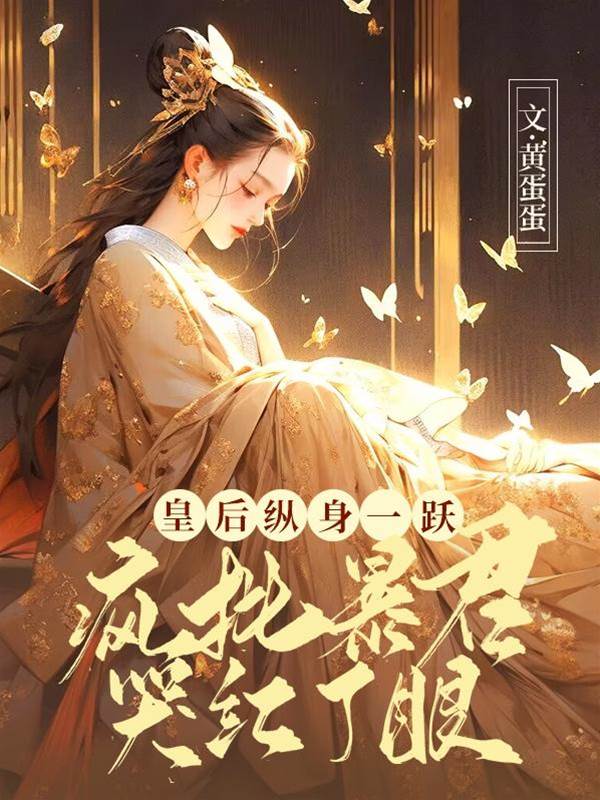《細腰美人寵冠六宮》 第42章 第四十二章
淑妃一雙眼睛直直的看著榻上的虞若蘭,有苦難言。只能打碎了牙齒往肚里咽。
醫過來把過脈,虞若蘭的確小產了。
淑妃還有什麼可說的?!
“皇上駕到!”林深高唱一聲。
嬪妃們紛紛出門接駕,皇后走在最前頭,一看見帝王款步而來,步履如風,清雋俊的面容在一片影之下,顯得深邃幽怨,的心就不由自主的加速跳了起來。
封衡是的表哥。
這麼多年來,皇后一直有獨占,可也一直在裝大度慈善。
但皇后心里很清楚,皇上是一個人的夫!
眾嬪妃請安,封衡揮袖一掃,“都起來吧。”
皇后走上前,一只圓潤玉手故意搭在了封衡手臂上,但實則是虛虛的搭在了上面,以免被帝王拂開,“皇上,貴嬪妹妹的孩子沒了,臣妾知道皇上心中難,皇上還會有其他孩子的。”
皇后聲細語的寬,宛若最心的解語花。
封衡掃視了一圈,淑妃致的面容已低沉到了極致。
委屈、不甘、怨恨,諸多緒雜。
約明白,自己被虞若蘭下套了。
可沒有任何證據。
淑妃抿著,可憐的著封衡。
此刻即便在外殿,封衡也能聞到一令人不適的腥味。
帝王幽眸之中,神不明。
就在眾人都以為淑妃這次栽了時,封衡淡淡啟齒,“虞貴嬪小產,淑妃有責,罰自今日起,抄寫經書半個月。至于虞貴嬪,朕會讓太醫院每日過來定時復診。”
帝王話音一落,淑妃愕然,眾人皆愕然。
竟然……只是這般輕的懲戒麼?
淑妃娘娘果然還是獨一份的存在,不愧是皇上的心頭白月。
淑妃立刻展一笑,福謝恩,“臣妾謝皇上。”
Advertisement
皇后微微愣住,一時間尋思不明白了。皇上這又是何意?
殿,虞貴嬪聽到了封衡的話,咬著的同時,雙手揪了被褥。
只是懲淑妃抄半月的經書?!
今日鬧這一場,并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不過,唯一的好事是,落胎的可以揭過去了。
虞貴嬪眼下只能忍。
夏荷站在一旁,眉心擰,似乎想到了什麼,但又不能篤定。
封衡離開之后,眾嬪妃也訕訕離去。
原本都是過來看好戲的,可誰知,這場戲才剛剛開幕,就結束了。
*
朝閣。
虞姝聽到不久之前的變故,又喝了杯花茶驚。
原來,虞若蘭今日登門來見,還真是來陷害的。
結果,陷害不,卻盯上了淑妃。
不過,按的猜測,皇上理應知道后宮的一切私,可為何還是沒有對虞若蘭如何?
難道是為了安將軍府?
父親眼下在嶺南駐扎,且不論父親此人如何,三十萬虞家軍若是忠于皇上,皇上定能盡快鏟平他一統大業的所有阻礙。
可三十萬虞家軍,必須有一個虞家人來統領。
皇上會扶持二哥麼?
說實話,虞姝并不盼著二哥兵權過重。
功高過主,遲早會反噬。
幸好,還有父親和大兄著二哥一頭。
罷了,皇上必然有他自己的布局,不便揣測圣意,就算是揣測,也只能猜出一些細枝末節。
與皇上相比,的腦子終歸是淺薄的。
正托腮思忖間,脖頸突然傳來一溫熱,的。
虞姝一側過臉,就被一張俊無儔的臉嚇了一跳。虧得封衡摟住了的細腰,不然又要跌池子里。
虞姝尖了一聲,嗔帝王,“皇上怎麼也不讓人通報一聲?嚇壞嬪妾了。”
Advertisement
虞姝一只手拍了拍脯。
封衡在人脖頸深吸了一口香,目往下,掠過一抹雪峰山巒,眸中神忽然暗了暗。
清泉池旁邊種了一株水桶細的紫玉蘭,蔥郁枝葉遮了烈日,樹下一片清涼,是極好的納涼之。
封衡原有些疲乏,此刻圈住人細腰,靜坐池邊,竟突然覺得水中那只小烏也變得眉目清秀了起來。
總之,他挨近了虞姝,心也了。
封衡在池邊白玉石上落座,扣著人柳腰,將抱在上,附耳說,“嚇這樣?朕給你拍拍。”
封衡的手掌,代替了虞姝的手,在口輕拍了幾下。
虞姝,“……”
就在僵住,以為帝王實則骨子里是個浪子時,封衡卻又不聲的收手了,仿佛還是那個不重//的帝王。
封衡蕭的下就落在虞姝的肩頭,他看著虞姝輕輕扇的睫,輕笑問道:“方才在想什麼?”
虞姝回過神來,盡可能的表現出一個子對心悅男子的癡慕,“嬪妾在想、想皇上!”
虞姝隨口扯謊。
封衡卻是被逗笑了,他的腔微微輕,虞姝能夠的十分清晰。
封衡又問:“哦?是麼?那有多想?想朕做甚?昭昭所想,可是與朕所想的一樣?”
虞姝,“……”這是要打啞謎麼?
怎會知道皇上是如何想的?
這樣的皇上,著實讓不知該如何應對。
說起來,封衡在虞姝心中的印象,依舊是兩年前那個手持長劍,輕易就能將殺手一劍封的狠厲帝王。
醫過來復診,被宮人領朝閣,見年輕的帝王正抱著人,也不知帝王究竟附耳說了些什麼,人被到面紅耳赤,萬般無措。
Advertisement
醫愣住了,不由得多看了一眼。
這纏綿悱惻的畫面,只在話本子里才見過。
聽太醫院那邊說,虞貴嬪娘娘才剛剛落了胎,皇上怎還有心在這里打罵俏?
這后宮,果然是只聞新人笑,不見舊人哭。
醫心中暗暗腹誹。
這便垂下眼簾,走上前行禮,“皇上萬福金安。”
封衡見來人是醫,也不耽擱時辰,直接抱著虞姝起,將抱了殿。
醫又是心驚。
昭嬪娘娘是傷了胳膊,又沒傷及。
皇上的偏寵,未免過于明顯了。
醫給虞姝換藥期間,封衡沒有避讓,見虞姝蹙眉,封衡突然低喝,“放肆!輕些!”
醫子一抖,立刻跪地,“皇上恕罪,微臣并非有意。”
虞姝神微訕,抬首看了一眼帝王,“皇上,嬪妾無事的。”
皇上當真在意麼?
虞姝只以為,是因冒死相救之故。倒是沒有把“”看得太重。
醫重新給虞姝上藥,因著外裳褪了一半,里面的兜若若現。這個時候,封衡本該關切虞姝的子,可他還是忍不住起了旖旎心思。
就連封衡自己也震驚,哪怕虞姝傷,他卻還依舊肖想。
虞姝的兜都是他親手挑選,他對這種薄紗料子甚是滿意,尤其是尚坊繡娘的做工,兜配上虞姝的段,真正是絕妙畫面。
醫剛包扎好,封衡便問,“昭嬪眼下可否行房中之事?”神理所當然。
虞姝面一紅,隨即,耳子和脖頸也紅了。
微張,幾乎錯愕。
醫已許配給太醫院的世家醫,但尚未婚,聞言也是面漲紅,斂著眸,迅速如實回道:“回皇上,莫要過于激烈即可。”
Advertisement
有醫在場,封衡毫不避諱,“昭昭,那朕今晚過來。”
虞姝,“……”
醫離開朝閣后,頻頻回頭去,臉上一直火辣辣的。
雖然淑妃明面上最寵,可皇上對昭嬪娘娘似乎更是熱衷啊。
*
辰王府。
宮里的人送來旨意,王府上下都已知曉,辰王和張家二小姐的婚期就定在了下月初。
也就是說,辰王府從今日起就要開始忙碌大婚一事。
辰王舞了一會劍,最后一招時,長劍揮出,直接刺穿一株百年梧桐。
種樹梧桐下,自有凰來。
他想要的人,怕是一輩子不會來了。
辰王單膝跪地,一手撐在地面,指尖狠狠掐土中。
總算是明白了他那個好皇兄的意圖!
溫年站在一旁,打稿了腹稿,方才問道:“王爺,咱們是順著皇上的意?還是將計就計……不如,就讓楚王認為,你是他的兒子?”
楚王無子無,又已四十出頭,后大業自是要留給子嗣的。
辰王只要認父,就能平白的多出小半壁江山。
屆時,得了雍州,就能與封衡抗衡一二了。
再過幾年,鹿死誰手,還不一定呢。
辰王仰面,汗珠自額頭落,“溫年,你是想讓我認賊作父?!”
幾個皇子之中,他是最先帝重疼的一個兒子,是楚王領兵造反,殺皇宮,謀害先帝。
他不替父報仇就罷了,還要認賊作父?
溫年愣住。
辰王忽然仰面大笑了幾聲,這人世間究竟是怎麼了?既人人都可以不在意脈親緣,那又何必要生生不息的繁衍?!
溫年,“王爺?你莫要嚇唬屬下。”
風拂過,辰王的笑聲在風里消散,晨炫目,卻人盡是絕。
好片刻,溫年又問,“王爺,那婚禮之事,可要安排起來?”
辰王站起,“不安排?那我難不抗旨?!安、排!”最后兩個字,近乎咬牙切齒。
作者有話說:
沈卿言:沒有戲份的一天,寂寞呦~
——————
PS:寶子們,晚上給大伙一起發紅包哈~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1900 章

嫡女驚華
鳳驚華前世錯信渣男賤女,害的外祖滿門被殺,她生產之際被斬斷四肢,折磨致死!含恨而終,浴血重生,她是自黃泉爬出的惡鬼,要將前世所有害她之人拖入地獄!
194.9萬字8.18 337396 -
完結290 章

家有夫人兇又惡
傳聞朗月清風的韓相栽了,栽進那名鄉下長大,粗鄙不堪的將府大小姐手中… 自此相府每天都熱鬧,昨日剛點了隔壁尚書家,今日踹了那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 對此,韓相自始至終只有那淡淡一句話“夫人如此辛苦,此刻定是乏了,快些休息吧…” 某女聞言咽了口口水…腳下略慫的逃跑步伐邁的更大了…
26.6萬字8 10001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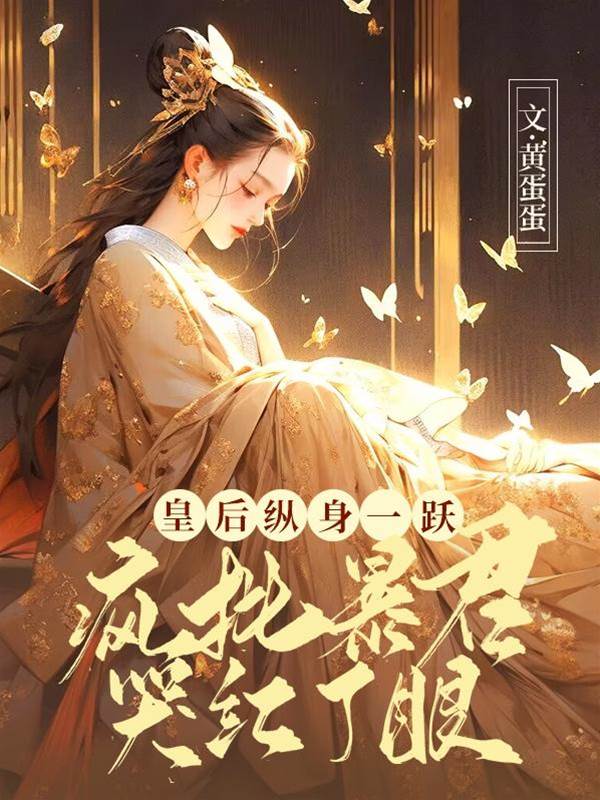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