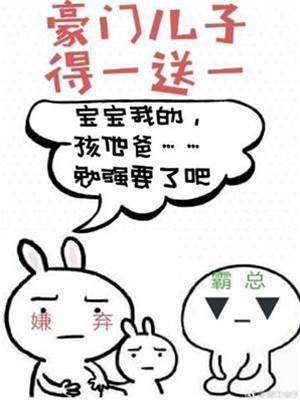《風繼續吹》 第42章 第 42 章
吃瓜吃到自家頭上,這打臉來的夠快的,朋友幾個都很不厚道,頓時笑噴了。
“文明文明,非常文明。”
江開:“……”
靜惹來前廳的注意力,暫時中斷了趙夢真和會所工作人員的爭執。
盛悉風也隨著眾人的目所向,一起看向電梯廳的嘈雜。
看到簇擁中心的那位,也是一頓。
本沒想到他還在國,猶記得在泉市的最后一個晚上,他打電話過來死命催的猴急勁,還以為他真的忙到不可開。
第二天飛機一直延誤,還怕耽誤他正事。
江開邊的朋友哄笑過一陣,很快就發現這“夫妻倆”狀態不太對勁,只一下對視過后,就先后冷淡地撇開頭,儼然連招呼都不打算打。
大家很有眼力見,紛紛收了調侃,互相看來看去,用眼神打探況,但沒一個人知道——剛才不還一口一個“我老婆”呢嗎?
得多順暢啊。
尤其剛從泉市回來的龍天寶,更是懵——這倆人不是如膠似漆嗎?盛公主大半夜都要跑出去買作案工。
這會就算是塊木頭,都能覺出二人之間的敵意。
怎麼沒敵意,當然有敵意——真晦氣,出來瀟灑還要看前夫/前妻的臉。
盛悉風第一時間就試圖擋住金的視線,但為時已晚,這傻狗已經發現江開了,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它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一邊上躥下跳,一邊沖他鬼。
哪怕竭盡全力保持表上的肅穆,但眾目睽睽之下,和一條興過度的狗拉拉扯扯,整的畫風可想而知,多有點稽,十分影響在前夫面前高貴冷艷的前妻形象。
“別裝。我看你這幾天吃得香睡得著,也沒惦記他。”好聲好氣跟金商量,“給我點面子,我給你加三天餐。”
Advertisement
金這時候哪管說什麼,見江開不回頭,以為自己鬧得不夠大,而且它是典型的人來瘋,十分萬眾矚目的覺,大家越看它,它越來勁。
盛悉風有點惱了,揪住它的耳朵,拜托它看清現實:“你看人家理你嗎?狗!”
金舞得更歡,一個猛撲,頸的鎖扣竟然松開了,它一個踉蹌,往前跌出幾步,回頭疑地看看掉落在地的繩子,又看看,再看看遠的江開。
在男主人和主人之間猶豫不決。
盛悉風來了氣,將繩子往它面前一扔,說:“這麼喜歡他,那你跟他走吧。”又補上一句,“不用回來了。”
語氣平和,但殺傷力十足,金一下子蔫了,迅速做出決斷——它選。
低眉順眼地走回來,挨在腳邊,蹭的小。
盛悉風氣還沒消,冷眼旁觀。
江開看不下去,淡聲質問:“你跟一條狗計較什麼?”
“這個好像不到你管吧?”盛悉風奇怪道。
狗是的,想怎麼養就怎麼養。
他要真的在乎,剛才狗子上躥下跳的,他怎麼舍得連眼神都不給一個?
大伙見況不對,連忙圓場,一窩蜂跟打起招呼,畢恭畢敬的“開嫂”。
盛悉風意識到江開可能還沒跟別人說過離婚的事,既然他沒說,總歸有他的顧慮,也不方便幫他公開,只是無論如何不想再冠以這個稱呼了。
“我沒有名字嗎?”
江開的呼吸微微一滯。
這一刻,他忽然真正意識到他們的離婚事實。
這種覺很奇怪,明明五分鐘前,他還在習慣地用“我老婆”來稱呼,用稀松平常的語氣說起的事跡。
跟他老婆的名頭綁了22年,無論他不愿,這個認知都已經深深植他的骨,他潛意識里一直知道,也早就默認。
Advertisement
可是不是的。
完全可以不是他的,也完全可以扔下他妻子的名頭。
還沒習慣離婚事實的人只有他,適應得很好。
固有認知一朝分崩離析,像舵手失去方向的把控。
這伙人多是江開的舊友,或多或聽說過盛公主的名頭和輝事跡,知道難搞,因而也不跟計較什麼,只當夫妻倆吵架,盛悉風鬧脾氣,于是打著哈哈附和:“是是是,您當然有名字,只是我們不配,不開嫂,那您盛士,盛公主,ladysheng,prcesssheng行了吧。”
配合了盛悉風“獨立人格”的需求,眾人繼續暖場子,招呼起盛悉風那幫朋友,他們不敢再霉頭,于是客套地請示趙夢真兩幫人要不要一起,順便跟匯報男朋友的行程:“峰子應該已經在來的路上了。”
趙夢真自然拒絕了拼場的提議,走過去小聲問盛悉風的意思:“你要是不想待,我們可以走的。”
“沒事。”盛悉風說。
難不離了婚,還得繞著他走?
要知道,本來甚至愿意大大方方跟他當個朋友的,誰他小心眼,還拿“炮-友”這種詞語侮辱純真的友。
有了老板的特許,金功被放行,侍者引著雙方去到各自的包廂,兩個包廂就在隔壁。
先后邁進不同的門,像走進兩個不同的世界。
包廂里k歌、牌桌、麻將桌、臺球桌等一應俱全,趙夢真胡點了幾首歌放原唱,怎麼想都覺得可惜,和盛悉風在前任面前的發揮都不夠出。
還沒把前男友等來,別的合伙人已經畢恭畢敬把狗請了進來。
至于盛悉風呢,雖說沒落下風,但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Advertisement
“早知道把任豪杰也上了,就不信氣不到你前夫。”
寢室幾個生一致認定任豪杰是個可以發展的對象,但盛悉風一直刻意和他保持距離,也不同意趙夢真他一起玩。
在的長過程中,和同齡男生的接不多,沒有特別要好的異朋友。離婚后,愿意去接一些別的異,當然不一定要發展人關系,順其自然就行,如果可以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很不錯。
但和任豪杰注定沒法順其自然,覺得力太大,更不想給人錯誤的信號和不靠譜的希,最后白白造傷害。
誠然,今天任豪杰在的話,江開應該會不高興。
從小學開始,他莫名其妙就對人家很有敵意。
“我對氣他沒興趣。”盛悉風慢慢說,“我現在,做什麼都不想以他為目的了。”
而隔壁包廂里,了幾個年輕的孩子陪玩。
龍天寶像母護崽子,把試圖坐到江開旁邊的生趕開:“離他遠點,他老婆在旁邊包廂。”
江開懶洋洋地倚在沙發里,笑看自己的護草使者一眼,但到底沒阻攔。
他懶得應付這些姑娘,而且他無比確信,這一次盛悉風真的不會管他了,哪怕他左擁右抱,大上再坐一個,看到了也不會多說他一句。
他終于擺了,這個小時候黏著他跑,無數次害他挨打挨罵,長大后斷他桃花,最后為他人生中最大枷鎖的麻煩,終于徹底放他自由了。
按理說,是件值得慶祝的事,可是他并沒有想象中的開心。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對盛悉風的非常矛盾。
一方面討厭、希離自己遠點,一方面卻總忍不住過度關注。
其實這很正常,人難免關注自己的敵人,時間久了,產生點奇奇怪怪的惡趣味和占有也不奇怪。何況他們一起長大,總有分在。
Advertisement
等到結婚的年紀,他早已談不上討厭,甚至如果不是而是別人,他絕無可能答應結婚,即便夢想的就擺在眼前。
因為是和,他才愿意出賣自己的婚姻。
只是多有點不甘心,那麼早、那麼年輕就塵埃落定,他甚至沒有談過一場真正的,沒有真正過,也沒有被真正過。一片空白。
他以為,比起舍不得,自己終歸是更希能擺的。
離婚后,他一面對的絕到負氣,一面解地想,也好,從此以后恢復自由,想怎麼玩怎麼玩,再沒有人壞他好事,他也不必有任何道德負擔。
離婚后的這幾天,每天和朋友尋歡作樂,當下也算得上愜意快活,只是一個人回到家,家里到都是盛悉風沒帶走的東西,的服,的鞋,的琴……
到都是的影子,可到都沒有。
那種無邊的寂寥便撲面而來,惹得他煩悶無比。
許是在申城,幾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和盛悉風離婚,他沒法放開手腳做自己。
所以為什麼不說呢?對所有的家人朋友守口如瓶,他并不害怕事捅出去,既然敢離,就敢面對后果,反正本來就不可能瞞家里一輩子。
又為何遲遲沒有離開,去異國他鄉奔赴徹底的自由?訓練任務那麼繁重,待在申城的每一天都是浪費。
他不知道。
有什麼東西,牢牢絆著他,讓他對這片土地產生強烈的留念,生怕這一走,就再也抓不住。
第五次和龍天寶干杯的時候,龍天寶實在忍不住,憂心忡忡地說:“哥,你和盛公主到底怎麼了?實在不行就過去求個和唄,男人嘛,跟老婆低個頭怎麼了。”
“廢話。”
他為什麼要低頭,有什麼可低頭。
要離婚的人是。
他自由了。
天大的好事。
趙夢真的男朋友來的時候,江開已經有些微醺。
“大家好,我韓旭峰。”韓旭峰沒有第一時間去找趙夢真,而是先過來江開他們包廂坐了會,他和在場不人都不,不過男人之間,幾杯酒就能稱兄道弟,并不尷尬。
經眾人介紹,韓旭峰才知道自己和江開還有一層伴同寢的淵源,他非常震驚,半信半疑道:“你是盛悉風的老公?盛悉風結婚了?真的假的?我和趙夢真在一起快半年了,我怎麼從來沒聽說過啊?”
他對趙夢真寢室幾個生都關照,和盛悉風也算識,從來沒聽到過半點風聲,而且前兩天他去過家慶祝喬遷之喜的時候,趙夢真還有給介紹男朋友的意思。
當然他不會傻到這種時候說這些,畢竟是別人的家事,多一事不如一事,他只當趙夢真也不知。
對于盛悉風在這段婚姻中的種種避嫌行為,江開早都已經聽麻了,他心下煩躁,卻不得不替善后,敷衍著解釋:“年紀小,害。”
韓旭峰敬過一圈酒,才站起道別:“我去我朋友那了,你們先玩。”
合伙人笑著拿了個骰子丟他:“去吧去吧,心不在焉的,早等不及了吧?”
“開哥要不要跟我一起過去?”韓旭峰順口邀請。
那一瞬間心頭有種說不上來的,像極了小時候討厭卻還想到面前刷存在的心態。
他抿了一口酒,搖頭。
眼看著韓旭峰的背影消失在門邊,醉意漸漸上頭,他對著重新闔上的門,一時出神。
龍天寶順著他的視線,向空的門,然后語不驚人死不休地來了句:“開哥,你是不是很嫉妒人家,可以名正言順見到盛公主?”
江開轉眼看他,瞇起眼睛,過了兩秒,直接摁著他的后頸把他摁進了沙發里。
龍天寶拼命掙扎,直喊“饒命”,等脖子上的桎梏松開,他迅速跑遠,跑到江開捉不到的地方,才敢控訴:“開哥你怎麼還惱怒,一點都玩不起!”
這一天,江開在距離盛悉風的一墻之隔的地方,一杯接一杯地喝酒,龍天寶不理他了,恰好他也不想別人來煩,兀自自酌。
直到有朋友唱了一首歌,他的心仿佛被什麼重重擊中,扭頭看向電視屏幕,那句歌詞已經一閃而過,卻深深烙印到他心里,一下灼傷到他。
那句歌詞唱道:“離開你以后,并沒有更自由。”
離開盛悉風以后,他沒有得到夢寐以求的自由。他什麼都沒能得著,只是一味失去。
失去了什麼,他一時想不通,只知道弄丟了很重要的東西。
又是幾杯酒下肚,他想起來了,他失去了他的狗。
他出門左轉,近乎本能地推開了隔壁包廂的門。
門開的一瞬間,他就覺到了清甜的氣息,所有的躁和不安都在這一瞬偃旗息鼓,像黃昏的雀歸塔。
宿命般不可抗拒的安全。
里頭的人齊齊看他,盛悉風正在和朋友們打牌,臉上還維持著笑意,眼見是他,眼底染上一層疑慮。
江開從中讀出的不歡迎,可他有他的正當理由。
“我至有狗的探視權吧?借我玩會。”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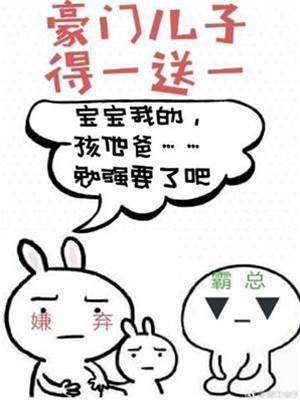
豪門兒子得一送一
別人去當后媽,要麼是因為對方的條件,要麼是因為合適,要麼是因為愛情。 而她卻是為了別人家的孩子。 小朋友睜著一雙黑溜溜的大眼,含著淚泡要哭不哭的看著林綰,讓她一顆心軟得啊,別說去當后媽了,就算是要星星要月亮,她也能爬著梯子登上天摘下來給他。 至于附贈的老男人,她勉為其難收了吧。 被附贈的三十二歲老男人: ▼_▼ ☆閱讀指南☆ 1.女主軟軟軟甜甜甜; 2.男主兒砸非親生; 3.大家都是可愛的小天使,要和諧討論和諧看文喲!
31.8萬字8.33 47271 -
完結72 章

心機女的春天
韓熙靠著一張得天獨厚的漂亮臉蛋,追求者從沒斷過。 她一邊對周圍的示好反應平淡,一邊在寡淡垂眸間細心挑選下一個相處對象。 精挑細選,選中了紀延聲。 —— 韓熙將懷孕報告單遞到駕駛座,意料之中見到紀延聲臉色驟變。她聽見他用浸滿冰渣的聲音問她:“你設計我?” 她答非所問:“你是孩子父親。” 紀延聲盯著她的側臉,半晌,嗤笑一聲。 “……你別后悔。” 靠著一紙懷孕報告單,韓熙如愿以償嫁給了紀延聲。 男人道一句:紀公子艷福不淺。 女人道一句:心機女臭不要臉。 可進了婚姻這座墳墓,里面究竟是酸是甜,外人又如何知曉呢?不過是冷暖自知罷了。 食用指南: 1.先婚后愛,本質甜文。 2.潔黨勿入! 3.女主有心機,但不是金手指大開的心機。
22.8萬字8 6822 -
完結857 章

重生九零肥妻歸來
中醫傳承者江楠,被人設計陷害入獄,臨死前她才得知,自己在襁褓里就被人貍貓換太子。重生新婚夜,她選擇留在毀容丈夫身邊,憑借絕妙醫術,還他一張英俊臉,夫妻攜手弘揚中醫,順便虐渣撕蓮花,奪回屬于自己的人生。
159.8萬字8 97590 -
完結523 章

重生蜜戀:偏執九爺他淪陷了
前世,云漫夏豬油蒙心,錯信渣男賤女,害得寵她愛她之人,車禍慘死!一世重來,她擦亮雙眼,重啟智商,嫁進白家,乖乖成了九爺第四任嬌妻!上輩子憋屈,這輩子逆襲!有人罵她廢物,醫學泰斗為她瑞殺送水,唯命是從,有人嘲她不如繼姐:頂級大佬哭著跪著求她叫哥!更有隱世豪門少夫人頭街為她撐腰!“你只管在外面放建,老公為你保駕護航!”
88.6萬字8.18 140070 -
完結167 章

聖佛子人設崩了,原是寵妻狂魔
【強製愛 男主偏執 雙潔】南姿去求靳嶼川那天,下著滂沱大雨。她渾身濕透如喪家犬,他居高臨下吩咐,“去洗幹淨,在床上等我。”兩人一睡便是兩年,直至南姿畢業,“靳先生,契約已到期。”然後,她瀟灑地轉身回國。再重逢,靳嶼川成為她未婚夫的小舅。有著清冷聖佛子美譽的靳嶼川,急得跌落神壇變成偏執的惡魔。他逼迫南姿分手,不擇手段娶她為妻。人人都說南姿配不上靳嶼川。隻有靳嶼川知道,他對南姿一眼入魔,為捕獲她設計一個又一個圈套......
29.1萬字8.18 45878 -
完結150 章

垂涎你許久
【破鏡重圓+強取豪奪+雙潔1v1】向枳初見宋煜北那天,是在迎新晚會上。從那以後她的眼睛就再沒從宋煜北臉上挪開過。可宋煜北性子桀驁,從不拿正眼瞧她。某次好友打趣他:“最近藝術係係花在追你?”宋煜北淡漠掀眸:“那是誰?不認識。”後來,一個大雨磅礴的夜晚。宋煜北不顧渾身濕透,掐著向枳的手腕不肯放她走,“能不能不分手?”向枳撥弄著自己的長發,“我玩夠了,不想在你身上浪費時間了。”……四年後相遇。宋煜北已是西京神秘低調的商業巨擘。他在她最窮困潦倒時出現,上位者蔑視又輕佻的俯視她,“賣什麽價?”向枳躲他。他卻步步緊逼。無人的夜裏,宋煜北將她堵在床角:“說你後悔分手!”“說你分手後的每個日夜都在想我!”“說你還愛我……”四年後的宋煜北瘋批難纏,她嚇到想要跑路。逃跑時卻被宋煜北抓回。去民政局的路上,她被他紅著眼禁錮在懷裏:“再跑,打斷你的腿!”
25.4萬字8 85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