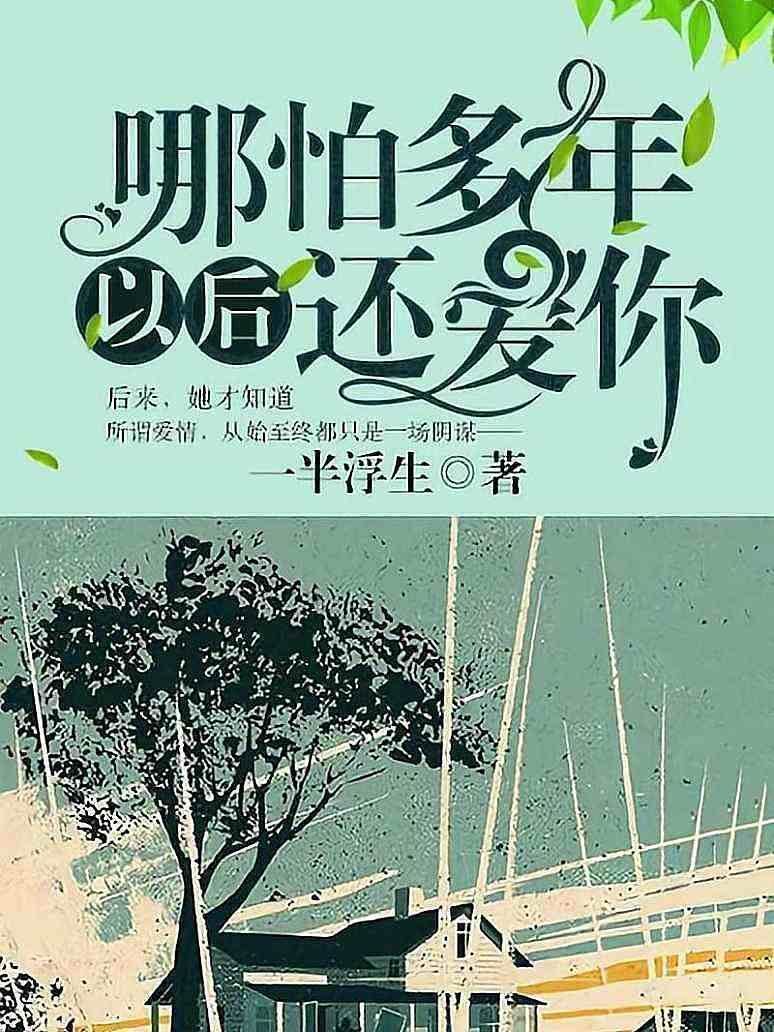《我的婆婆是重生的[七零]》 第84章 壞主意
莊志希覺得自己最近多有點倒霉。
這總是能遇到腦殘患者,還要被牽連。
一大早的,他就配合了一場,下午又被保衛科過去了。這一次,是白斗的“供詞”。白斗這個人,就沒什麼心眼,這不,事一鬧大了也不會撒謊,直接就自己的打算說了出來。
正因此,保衛科來找莊志希再次核實,莊志希的臉黑的像是黑炭。
張三兒和李四兒對視一眼,又齊刷刷的去看劉科長,劉科長也在留意莊志希,想看出莊志希是不是早就知道這件事兒,從而故意的引周群過去。
雖然這個可能不大,但是也是有的。
不過莊志希看起來這麼生氣,這個可能就降低了。他確實就像是剛知道這件事兒,一張臉黑的不像樣,他看到莊志希放在桌上的手都攥起拳頭了,仿佛如果白斗在他邊,他直接都能打人。
莊志希似乎氣了好久,終于平復心抬頭說:“第一,我不知道他的打算,確實,他在水房的時候曾經堵過我,說找我有事兒,但是也不說什麼事兒,我就沒多理他,很快的離開了。第二,他說中午跟我好了……”他嗤笑一聲,說:“這就是撒謊了,你們可以去我們科里問一問,我中午一直都跟科里人一起去吃午飯的,就沒跟他有過接,一句話都沒有說過。他白斗想用我來做擋箭牌,掩蓋自己干的那些惡心事兒,我可不會配合。別以為是鄰居我就得無條件幫他,他算老幾啊!”
莊志希黑著臉說:“這件事兒,如果他是真的有心算計我,那麼我覺得他活該被人踹碎蛋;如果這件事兒里本沒有我的事兒,他想把我拉進來當擋箭牌,推自己的無辜,不好意思,我不配合。讓他去死吧。”
Advertisement
張三兒看莊志希氣的不行,趕安他:“你別生氣了,我們知道白斗這事兒做的不地道……”
莊志希冷笑:“不地道?他是做事兒不地道嗎?他是卑鄙無恥,我以前怎麼不知道他這麼多心眼呢。咱就不說后一種可能,咱就說前一種,我就想問問,我怎麼得罪他了。我他媽跟他本沒有什麼過節啊!”
這話一說,保衛科一個個都呃了一聲,有點不知道怎麼說了。
張三兒:“白斗說,你們家欺負王香秀兒子……他就想報復報復。”
莊志希不可置信:“臥槽,那王香秀兒子來我家東西被我大嫂抓個正著,我們還不能去他家門口罵幾句了?擱了脾氣不好的早揍他們家孩子、砸他們家玻璃了,我們家已經夠可以了。真是倒了八輩子霉,遇到這種鄰居。你要是這麼說的話,那他想算計我有可能是真的。畢竟我也不覺得他敢大膽的大白天的就對姜蘆圖謀不軌,有賊心也干不出這個事兒啊。”
保衛科眾人紛紛點頭,其實大家跟白斗同事了十幾年,多也還是有點了解的。白斗這個人雖然不著調的蔫壞,整天想著找媳婦兒。但是這人屬實對自己沒有一點避暑,屬于那種十分自我覺良好的,在他心里,就算是配一個天仙兒都是可以的。凡夫俗可不是他的考慮范圍。
姜蘆條件是好,但是已婚,且沒有孩子,在白斗的眼里,恐怕都算是配不上他的了。
要說真是要對人干點什麼,他們保衛科都覺得可能不大。現在據白斗的代,他是為了報復莊家,那就很有可能了。
莊志希:“草,我真是叉叉他八輩祖宗,他家人怎麼就能缺德這樣,他包庇小還有理了?媽的這是什麼東西啊,還想算計我。哎不對……他算計我歸算計我,拉扯人家姜蘆進來干啥?”
Advertisement
他疑的皺眉,問了出來。
張三兒:“……”
他幽幽說:“他說看周群不順眼,加上周大媽整天欺負蘇家,他想著見義勇為,給他們家一個沒臉。”
莊志希:“……”
他呵呵冷笑,說:“真是搞破鞋搞得地山搖。”
張三兒:“來來,你喝點水,也別生氣。”
莊志希:“我能不生氣嗎?如果我真的中計了,你說我現在是個什麼況?他這是喪盡天良啊。真是活該碎了,活該!!!”
莊志希起,說:“還有事兒嗎?沒有我就回去了,實在不想聽白斗那些惡心人的事兒了。這玩意兒腦子讓野狗吃了,腦殘。”
“噗!”幾個保衛科的沒忍住,笑了出來。
這時劉科長咳嗽一下,說:“行了,我再問你最后一件事兒,你沒答應他?”
莊志希氣沖沖的:“我答應他媽!我本就沒跟他說話!有本事你給他來,我們對質,我們現場對質,看我到底答沒答應他!”
“你好好說話,發什麼火。”
莊志希:“這擱誰不發火?劉科長,如果事真是他自己代的這樣,那麼也該理吧。他這是栽贓陷害,你們不能因為我沒有中計就不當一回事,如果我真的中計,那麼我現在還能坐在這里說話嗎?我怕是已經去蹲笆籬子了吧?我會不會白斗這麼好的待遇,可說不好。”
他意味深長:“白斗是保衛科的人,本來就應該更加的以作則,他應該比別人更懂事的嚴重,可是他做的還是毫無遲疑,那麼不嚴懲都不足以讓我們普通的群眾安心了吧?他今天能遷怒我們家,明天一樣也能遷怒其他人。他今天看完不順眼就搞了這麼大的事兒,那麼明天看廠長不順眼,是不是還能去人家放一把火?或者是把廠長跟寡婦關在小倉庫?那麼是不是以后看誰不順眼都能構陷一下了?”
Advertisement
他也不提白斗出保衛科,劉科長會護犢子,這樣就是徹底得罪劉科長了。但是該說的,他也不會畏畏的。一個男人要是畏畏,那也只會讓人看不起。
“他不會這麼大膽的。”劉科長蹙了眉,也是心累。
莊志希笑:“那他想構陷我的時候,您能想出來他敢做這種事兒嗎?恐怕也是想不到的吧?有些人雖然看著不像是心眼多,但是就是蠢人做事兒才更莽。你本不知道,他腦子一下一次能干什麼。”
劉科長若有所思起來。
其他人用力點頭,這話形容白斗,再切不過了,果然還是老鄰居,彼此了解的很啊。
劉科長:“這件事兒你放心,廠子里也會給你一個代的。”
莊志希苦笑一下,說:“我還真沒想到這事兒能跟我有關系,但是既然他都這麼干了,不管是真的還是他只是想找個借口推,我都不能原諒這個人。”
停頓一下,他說:“我先回去了。”
莊志希起,這一次劉科長倒是沒說什麼,眼看莊志希走了,劉科長罵道:“你說白斗這個癟犢子干的都是什麼事兒,真是給我們保衛科抹黑。”
張三兒:“我看小莊真不知道這事兒……”
李四點頭,他說:“科長,你說白斗是真的打算算計莊志希,還是本沒有想要算計莊志希,就是相中了姜蘆,想占便宜呢?這被發現了,他才說自己想要算計莊志希,畢竟這陷害同事鄰居還能推是開玩笑。但是對婦圖謀不軌,可就要進去了,嚴重的可能都要蹲笆籬子。”
雖說他們比較相信白斗不至于,但是又一想,確實白斗這個人有點莽,這莽過頭了,人難免犯蠢。
Advertisement
人啊,就怕沖,一時沖,也未必不可能。
“人心隔肚皮,誰知道呢。雖然我們所有人,甚至包括莊志希都相信他可能確實是要針對莊志希。但是還真是不能全然相信,首先他本沒找莊志希過去,這個莊志希有證人,而且他敢對質,我相信他沒撒謊。再說,就算是白斗找了,莊志希沒去,他為什麼還要躲在里面等著姜蘆呢?這是最關鍵的。”
“對,不管是他找沒找莊志希,莊志希都沒去,他還躲在哪里,還是把姜蘆弄進了門,真的不太值得被相信。再說他說自己是因為莊家針對蘇家想報復,這個理由也站不住腳。王香秀的兒子是小,本來就是錯。人家連手都沒有,怎麼就要報復了?那要是這樣就報復,他也該報復當時的當事人,也就是莊志希的嫂子啊。”
“可不是嗎?”
“他應該還是對姜蘆有意思,故意想大事化小。”
劉科長點頭:“我覺得也應該是這樣,他應該還是抓住了莊志希的心思,你看莊志希自己都覺得,白斗是有可能因為這件事兒報復他的,因為白斗沖。可能他就是利用了大家的這個想法,所以對姜蘆圖謀不軌。我們都覺得他眼高看不上姜蘆,可是這又不是讓他跟姜蘆結婚。他占個便宜,真的出事兒,姜蘆為了面子也未必敢出聲報警的。”
“對對對。”
劉科長覺得,自己看了真相,不得不說,明人總是要給事想的復雜,劉科長恰恰就是如此了。而保衛科的其他人也覺得,這樣才最有道理。
不然的話,沒法兒結束莊志希沒去,他們還是把姜蘆推進門啊。
這是一個套路,肯定是一個套路。
保不齊,他先去找莊志希,就是給自己事敗做一個應急的預案,可能,這可太有可能了。
沒想到這老小子還明。
劉科長這麼一分析,張三兒開了口:“科長,你也別覺得白斗傻,他是看起來比較莽心眼不多。可是他也從來都不吃虧啊。就算是在咱們保衛科,你看他的活兒也干的不多啊。”
工資不拿,活兒干得,晚上要值班的活兒,他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這麼一想,誰敢說這個人沒心眼?
“你這說的倒是有點道理。”
劉科長:“這混球兒現在還敢跟我玩心眼,我看他是不知道馬王爺三只眼。”
王二癩子神兮兮的低聲音說:“科長,保不齊這個事兒,真的能大事化小。”
“怎麼?你看我是那樣的人?我這人最是……”
“不是不是,我當然不是說您,我是說那誰,就是那個王香秀,今天一天都在糾纏周群,我們都看到了,肯定是給白斗求啊。如果周群夫妻改口說白斗是開玩笑,這事兒還不就大事化小了?”
劉科長:“什麼玩意兒?”
他抓了抓頭發,覺得自己真是不理解這些人,這都干的什麼事兒啊。
他說:“這他媽……”
“咱們等等看吧。”
“就是啊。”
劉科長:“呸!”
保衛科熱鬧一片,莊志希出了保衛科,面容發黑,臉十分難看,他面無表的回到辦公室,正好也到了下班時間了。崔大姐好奇的湊過來,問:“小莊,咋回事兒啊?”
莊志希并沒有瞞,大概說了說。
這事兒他瞞不瞞的,意義也不大,因為就算他不說,保衛科也要說。索,莊志希直接就說了事的大概。聽得大家目瞪口呆,說:“什麼玩意兒,這人怎麼這樣啊?”
“哎不是,他對王香秀還真是真心啊。”
“深似海,一般夫妻都沒這麼不顧的。”
“嗐,為什麼你們都覺得他說的是真話呢?也有可能是假話啊!如果真是定下來流-氓-罪,那多嚴重啊。但是他要是把事往別的地方扯,可能就沒有那麼嚴重了。雖然構陷同事也嚴重。但是到底沒功不是?這事兒就不算大,我看啊,他那話就是推。就是故意給自己找補的臺階。”
“有可能。”
“什麼有可能,就是這麼回事兒。”
“小莊你也倒霉,遇到這麼個不著調的鄰居。”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6 章

他只對她溫柔
你已經是我心臟的一部分了,因爲借走的是糖,還回的是心。—— 宮崎駿 文案1: 請把你的心給我。—— 藍晚清 當我發現自己愛上你的時候,我已經無法自拔。 —— 溫斯琛 愛上藍晚清之前,溫斯琛清心寡欲三十年,不嗜賭,不.好.色。 愛上藍晚清之後,溫斯琛欲壑難填每一天,賭她情,好.她.色。 文案2: 在T大,提起生物系的溫教授,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姓溫,但人卻一點溫度都沒有,高冷,不近人情,拒人千里。 但因爲長得帥,還是不少美少女貪念他的美色而選修他的課,只是教訓慘烈,一到期末,哀嚎遍野。 後來,大家都明白了,溫教授?適合遠觀,不適合褻玩。 然後,學校貼吧一個帖子火了,「溫教授性子冷成這樣,做他女朋友得有多慘?」 底下附和聲一片—— 不久,學校貼吧另一個帖子也火了,「以前說心疼溫教授女朋友的人,臉疼嗎?」 底下一溜煙兒的——「疼!特碼的太疼了!」
19.7萬字8 16870 -
完結569 章

閃婚后發現老公是首富大佬
霍斯宇人帥多金,性格冷清。 本以為自己嫁了個普通人,沒想到對方竟是隱藏大佬,身家千億。 關曉萱慫了,她只想過平凡的生活。 霍斯宇將人緊緊圈在懷裡,語氣喑啞: “想跑? 你已經嫁給我了,這輩子都跑不掉! ”
62.8萬字8.09 194371 -
完結572 章

神秘愛人:總裁,晚上見
老公背著她在外養小三,婆婆竟打算讓小三代替她生子?士可殺不可辱,所以她也光榮的出軌了。只是她萬萬沒有想到,那男人竟然是她老公的…… 離婚之日,便是她訂婚之時,她簽完離婚協議,轉身嫁給了全城最有名的富二代…… 他一步步逼緊:“女人,只要寶寶不要爹,你說我要怎麼懲罰你才夠……”
98.9萬字8 85239 -
完結2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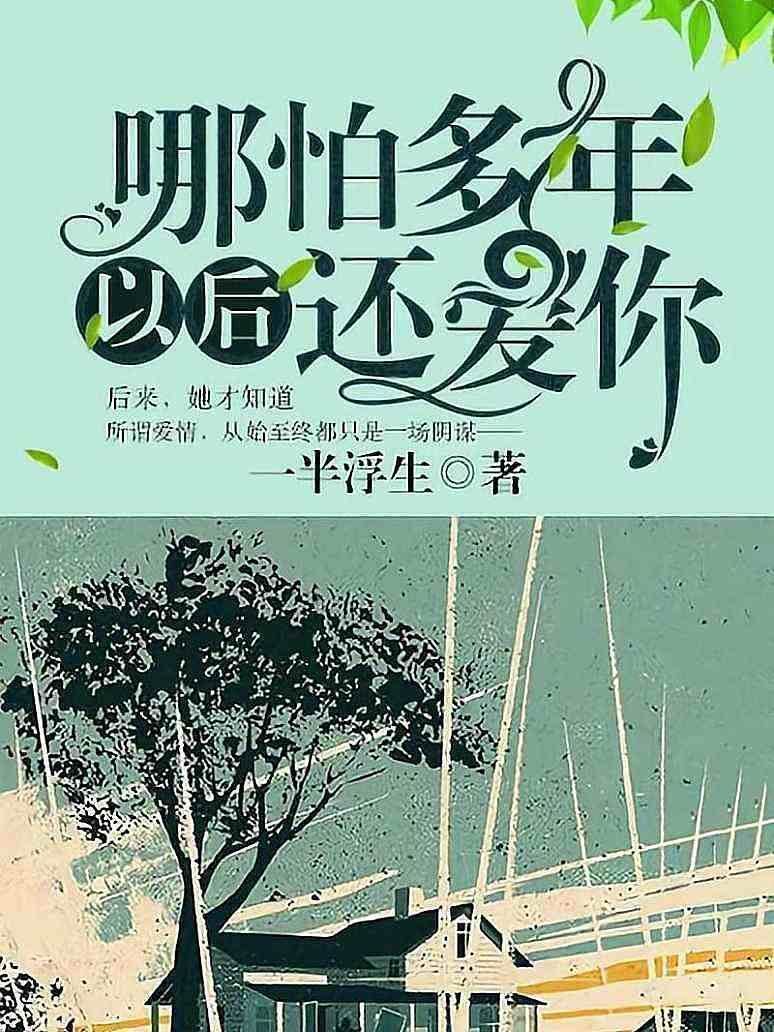
哪怕多年以后還愛你
“生意麼,和誰都是談。多少錢一次?”他點著煙漫不經心的問。 周合沒有抬頭,一本正經的說:“您救了我,我怎麼能讓您吃虧。” 他挑眉,興致盎然的看著她。 周合對上他的眼眸,誠懇的說:“以您這相貌,走哪兒都能飛上枝頭。我一窮二白,自然是不能玷污了您。” 她曾以為,他是照進她陰暗的人生里的陽光。直到最后,才知道,她所以為的愛情,從頭到尾,都只是一場陰謀。
107.8萬字8 3589 -
完結64 章

網戀到一見鐘情對象的下場
【雙男主+一見鐘情+雙向奔赴+HE】【霸總攻江野×音樂主播受宋時慕】 小透明音樂主播宋時慕是音樂學院的一名優秀大學生,直播間常年蹲守一位忠粉,次次不落地觀看直播,準時打賞高額禮物。 線下見面時,宋時慕發現這位忠粉竟然就是他在開學典禮上碰見的一見鐘情的對象~ 【小劇場:直播間高呼讓主播賣萌。 宋時慕無奈捂臉,擺手強調三連:“主播是正經人,主播不會賣萌。” 忠粉江野:“真的?那昨天晚上向我撒嬌的是誰?” 直播間內:“哇哦~”】
11.5萬字8 3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