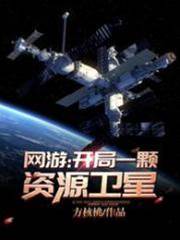《在古代打更的日子》 第41章 第 41 章(捉蟲)
六馬街,碼頭。
樟鈴溪的江水一下下的拍著河岸。
“呼,澎,呼,澎……”
風聲裹挾著水浪的聲音,落在耳邊格外的深沉。
江面零星幾艘烏篷船,沒有客人,載客的艄公在船艙里閉目休息。
江水悠悠,船兒晃晃,當真是得浮生半日閑。
顧昭和趙家佑遠遠的墜在陳牧河后。
陳牧河行進的方向確實是六馬街的碼頭,但在臨近碼頭時,只見他拐了個彎,轉進了碼頭旁邊的小路,鉆進林中。
隨著影幾個錯,陳牧河的影被樹木遮掩,不見蹤跡了。
“哎哎,怎麼辦,他人不見了。”
趙家佑扯了扯顧昭的袖,著急不已。
顧昭的眼睛瞅著前方,頭也不回道。
“我瞧見了,不打,他估計是去取船了,咱們盯著江面就。”
趙家佑看著河堤兩旁的林,憂慮不已。
“要是跑了再去哪里找,不然咱們也跟進林子里吧。”
“不可!”顧昭連忙出聲拒絕。
“林里頭土地,長蟲頗多,這季節長蟲剛剛出,兇著呢!再說了,里頭樹木多藤蔓也多,咱們跟近了容易被發現,跟遠了還容易跟丟人。”
見趙家佑還是不放心樣子,顧昭繼續道。
“家佑哥,你就放心吧,他想要離開玉溪鎮,除了走水路便是走陸路,既然來了這個方向,那定然不可能是藏了馬的。”
樟鈴溪常年水漲水落,河堤這一片的林時常被江水浸潤,土壤,偏生又長了天生天養的河枷藤。
整個林子得很,連他們玉溪鎮的人都不稀罕走。
里頭除了長蟲還有許多的蚊蟲。
這時候的蚊子毒得能咬死一頭大黃牛,又怎麼能藏得住一匹活生生的駿馬?
Advertisement
顧昭:“馬兒又不是人,懂得忍藏,要是被蚊蟲咬得厲害,那靜大了去了。”
趙家佑聞言連連點頭。
“此言有理。”
他按捺下耐心,跟著顧昭朝樟鈴溪的江面眺。
顧昭和趙家佑站的這個位置頗好,此是河凹岸,放眼朝江面看去,不拘是哪個方向有船出來,都是十分顯眼的。
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約莫過了一柱香后,左面的江面有一艘船出來了。
顧昭凝神看去,沉聲道。
“出來了。”
趙家佑順著顧昭的視線看去,果然,那兒一艘又窄又深的烏蓬小船。
撐船的艄公頭戴一頂斗笠,他站在微微翹起的船尾,手上的竹蒿一個用力,船兒借著水流和風力,嗖的一下劃遠了。
長長的水波在烏篷船后漾開。
艄公一個轉,落在他的面龐上,正好讓顧昭和趙家佑瞧清楚艄公臉上的絡腮胡子。
顧昭眼力好,當下連他面上的神都看清了。
“嘖,心真不錯,上還哼著小曲兒呢。”
趙家佑踮腳,“是他嗎?裳的和方才不一樣了。”
顧昭點頭,“是他!”
“裳裝扮換了,這胡子可沒換,胡子留這樣,咱們就是想昧著良心說不是他都不啊。”
趙家佑點頭,這倒也是。
他看著顧昭燃了三柱清香,煙氣化作白鶴,飛鶴傳信,不過是片刻時間,碼頭邊的河面上憑空出現了一艘竹排。
顧昭一個縱,作利落的躍上竹排,竹排在水中微微漾了漾,一圈圈波紋隨即漾開。
趙家佑也跟著上去了。
只見顧昭手中長蒿一撐,竹排悠悠往前。
趙家佑左看右看,想著尋一竹篙,不想除了顧昭手中那,整個竹排上別無他。
Advertisement
失的趙家佑不免小聲嘀咕道。
“仙妹妹也忒小氣了,怎麼就只借了一長篙過來。”
顧昭:“一就夠了。”
接著,趙家佑便發現了,江波中,竹排雖然悠悠晃晃,行進的速度卻著實不慢。
不過是一盞茶的功夫,竹排悄無聲息的進了胡子矮漢的烏篷船,一前一后相隔幾米綴著。
烏篷船上的胡子矮漢卻無一察覺。
趙家佑閉了。
是他笨了,金仙的竹排,那和他家老爹扎的竹排能一樣嗎?
離得近了,顧昭朝胡子矮漢面上瞧了瞧,神若有所思。
“……難怪留了這麼一大把胡子。”
趙家佑不解:“嗯?”
他做了個型,“顧小昭,我能說話嗎?”
顧昭點頭。
趙家佑呼了口氣,隨便說了兩句話后,見烏篷船上的艄公沒有一一毫的察覺,拍了下手,樂呵道。
“神奇!”
顧昭停了竹蒿,讓竹排不遠不近的跟著。
金仙為竹娘,扎的竹排帶著竹娘的妖炁,妖鬼迷心,炁行而上,自然遮掩藏了坐在竹排上方的顧昭和趙家佑。
船行間,兩岸的景不斷的往后。
樟鈴溪江波浩渺,等船兒到了大河江域的時候,兩邊的島嶼也了許多。
很快,趙家佑便無聊了,手了水花。
烏篷船上,陳牧河無意間瞥了一眼,眼睛倏忽的瞪大了一些。
只見江波上無端的出現了一只手江水,那手有些黑,有些胖,不過是眨眼間便又不見蹤跡。
陳牧河慌神了,了下眼睛,自言自語道。
“是我眼花了吧!”
他疑神疑鬼的四探看了下,江波浩渺,除了流水潺潺,哪里還有什麼黑胖手江?
雖然如此,陳牧河的后背上,還是不可抑制的爬起一層層皮疙瘩。
Advertisement
青天白日的,他的額頭上沁出了豆大的冷汗。
陳牧河很想說是自己眼花了,但為榮門的高手,甚至可以稱為是高買的角,陳牧河對自己的眼力還是很有自信心的。
不夸張的說,一只蚊子從他面前飛過,他都能辯出到底是公還是母!
顧昭和趙家佑:……
兩人沉默的看了一眼胡子矮漢。
只見他從慌神到鎮定,只用片刻的時間。
只是那劃得飛快的槳擼了他心底的不平靜。
倏忽的,陳牧歌像是想起了什麼,轉進了船艙,從行囊里拿了一個事掛在脖頸上,這才松了口氣。
趙家佑臉上神訕訕:“原來,把手出竹排就會被瞧見啊。”
“是啊。”顧昭也在慶幸:“還好還好,家佑哥,你剛才要是了頭出去,肯定更嚇人!”
趙家佑:……
……
因為嚇到了人,趙家佑的手腳不敢再了。
他的目落在陳牧河脖子的紅繩,又問道。
“他尋了什麼東西掛上啊。”
顧昭:“是一張驅鬼符。”
瞧胡子矮漢脖頸那符箓散發的瑩,顯然是有道行的人畫出來的。
……
趙家佑和顧昭兩人不是鬼,這符箓對他們自然是不管用,但對河里其他的東西就管用了。
符箓掛在脖子上,陳牧河的膽氣壯了起來,肩上那三把火瞬間燃得更旺了。
他環顧了下河面,正好這時一個黃梨木小匣子打江面飄過。
木匣子有些陳舊,常年在水里浸泡,上頭的紅漆有幾分腐朽斑駁。
但那匣子雕刻得十分巧,上頭一副百子戲耍圖,每一個小人都十分的活靈活現,憨態可掬。
可以想見,這匣子定然是大家之,讓人不好奇,這木匣子里是不是裝了什麼寶。
Advertisement
陳牧河卻眼睛一沉,怒目朝那匣子瞪去,叱咤道。
“滾!我是不會撿的,你個鬼東西給我滾遠一些!”
話才落地,就見原先漂浮在樟鈴溪江面的木匣子抖了抖,隨即緩緩的沉了下去。
太高高掛著,陳牧河的心就像那被擂的黃皮鼓,嘭嘭,嘭嘭,嘭嘭,劇烈的跳個不停。
陳牧河抹了一把臉,咒罵道。
“呸,死東西!也不打聽打聽老子是誰!還敢嚇我,回頭我連你的墳都掘了!”
……
烏篷船行進越來越快,瞧不見的竹排也不遠不近的綴著。
竹排上,趙家佑瞠目結舌,他的心也跳得很快,轉過頭去看方才木匣沉下的地方,說話都有些結了。
“顧小昭,剛,剛剛這是怎麼回事,怎麼那人說了一句話,那木匣子就沉下去了?”
這一前一后的,他就是想欺騙自己說是巧合都不。
顧昭也回頭看了一眼。
江水悠悠,煙波浩渺,隨著船行而過,木匣子沉水留下的痕跡早已經消失不見,江面一片的平靜。
“這是水鬼的障眼法,水鬼迷心,時常會頂著一個看過去值錢的東西漂浮在江面上。”
“要是有人心生貪婪去打撈,就會被水鬼拽了下去。”
嗖!
趙家佑立馬收回了手,正襟危坐的坐好。
顧昭繼續解釋道。
“剛才這位胡子大叔符箓有符力,再加上他膽氣足,火旺,又一語道破了水鬼的迷心計,水鬼自然悻悻離去。”
這也是坊間中常說的,鬼有三技,一為遮,二為迷,三為嚇。
陳牧河雖然做人不行,到底是行走江湖的,也不知道做了多惡事,是否沾了也不知。
這等惡人,便是鬼瞧見了都怕沾染的。
欺善怕惡,鬼和人是一樣的。
趙家佑收回目:“我只聽我阿說過水鬼魚,沒有聽過這個。”
顧昭:“嗯?”
趙家佑:“我阿以前不讓我們去碼頭附近玩,時常嚇唬我們,說是河堤旁的活魚不能撿,那是水鬼幻化,引著我們下河,現在看來,這事也是真的。”
顧昭點頭應和了下,“形式不一樣,本質是一樣的,都是鬼計中的迷。”
趙家佑又盯著烏篷船上的胡子矮漢多瞧了兩眼,目重點落在他脖頸上掛的符箓上,來了興致。
“嘿!他這麼一喝聲,那水鬼就沉了下去,看來這符箓威力很大嘛。”
顧昭:“不止這個符箓,他應該還得到過高人的指點。”
“方才遠遠的沒有瞧清楚,眼下這麼一看,這位大叔年輕時可能是破了一次很大的財。”
瞧那模樣,說不定還是人財兩失。
趙家佑:“怎麼說?”
顧昭:“你看他的下,尖而細瘦,鼻孔卻大,在鼻翼有一道深疤,《麻相學》里說了,這鼻子是財帛,問富在鼻。”
“財帛都破了,可不就是失了大財了?”
“再加上他這鼻孔,還有那下,這是典型的萬千金沙淌手過,細抓卻空的面相。”
“嘖,富貴容易卻留不住財,這一臉的絡腮胡子,尤其是人中位置,這都是為了留財蓄起來的。”
趙家佑懷疑了,“真的嗎?”
“顧小昭你準不準啊?”
顧昭攤了攤手,不負責任道,“不知道,我也是書里瞧的,不然你回頭問問他,就知道我算得準不準了。”
趙家佑拊掌,“好好,一會兒我定然要問他一問!”
“顧小昭,你也給我算算吧。”
顧昭拒絕,“不要!”
趙家佑不痛快了,“為什麼不要!”
“是不是坊間的說法,什麼命越算越薄,又或者是好命扛不住三回算?顧小昭,你幫我算算吧,我不怕!”
趙家佑就差嘭嘭拍膛保證了。
顧昭:
知道了還要問。
睨了他一眼,涼涼道。
“我給你算了,你有銀子給卦金嗎?”
趙家佑:
他想了許多緣由,沒想到居然是這個原因!
一時間,趙家佑瞧著顧昭的眼神都哀怨了。
“你我兄弟,生死與共數回,我和你說分,你卻和我談錢,我這顆心啊,就似被那尖刀渾絞,真是痛煞小子也!”
顧昭:
讀書果真有用,瞧瞧,家佑哥都能說痛煞小子了!
“你又不是第一天認識我,我這人就這樣,郎中兼著開棺材鋪子,活要錢,死也要錢,誰讓我這般窮呢!”
“你!算了算了。”
趙家佑瞧著顧昭的樣子,頹然敗走。
日頭一點點偏西,顧昭時不時化炁為風,掌風徐徐的朝烏篷船吹去,陳牧河覺得除了方才那一個驚嚇,他這一路順暢極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451 章
左道傾天
是非誰來判定,功過誰予置評?此生不想規矩,只求隨心所欲。天機握在手中,看我飛揚跋扈。————我是左小多,我不走尋常路。
407.7萬字8 24101 -
完結108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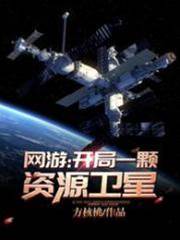
網遊:開局一顆資源衛星
2049,各國政府推出虛擬遊戲‘全民戰爭’,以遊戲中資源兌換的積分,將人劃分爲三六九等。陳風開局獲得超級寶物:資源衛星!“叮!山穀發現良田萬畝!”“叮!高山發現大型金礦一座!”“叮!平原發現特殊資源:馬群!”“恭喜玩家招攬絕世武將呂布,項羽,楊再興,諸葛亮......”“恭喜玩家訓練特殊兵種虎豹騎!”憑藉寶物,陳風建設城鎮,訓練士卒,招攬武將,吊打各路玩家,NPC勢力,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敗之路。各位書友要是覺得《網遊:開局一顆資源衛星》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臉書和推特裡的朋友推薦哦!
209.3萬字8 28813 -
完結1719 章

武道成皇
天星大陸,武道為尊,弱者淪為螻蟻,而強者凌駕於天地之間,少年身攜天火,逆天而為,踏海碎山,順者昌,逆者亡,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319萬字8 36957 -
連載81 章

我有一個諸天模擬器
蘇玄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能夠穿梭諸天萬界,並且覺醒模擬係統,可以無限模擬自己未來的人生。大周世界:有道君掃遍世間魑魅魍魎,威臨天下一甲子,名傳後世三千年,俯仰天地,古今無雙。大炎世界:有帝王窮極天下,鑄造無盡長城,北禦蠻荒獸潮,斬落九十六尊大妖王,功德無量。星空世界:有神話種肉身橫渡無垠宇宙,神火萬萬年不滅,視星辰為玩物,不老不死,舉世皆寂。......洪荒世界:有聖人口含天憲,謀天算地,無量無
17.7萬字8.18 7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