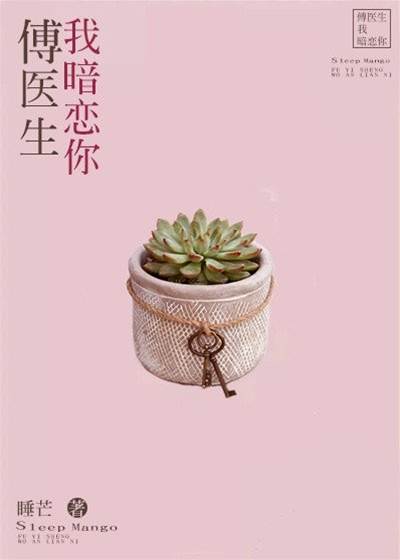《偷風不偷月》 第40章 第 40 章
許遼繞進吧臺, 調了兩杯青檸水,問:“查什麼?”
項明章想了想:“一支地下搖滾樂隊。”
許遼說:“怎麼會跟樂隊扯上關系?”
“別管那麼多。”項明章端起杯子,“無置樂隊, 貌似已經解散了, 查一下那些人都在哪, 尤其是一個張徹的。”
許遼記下來,靜了片刻,問:“你媽最近怎麼樣?”
項明章道:“老樣子。”
許遼點點頭, 又過了一會兒, 說:“你不打算問問我在國辦的事?”
項明章口氣輕蔑, 眼底盡是涼薄:“項瓏要是病了死了, 你早就越洋跟我匯報了,既然沒有, 我關心他干什麼。”
許遼說:“我會繼續人看住他。”
未的青檸酸得厲害, 項明章吃到一粒籽,皺起眉:“真難喝,給我換一杯。”
“換什麼,威士忌?”許遼意有所指,“聽說你之前帶了朋友來喝酒?”
項明章實際上是雲窖的出資人, 他和許遼的關系鮮為人知,因此這里就像一基地,他偶爾來放松一下, 從沒帶任何外人來過。
項明章瞥向卡座的位置, 回答:“算不上朋友。”
許遼挑眉:“那是什麼人?”
“好奇啊?”項明章是生意人, 絕不肯吃虧, “你盡快查出線索, 到時候我帶他來謝你。”
楚識琛不知道自己遭人議論, 他困倦至極,回房睡了一整天。
窗簾忘記拉,黃昏時分,余暉照耀著半張床。
楚識琛醒過來,出手機打開微信,最新一條朋友圈是錢樺發的餐廳廣告。
他點了個贊,爬起來整理那些資料。
錢樺給的件賬號有三十多個,涵蓋吃喝玩樂各方面,“楚識琛”曾經使用最多的社件有四個,除了微信,另外三個都是外國件。
Advertisement
舊手機號和微信號一起注銷了,就算找回來,上面的數據記錄也沒辦法再恢復。
楚識琛埋頭鼓搗了兩個鐘頭,功登錄了一個郵箱,再通過郵箱驗證,重新設置了件碼。
打開前,他在心里對真正的“楚識琛”說了句“見諒”。
這個件可以在全球范圍使用,主要用于分照片和視頻。
他瀏覽“楚識琛”發布過的容,每一張照片皆是與他酷似的面孔,展示著他永遠不會做的表——吐舌、皺鼻子、用力嘟著……他生出一難以言喻的覺,怪異又奇妙。
最新一張照片發布于出事前的一個月,燈昏暗,拍的是一支麥克風,配文關聯了一個“xx”的賬號。
楚識琛點進去,發現“xx”是搖滾樂隊的員之一,名字星宇。
星宇和“楚識琛”互相關注,發布的照片會互相評論、點贊,私信聊天的記錄里,“楚識琛”主問星宇要過聯系方式。
踏破鐵鞋無覓,楚識琛立刻保存號碼打過去,結果已空號。
他不死心,在私信給星宇發了一個“你好”。
苦等了一天,楚識琛不記得登錄過件幾百次,然而沒等到回復,星宇換掉了頭像、清空了照片,并且把他拉黑了。
楚識琛:“……”
周一上班,楚識琛暫時擱下私事,計劃書完,一早項明章通知他,讓他和項樾的總經理商討“退款”機制的推進。
總經理有協調各部門的權限,楚識琛負責主導的程序。
如他們所料,計劃書的條例給出來,業務部門的抵緒消退了大半。
項明章有應酬,一整天沒面,那天和段昊夫婦吃飯,談到文旅產業的政策向,楚識琛猜測項樾大概要有新項目了。
Advertisement
兩個人各忙各的,一個在公司里案牘勞形,一個在外面風雨奔波。
幾次通話都默契地只論公事,彼此放心。
眨眼到了周三,清潔大姐中午來打掃,抱怨總裁辦公室的桌上堆得太滿,不敢,桌子臟了都沒辦法干凈。
楚識琛把人打發了,獨自走進項明章的辦公室。
寬大的辦公桌上積攢了幾十本文件,楚識琛繞到桌后一一整理,騰出一塊寫字的地方。
那支新換的鋼筆估計不太合意,項明章上次用完隨手一丟,滾在鍵盤上,筆尖的墨水已經干涸。
楚識琛把鋼筆清洗干凈,拉開左手的第一只屜,里面用來放常備品,胃藥、車鑰匙、薄荷糖、備用手機,他把鋼筆放下,不可避免地看見屜里多了一顆紐扣。
是那一晚他拉扯表鏈,從項明章襯衫上崩掉的一顆。
楚識琛出食指點了點,估計襯衫都扔掉了,還留著這一顆扣子有什麼意義?
正忖著,手機振起來,楚識琛拿出一看來電顯示,心虛般將屜關上。
他按下接聽:“項先生?”
項明章問:“吃完午飯了麼?”
“還沒。”楚識琛下意識地向窗外,“你回公司了?”
項明章說:“我在圖書館,吃飽了來找我。”
午休時間圖書館人跡寥寥,楚識琛刷工作證進去,按圖索驥,直奔第三層文旅相關的書架。
項明章正在翻閱一本書,低著頭,腳步聲停在他后的書架前,楚識琛與他背對背,相距咫尺。
項明章低音量:“你怎麼知道我在這邊?”
楚識琛過一排書脊,說:“我查了監控。”
項明章道:“那你當初不應該選書,應該選門衛。”
楚識琛說:“門衛的制服我不喜歡。”
Advertisement
項明章借了兩本書,和楚識琛一起從圖書館的后門離開,那條梧桐小徑三天未掃,鋪滿了秋葉,一片金黃。
楚識琛不忍心踩踏,在臺階上立著,如果談公事不必來這里,他靜候著項明章開口。
項明章亦不喜歡拖泥帶水,直接問:“樂隊查得怎麼樣了?”
通過三四個件上的留痕跡,楚識琛說:“我好像認識樂隊主唱,星宇,以前跟他頻繁互過。”
“什麼程度?”項明章追問,“你們的聯系僅限于網絡?”
楚識琛這兩天查了曾經的銀行記錄,回答:“不止,還有資金往來,最后一筆應該是派對上的演出費,高達七位數。”
這種名不見經傳的地下樂隊,一場私人表演居然上百萬,項明章道:“你還真是喜歡這幫人。”
楚識琛雖然出富貴,但見夠疾苦,過去不曾在梨園豪擲千金捧花旦,現在也不贊同揮霍百萬請樂隊,他揶揄道:“可能我欣賞他們的音樂素養吧。”
項明章說:“一幫年輟學的混混,彈個吉他,唱點要死要活的空話,有什麼音樂素養?”
楚識琛哪知道,故作好奇:“你借了什麼書?”
“別轉移話題。”項明章不上當,“找到賬號聯系了沒有?遇上你這種傻大款,他們應該纏著不放才對。”
楚識琛有點尷尬:“他把我拉黑了。”
項明章幸災樂禍地笑了一聲,邁下一階,轉和楚識琛面對面,說:“我認識個朋友有點門路,能幫你找人。”
楚識琛揣“門路”二字,任何時代都不缺地頭蛇,背景復雜,招數厲害,舊時每個商幫都會結一二來保障生意。
可他告訴項明章是為了避免誤會,不是要讓對方牽扯進來,他說:“不用了,這件事與你無關,你不要手。”
Advertisement
項明章反問:“那跟錢樺有什麼關系,你怎麼麻煩他?”
楚識琛說:“他是游艇公司的投資人。”
“他是什麼不重要。”項明章不容反駁地說,“重要的是你該意識到,找我比找任何人都有用。”
楚識琛聽出十足的傲慢:“難道你——”
項明章終于暴來意:“我找到星宇了。”
無置樂隊解散后,五名員各奔東西,大多沒了音信,只有主唱星宇還算活躍。
不過本來就沒混出名堂,現在星宇單槍匹馬,換了個藝名在國四跑線下演出。
這周六市里舉辦音樂節,星宇會參加。
楚識琛問:“音樂節是唱歌的?”
一片落葉飄下,項明章接住:“廢話,我把舉辦的時間和地點發給你,星期六我和你一起去。”
這個世界太新鮮、太陌生,有人陪伴就多一分安定,可楚識琛認為不該承,他拒絕道:“謝謝你幫我調查,但這件事跟你沒關系,我怕你牽連進來會惹上麻煩。”
項明章拿落葉掃他的下:“擔心我?”
楚識琛嫌,奪下葉子:“沒有。”
“但我擔心你。”項明章說,“假如事故不是意外,是人為,你可能會有危險。”
楚識琛掐著葉,因為他是假的,所以不曾考慮過這個層面。
項明章明明白白地說:“我不想你再出事,楚識琛,這個理由夠不夠?”
干燥的葉很脆,輕易就斷了,梧桐葉從楚識琛的手中旋轉落下,被聒噪的秋蟬掩蓋了墜地的響聲。
午休時間結束了,項明章后退一階,轉踏過秋葉,過梧桐樹的隙灑下來,楚識琛落后一步踩著項明章的影子。
他的確出過事,卻非炸,而是四五年春夜里的一場海上風暴。
項明章有朝一日會知曉嗎?
到時回首今日的擔心,會不會覺得錯付和可笑?
忽然,項明章停下提醒:“對了,去音樂節不要穿正裝。”
楚識琛心不在焉地點點頭,又有樹葉不斷掉下來,這次他后知后覺地聽清了。原來葉落無聲,咚咚響的,是他的膛。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854 章
重生之軍長甜媳
重生前,她只顧著躲他,重生後,她步步爲營,將奪她人生的堂姐踩在泥濘裡。 再次重逢他,她只有一個想法:嫁給他、給他生猴子。 後來她才發現,她的想法變成葉爵攻略,每天折騰到腿軟。 葉爵:媳婦,通告下來我得去北邊半年。 宋嫣:你安心去吧,我會在家等你。 葉爵脫下衣物,一臉平靜的迴應:可以帶家屬一起過去。 宋嫣:… 在葉爵心裡,宋嫣比軍銜更閃耀。
88.4萬字8.17 268026 -
連載1508 章
媽咪爹地要抱抱
豪門陸家走失18年的女兒找回來了,眾人都以為流落在外的陸細辛會住在平民窟,冇有良好的教養,是一個土包子。結果驚呆眾人眼球,陸細辛不僅手握國際品牌妍媚大量股份,居然還是沈家那個千億萌寶的親生母親!
127.1萬字8 108022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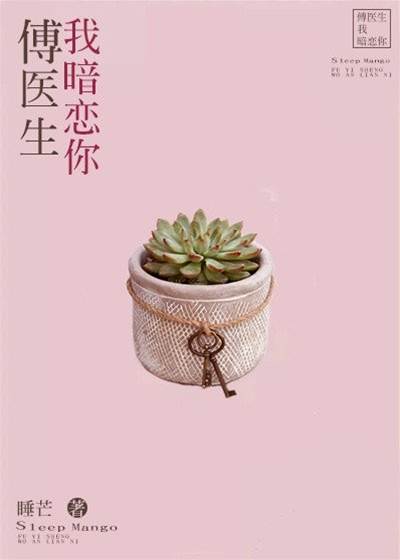
傅醫生我暗戀你
暗戀傅醫生的第十年,林天得知男神是彎的! 彎的!!!! 暗戀成真小甜餅,攻受都是男神,甜度max!!!! 高冷會撩醫生攻x軟萌富三代受 總結來說就是暗戀被發現後攻瘋狂撩受,而受很挫地撩攻還自以為很成功的故事……
44.4萬字8 7391 -
完結319 章

婚後重生,賀少寵妻成癮
賀家賀大少以強勢狠厲著稱。 賀翊川為人霸道冷情,似乎任何人都激不起他的興趣,如同佛子一般,婚後禁慾半年之久。 娶她不過是受長輩之命。 遲早要以離婚收場,蘇溪也這麼認為。 哪知一次意外,兩人一夜纏綿,賀翊川開始轉變態度,對她耐心溫柔,從清心寡欲到溝壑難填,逐步開始走上寵妻愛妻道路! 兩個結婚已久的男女開始經營婚姻的暖寵文! 劇情小片段: 「賀翊川,你今晚怎麼了?你醉酒後可太能折騰人了。」 聽到她耐不住的抱怨聲,賀翊川拾起掛在他脖頸上的小手,輕輕地揉了揉,聲音低啞富有磁性:「今晚高興。」 「為什麼?」 「因為方俊傑他們祝我們新婚快樂,生活幸福。」他一字一句的啟唇,低沉清朗的聲線,清晰分明的灌入她耳中。 聽到後,蘇溪扶住他的手臂,將上半身和他的結實的胸膛拉開一些距離,昏黃的燈光斜照在她明亮的瞳孔里,清澈見底。 「你說該不該高興?」 男人清墨般的眼眸與她四目相對,薄直的唇角邊含著似有若無的笑意,眼神直勾勾地凝視著她。 蘇溪指尖在他手心中微微蜷縮,心跳也不由加速,語調輕緩柔和:「高興。」
52萬字8 11402 -
完結207 章

強撩!小可憐成了傅總的小祖宗
【甜寵+小可憐+日久生情+男主bking+雙結+治癒】傳聞,出櫃多年的傅先生被一個小女孩給強撩了。衆人紛紛爲女孩惋惜默哀,結果女孩第二天還在活蹦亂跳。甚至,堂而皇之地住進傅先生的家,睡他的牀、佔他的人…當傅先生扶着懷孕的鬱暖暖出現時,一個火爆的消息迅速傳遍全球傅先生被掰直了!傅景琛一直以爲自己養了個好欺負的小可憐。直到某天親眼看到她和人打架的狠樣,他瞬間醍醐灌頂,這哪是什麼小可憐,分明就是個張牙舞爪的小霸王!
35萬字8 156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