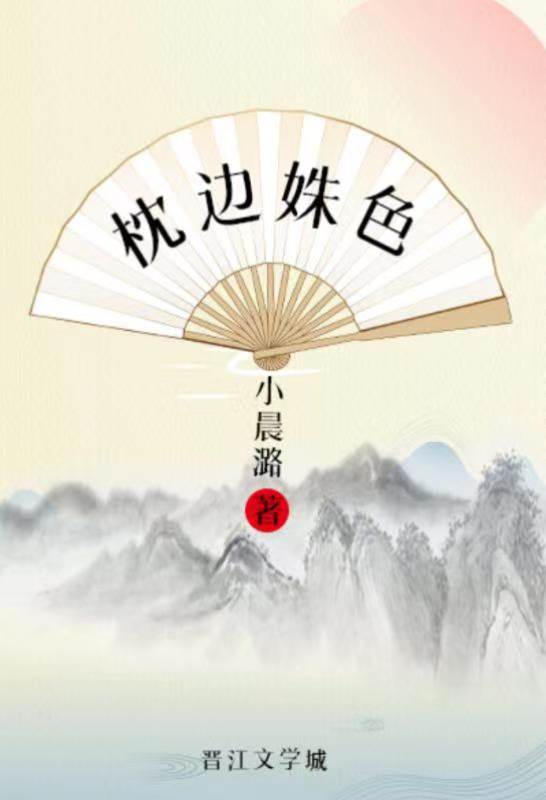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樊籠》 第96章 設私刑
黑暗中,蘇傾的更加敏。
隨著對方沉冷的話音落下,耳邊炭火燃燒的噼啪聲愈發清晰,伴隨的仿佛還有附著在皮上的熱度。
蘇傾的腦中開始不可控制的勾勒各種慘無人道的酷刑。
仿佛是為了讓的想象更形象,沒等無聲的寂靜在昏暗的空間中蔓延過久,宋毅沉緩的聲音便再次響起。
“我且給你介紹幾種。”他抬手翻著火鉗,深不見底的眸卻越過熱烈跳的火,目不斜視的定在前方那人的蒼白的臉上:“譬如那夾,烙片,刑鞭,尖凳,釘椅……還有那鐵蓮花。”
炭火燃燒的噼啪聲中,多了些清淺卻急促的呼吸聲。
宋毅盯著:“對于肯乖乖配合的囚犯,上述刑便足矣。可總有些到底的茬子……那便不得用上些別的手段。比如湯鑊、刖刑、梳洗、剝皮、凌遲、車裂。”
仿佛未見前方人那瞬息失煞白的面,宋毅繼續道:“刑室的大門只給活人進出。如果犯人瘐斃,則從獄墻西側的拖尸拉出去。你且告訴本,你是要從大門走出去,還是想從里被拉出去。”
蘇傾蜷手指,住掌心,迫自己開口道:“不知宋大人……想要我如何配合你?”
火鉗翻炭火的聲音停了下。
宋毅冷笑的看向道:“本還當你會死到底。”
蘇傾蒼白的面掩映在室昏暗的線中。
“宋大人抬舉了。我亦不過世俗的凡人,并非悍不懼死的義士,若能求生,何必奔死。”
“如此,甚好。”宋毅鋒利的眸在面上流連。下一刻,聲音陡然寒厲:“接下來本問你一句,你便如實答一句,若敢有半句瞞……那今日你就從里出此地罷。”
Advertisement
蘇傾抿了抿,點點頭算是默認。
宋毅便扔了手里火鉗。
起,緩步踱至蘇傾面前幾步遠停住,牢牢擋住了后的炭火朦朧的暈。
蘇傾的眼前遂變了一片黑暗。
宋毅微闔了眼瞼,居高臨下的睨著。
“你是不是要首先坦白自己的真實份?告訴本,你究竟是誰?”
蘇傾聽著他微沉的問聲,有瞬間的茫然。
隨即又想到此次被卷的烏龍事件,不免有些恍然,便開口解釋道:“此次涼州舊部叛當真與我無干。大概是因為我與他們口中的福王世子有幾分相似……”
“誰問你這個。”宋毅冷聲:“你姓誰名誰,家住何,家中又有何人?”
話音一落,蘇傾便窒住。
宋毅敏銳的目沒有錯過面上一閃即逝的愕然,以及遲疑。
“蘇傾。”瓣輕微蠕:“只記得個名字,其他的……都不記得了。”
宋毅的目從臉上劃向一旁的刑,出口的聲音不帶起伏:“真的?”
“真的。”
宋毅脖上的青筋跳了跳。
忍了忍,他方勉強住心底兇意,令自己出口的聲音盡量平靜:“你與巫相又是何種關系?”
蘇傾當真詫異:“巫相?是誰?”
黑暗中,宋毅勾了角,無聲冷笑。
若他們之間沒有任何關系,那巫相又何必自斷一臂來也要搭救于?當那巫相是個悲天憫人的菩薩不?
這種鬼話,也就適合說給鬼聽罷。
偏的如此茫然無知的模樣,裝的甚是地道。
亦如當初順攀在他脖頸時,答應他會等他回來時候的乖巧模樣。
若不是吃過的虧,上過的當,他會當真以為懵懵懂懂一概不知。
想起從前,宋毅臆間就騰起了些戾氣,便有幾分沖,恨不得將他之前吐口的威脅之語付諸實現。
Advertisement
他真恨不得能施用手段吐出實話。
宋毅的目死死釘在不遠的刑鞭上,夾上。
可好半會,他的雙腳卻猶如被釘住,依舊杵在原地。
意識到這一點,他的臉當即變得十分難看。
蘇傾也不知自己有沒有說錯什麼,只約到自己這話出口之后,氣氛陡然變得怪異起來。
“宋大人所提到巫相,我是真的不認識。”
蘇傾坦誠的重復道。
宋毅陡然將目轉向。又兇又厲。
不說是嗎?他會有法子弄清楚的。
“下一個問題。”宋毅緩緩問:“你跟魏期是什麼關系?”
眼見面上浮現茫然之,宋毅聲音陡然嚴厲:“別告訴我魏期你也不認識。就是那沈子期!”
蘇傾似被此問鎮住,不知覺的張了張口。
不可否認,他這猝不及防的一問,是蘇傾始料未及的,著實令驚訝了下。
“他……不過是一書生。”回過神,蘇傾迅速回道。雖不知他如何得知沈子期此人,又為何發此一問,可直覺他語氣不善,唯恐連累無辜,便謹慎斟酌著字句:“素日里我與南麓書院的學子打道的次數頻繁,久而久之,與那些學子就有幾分稔。”
宋毅笑了:“是嗎?稔到給你放牛,割草,劈柴,承包了你家中多半活計,甚至還稔到……登堂室?”
蘇傾呆住。
宋毅只覺得一邪火從心底騰起,焚的他理智寸寸崩塌,忍不住抬向前近一步。
“你可有……將子給了他?說實話!”
重的息盡數灑蘇傾的面上。宋毅咬牙切齒的說著,待說到那個‘他’字,語氣又狠又戾卻又帶著幾分不易察覺的嫉,當真是恨不得能發狠的嚼碎了嚼爛了,末了再活了漱口涼茶吐出來,方能稍解心中之郁怒。
Advertisement
蘇傾當即寒了臉。不由暗怒。
他這話,當真是下流無恥至極。
“宋大人,請自重。”
自重。宋毅齒間含著這兩字,慢慢咀嚼。
然后他就琢磨了,這是要與他徹底劃清界限啊。
蘇傾覺手腕一寬時,還暗松口氣,以為宋毅終于審完了,肯給松綁放回去。
抬手便要去解眼前的黑布,可沒想到剛一作,手腕卻驟然一。尚沒等回過神來,雙手已被反剪于后,再次被繩子牢牢綁了住。
蘇傾怒目圓睜,繼而掙扎怒問:“大人要作何?”
宋毅手強摟過掙扎不休的子,而后猛一俯,抄過彎將人打橫抱起。
“既然你不肯說,那本便親自檢驗。”沉聲說完,宋毅便抱著人三步并作兩步至炭火上方置的鼎中,不由分說的將給拋了進去。
蘇傾冷不防被拋其中,連嗆了幾口溫水。
卻原來鼎中盡數是水,此刻已被下方炭火燒的溫熱。
反應過來在何的蘇傾猛地按住鼎壁起,邊疾咳邊急聲解釋:“沒有!我與他什麼都沒有!”
蘇傾大悔!宋毅他從來鮮廉寡恥,悔不該按捺不住出口駁斥,從而給了他作惡的借口。
耳畔聽見嘩啦的踏水聲,蘇傾下意識的便向后了子躲避,直待后背猛地撞到堅的鼎壁,方知已然退無可退。
“我說!我說!沈子期與我從來是君子之,我們二人謹守君子之禮,從來清清白白,未曾有半分越矩!”
我們。二人。
獄墻上跳的火打在宋毅的臉上,落下晦暗不明的。這一刻,他眸里平添了幾分獰,升起種想要將那沈子期剁醬的念頭。
大概不知,沈子期三字從口中吐出,是那般語還休。
Advertisement
“晚了。”宋毅邊沉聲說著,邊手解著朝服朝步步欺近,直至將到退無可退的仄鼎壁邊角。
牢牢堵在前的那灼燙人的溫,蘇傾的子反的微,強自鎮定的試圖勸說:“我與那沈子期真的是……”
宋毅再也聽不得那三字。朝鼎外擲了朝服后,便抬手一把撕裂了那濡的囚。
蘇傾駭然吸氣,黑布下的雙眸頓時睜大。
“宋毅你作什麼!”
到他灼燙的掌心開始向下游移,蘇傾的子猛一個栗,而后水下的雙胡的踢向他,同時驚怒道:“為朝中一品重臣,宋大人,你的德行與守何在!縱使我為囚徒,也自會有國家律法判我罪行,你又有何權利在此私設刑堂,對我肆意妄為!你……你走開!”
指責的話語未盡,出口的話已是驚。
宋毅抓住水下那蹬的細弱雙纏在他腰腹間,充耳不聞的怒叱聲,到底按照自己的心意下沉子將用力抵在了鼎壁上。
黑暗的刑室里,激的水聲,/息聲,拍打聲,哭罵聲夾雜一片,許久未歇。
“宋毅……你就是冠楚楚的……狗!”
出口的怒叱換來一記重抵,蘇傾當即被激的子后仰,急促息。
宋毅半瞇著眸盯著前的這纖弱的子,作間,目始終纏著不肯移開半寸,約帶著幾分迷離之態。
而后他猛地驚覺,貌似他竟如此放不開眼前的。
大概……他宋毅真的是個狗罷。
暫停了作,他了眉心深口氣,而后伏在耳畔抑的問道:“最后一問題,三年前你為何要從府上逃離?”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74 章
錯嫁皇妃帝宮沉浮:妃
一夜承歡,失去清白,她卻成了他代孕的皇妃。紅綃帳內,他不知是她,她不知是他。紅綃帳外,一碗鳩藥,墮去她腹中胎兒,她亦含笑飲下。惑君心,媚帝側,一切本非她意,一切終隨他心。
64.9萬字8 15557 -
完結568 章

爽翻天!穿到古代搬空國庫去流放
【空間 女主神醫 女強 爽文 虐渣 發家致富 全家流放逃荒,女主能力強,空間輔助】特種軍醫穿越古代,剛穿越就與曆史上的大英雄墨玖曄拜堂成親。據曆史記載,墨家滿門忠烈,然而卻因功高蓋主遭到了皇上的忌憚,新婚第二日,便是墨家滿門被抄家流放之時。了解這一段曆史的赫知冉,果斷使用空間搬空墨家財物,讓抄家的皇帝抄了個寂寞。流放前,又救了墨家滿門的性命。擔心流放路上會被餓死?這不可能,赫知冉不但空間財物足夠,她還掌握了無數賺錢的本事。一路上,八個嫂嫂視她為偶像,言聽計從。婆婆小姑默默支持,但凡有人敢說赫知冉不好,老娘撕爛你們的嘴。終於安頓下來,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紅火。墨玖曄:“媳婦兒,我們成親這麼久,還沒有洞房呢!”赫知冉:“想洞房,得看你表現。”墨玖曄:“我對天發誓,一輩子心裏隻有你一個女人,不,下輩子、下下輩子也是。”赫知冉:“你說話要算數……”
104.2萬字8.43 421630 -
完結347 章

娘娘總是體弱多病
邰家有二女,長女明豔無雙,及笄時便進宮做了娘娘 二女卻一直不曾露面 邰諳窈年少時一場大病,被父母送到外祖家休養,久居衢州 直到十八這一年,京城傳來消息,姐姐被人所害,日後於子嗣艱難 邰諳窈很快被接回京城 被遺忘十年後,她被接回京城的唯一意義,就是進宮替姐姐爭寵 人人都說邰諳窈是個傻子 笑她不過是邰家替姐姐爭寵的棋子 但無人知曉 她所做的一切,從來不是爲了姐姐 所謂替人爭寵從來都是隻是遮掩野心的擋箭牌 有人享受了前半生的家人寵愛,也該輪到其他人享受後半生的榮華富貴
52.3萬字8 52 -
完結3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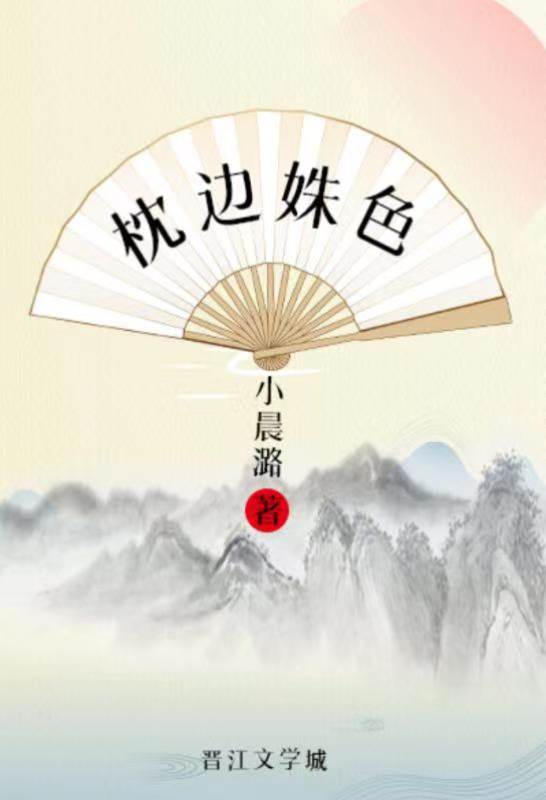
枕邊姝色(重生)
阮清川是蘇姝前世的夫君,疼她寵她,彌留之際還在爲她以後的生活做打算。 而蘇姝在他死後,終於明白這世間的艱辛困苦,體會到了他的真心。 得機遇重生歸來,卻正是她和阮清川相看的一年。她那時還看不上阮清川,嫌棄他悶,嫌棄他體弱多病……曾多次拒絕嫁給他。 再次相見。蘇姝看一眼阮清川,眼圈便紅了。 阮清川不動聲色地握緊垂在身側的右手,“我知你看不上我,亦不會強求……”一早就明白的事實,卻不死心。 蘇姝卻淚盈於睫:“是我要強求你。” 她只要一想到這一世會與阮清川擦肩而過,便什麼都顧不得了,伸手去拉他的衣袖,慌不擇言:“你願意娶我嗎?”又哽咽着保證:“我會學着乖巧懂事,不給你添麻煩……我新學了沏茶,新學了做糕點,以後會每日給你沏茶喝、給你做糕點吃。” 她急切的很,眸子澄澈又真誠。 阮清川的心突然就軟成一團,嗓音有些啞:“願意娶你的。” 娶你回來就是要捧在手心的,乖巧懂事不必,沏茶做糕點更是不必。
58.5萬字8 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