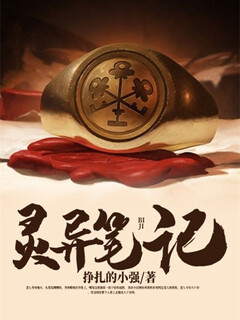《鬼吹燈》 龍嶺迷窟 第二十章 追憶
這幾天連續悶熱,坐著不都一地出汗,最後老天爺終於憋出了一場大雨,雨下得都冒了煙,終於給燥熱的城市降了降溫。(爪譏書屋 wWw.zhuaJi.org
雨後的潘家園古玩市場熱鬧非凡,在家忍了好幾天的業餘收藏家和古玩好者們,紛紛趕來淘換玩意兒。
大金牙忙著跟一個老主顧談事,胖子正在跟一對藍眼睛大鼻子的外國夫妻推銷我們的那只繡鞋,胖子對那倆老外說道:“怎麼樣?您拿鼻子聞聞這鞋裡邊,跟你們國的夢一個味兒,這就是我們中國明朝夢穿的香鞋,名……名你們懂不懂?”
這對會一點中文的外國夫妻,顯然對這只造型致的東方繡鞋很興趣,胖子借機獅子大開口,張就要兩萬,這價錢把倆老外嚇得扭頭便走。經常來中國的外國人,都懂得討價還價,胖子見這對外國夫妻也不懂侃價,就知道他們是頭一回來中國,於是趕把他們攔回來,聲稱為了促進中外流,在堅持和平共五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給他們打個折。
我坐在一旁著煙,對古玩市場中這些熱鬧的場面毫無興趣,從陝西回來之後我到醫院去檢查過,我和胖子背上的痕跡並沒有發現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什麼病也沒有檢查出來。
而且我也沒什麼特別的覺。最近財源滾滾,生意做得很紅火,我們從陝西抱回來的聞香玉原石,賣了個做夢都要笑醒的好價錢,又收了幾件貨真價實的明,幾乎每一筆,利潤都是翻數倍的。然而一想到孫教授的話,就覺得背後了一座大山,不過氣,每每想到這些就憂心忡忡,對任何事都提不起興致來。
Advertisement
那個可惡的、偽善的孫教授,死活不肯告訴我這個符號是什麼含意,而且解讀古代加文字的技,只有他一個人掌握,但是我又不能用強,著他說出來。
古藍出土的那批龍骨雖然毀壞了,但是孫教授肯定事先留了底。怎麼才能想個法子,再去趟陝西找他要過來看看,只要我能確定背上的印記與絕國鬼的眼球無關,我才能放心。可是那次談話的過程中,我一提到鬼這兩個字,孫教授就像發了瘋一樣,以至於我後來再也不敢對他說鬼那個地方了。
孫教授越是瞞推搪,我覺得越是與絕的鬼有關系。既然明著要孫教授不肯給我,那我就得上點手段了,總不能這麼背著個眼球一樣的紅斑過一輩子。
夏天是個容易打瞌睡的季節,我本來坐在涼椅上看著東西,以防被佛爺(小)順走幾樣,但是腦中胡思想,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做了一連串奇怪的夢,剛開始,我夢見娶了個啞姑娘做老婆,比比畫畫地告訴我,要我帶去看電影。我們也不知怎麼,就到了電影院,沒買票就進去了,那場電影演得沒頭沒尾,也看不出哪跟哪,除了炸就是山塌方。演著演著,我和我的啞老婆發現電影院變了一個山,山中朦朦朧朧,好像有個深不見底的深淵,我大驚失,忙告訴我那啞老婆,不好,這地方是沙漠深的無底鬼,咱們快跑。我的啞老婆卻無於衷,猛然把我推進了鬼,我掉進了鬼深,那底有只巨大的眼睛在凝視著我……
忽然鼻子一涼,像是被人住了,我從夢中醒了過來,見一個似乎是很悉的影站在我面前。那人正用手指著我的鼻子,我一睜眼剛好和的目對上,我本來夢見一只可怕的巨大眼睛,還沒完全清醒過來,突然見到一個人在看自己,嚇了一跳,差點從涼椅上翻下來。
Advertisement
定睛一看,shirley 楊正站在面前,胖子和大金牙兩人在旁邊笑得都快直不起腰了,胖子大笑道:“老胡,做白日夢呢吧?口水都他媽流下來了,一準是做夢娶媳婦呢。”
大金牙對我說道:“胡爺醒了?這不楊小姐從國剛趕過來嗎?說是找你有急事。”
shirley 楊遞給我一條手帕:“這麼才幾天不見,又添病了?口水都流河了,快。”
我沒接的手帕,用袖子在邊一抹,然後用力了個懶腰,了眼睛,這才迷迷怔怔地對shirley 楊說:“你的眼睛……哎,對了!”我這時候睡意已經完全消失,突然想到背後眼球形狀的紅斑,連忙對shirley 楊說道:“對了,我這幾天正想著怎麼找你,有些要的事要和你講。”
shirley 楊對我說道:“我也是有些重要的事。這裡太吵鬧了,咱們找個清靜的地方談吧。”
我趕從涼椅上站起來,讓胖子和大金牙繼續照顧生意,同shirley 楊來到了古玩市場附近的一龍潭公園。
龍潭公園當時還沒改建,規模不大,即便是節假日,遊人也並不多,shirley 楊指著湖邊清靜的一條石凳說:“這裡很好,咱們在這坐下說話。”
我對shirley 楊說:“一般搞對象馬路的才坐這裡,你要是不避嫌,我倒是也沒什麼。這小地方真不錯,約約會正合適。”
shirley 楊是國生國長,雖然長期生活在華人社區,卻不太理解我的話是什麼意思,問道:“什麼?你是說中的才被允許坐在湖邊?”
我心想兩國文化背景差別太大,這要解釋起來可就複雜了,便說道:“人民的江山人民坐,這公園裡的長凳誰坐不是坐,咱倆就甭管那套了。”說著就坐了下去。
Advertisement
我問shirley 楊:“陳教授的病好了嗎?”
shirley 楊在我邊坐下,歎了口氣說:“教授還在國進行治療,他的刺激太大,治療狀況目前還沒有什麼太大的進展。”
我聽陳教授的病仍未好轉,心中也是難過,又同shirley 楊閑聊了幾句,就說到了正事上,當然不是讓我還錢的事,和我所料一樣,是為了背上突然出現的眼球狀紅斑。
不僅是我和胖子,shirley 楊和陳教授的上也出現了這種古怪的東西。那趟新疆之行,總共活下來五個人,除了我們四個人之外,還有個向導,沙漠中的老狐貍安力滿,他上是否也出現了這種紅斑?
shirley 楊說:“安力滿老爺爺的上應該不會出現,因為他沒見過鬼。我想這種印記一定是和鬼族的眼球有著某種聯系。”
關於那個神的種族,有太多的沒有揭曉,但是這些不為人知的,包括那個不知通向哪裡的鬼,都已經被永遠地埋在黃沙之下,再也不會重見天日。
我把在陝西古藍從孫教授那裡了解到的一些事,都對shirley 楊講了,也許可以從中做出某種判斷,這個符號究竟是不是鬼帶給我們的詛咒。
shirley 楊聽了之後說道:“孫教授……他的名字是不是作孫耀祖?他的名字在西方考古界都很有威,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幾個古文字破解專家,擅長解讀古代符號、古代暗號以及古代加圖形信息。我讀過他的書,知道他和陳教授是朋友,但是沒機會接過他本人。1981年,埃及加羅泰普法老王的墓中,曾經出土過一批文,其中有一支雕刻了很多象形符號的權杖,很多專家都無法判斷符號的含義。有一位認識孫耀祖的法國專家寫信給他求助,得到了孫教授的寶貴建議,最後判斷出這支權杖,就是古埃及傳說中刻滿間文字的黃泉之杖。這一發現當時震驚了整個世界,從此孫教授便四海聞名。如果他說這種符號不是眼睛,而是某種象征的圖言,我想那一定是極有道理的。”
Advertisement
我暗暗咋舌,想不到孫教授那古怪的脾氣,農民一樣的打扮,卻是這麼有份的人,海水果然不可鬥量啊。我問shirley 楊:“我覺得這個是符號也好,是文字也罷,最重要的是它是吉是兇?與絕國那個該死的跡有沒有什麼關系?”
shirley 楊說:“這件事我在國已經找到一些眉目了,你還記得在紮格拉瑪山中的先知默示錄嗎?上面提到咱們四個幸存者中,有一個是先知族人的後裔,那個人確實是我。我外公在我十七歲的時候便去世了,他走得很突然,什麼話都沒有留下。我這趟回國,翻閱了他留下來的一些,其中有本筆記,找到了很多驚人的線索,完全證明了先知啟示錄的真實。”
看來事向著我最擔心的方向發展了,真是怕什麼來什麼,那個像噩夢一樣的鬼,避之唯恐不及,它卻偏偏像狗皮膏藥一樣黏在了上。我們是否被絕古國詛咒了?那座古城連同整個紮格拉瑪,不是都已經被黃沙永久地掩埋了嗎?
shirley 楊說道:“不是詛咒,但比詛咒還要麻煩,紮格拉瑪……我把我所知道的事從頭講給你聽。”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98 章
美女律師撞鬼
女律師夜遇女鬼,從此卷入一起性虐殺案,這和當年自己親眼目睹的被鬼扼喉自殺案有沒有必然的聯系?是人為還是受鬼控制?此鬼是不是彼鬼?冷情淡漠的法醫,是不是自己當年的豪門小老公?……她能否撥開眼前的迷霧,尋找出真相?……陰謀,一個個陰謀……難道僅僅是一個個陰謀麼?且看女律師穿梭豪門,在陰陽鬼道中痛並快樂著!
106.1萬字8 29505 -
完結1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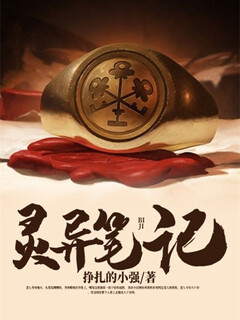
靈異筆記
為什麼自從做了眼角膜移植手術後的眼睛時常會變白?是患上了白內障還是看到了不幹淨的東西?心理諮詢中的離奇故事,多個恐怖詭異的夢,離奇古怪的日常瑣事…… 喂!你認為你現在所看到的、聽到的就是真的嗎?你發現沒有,你身後正有雙眼睛在看著你!
29.6萬字8 7634 -
完結5125 章

九零後天師
世人只知《魯班書》,卻不知《公輸冊》造化之術,一脈相傳。一代天師踏入凡塵,攪動萬里風雲!
916.1萬字8.33 782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