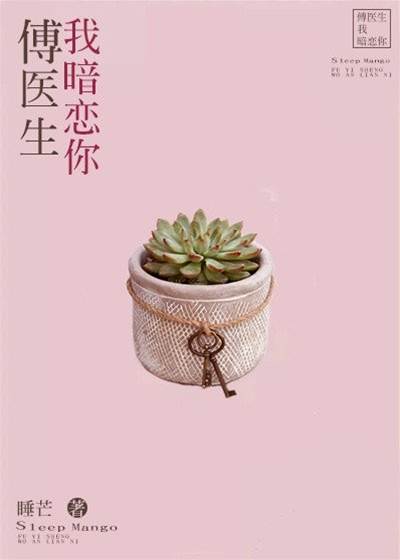《簪纓問鼎》 第339章
第339章
又下雨了。陳悅看著窗外連綿細雨, 心頭滋味百般。幾個月前, 他還日思夜想, 盼著有一天能夠天降甘,消弭旱。可是如今真下起雨來, 卻又讓人心焦的厲害。
冬日天寒,又逢連雨, 外面修路的役夫能吃得消嗎?萬一生起病來, 要如何是好?雨天路, 工地上定然四泥濘, 會影響鋪路的進度嗎?
百般思緒在中盤旋, 最終陳悅還是披上了蓑, 領著僕役向著工地走去。
去歲, 陳悅得知了冀州募糧修路的消息。苦思許久後,終於下了決心,包下了一段十裡左右的道。因為工程不大,需要的糧草也比想像的, 陳悅還以為做了一筆劃算買賣。誰料真正運來了糧, 開始工時, 旱災也初現端倪。
這可是大旱時的一船糧食啊!哪怕是在老家販售,也是一大筆錢, 何況千里迢迢運到冀州?
更重要的是, 一旦發生旱災,各地工程都要停擺。若是匪禍四起,還會引得流民境。冀州平定才多長時間?能在這樣的況下熬過大旱嗎?
雖說當地府一直說路還要修, 不會半途而廢,但是跟他一起包下路段的客商,有大半都反悔離開。雖然損了人力力,但是終歸沒有虧本。是趁早離開,保住本錢。還是咬牙舍本,搏上一把?不知怎地,陳悅想起了自己初到晉時見到的盛景,竟然頭腦一熱,留了下來。這下,可把他徹底拴在了冀州。
每日都要前往工地,監察役夫勞作,推算糧食損耗。他出小族,又沒有那麼大的財力,真是恨不得把一文錢掰八瓣。虧得修路的吏未曾使出什麼壞招,也遵守了當初的承諾,沒在他的工地上再添人手。就這麼一點點,撐著修了起來。
Advertisement
旱一日重過一日,每天都能聽到又有多流民境,又有多兵匪出沒。陳悅只覺自己踏在一條懸上,隨時都可能墜深淵。然而這搖搖墜的平衡,卻始終未曾被打破。來自幽州、青州、兗州的流寇,總是剛剛境,就被剿滅。那蜂擁不止的流民,也在被更加複雜的工程吞納。
只是區區冀州,就有如此能耐嗎?
焦慮從未退去,但是信心,卻也悄然生出。陳悅發現自己對這片土地,越來越好奇。若真的能修路,熬過了這個災年,冀州又會變何等模樣?
不知何時,陳悅忘掉了自己最初的打算。似乎這段路,了他的基命脈。大半年的時間,日日如此,直到這場冬雨來臨。
下雨是好,但是正在修的路,可比來年春耕重要多了。眼看竣工在即,可別橫生枝節。
匆匆趕到了工地,和預想有所不同,雖然寒雨綿綿,但是路上役夫依舊不。大部分都披著蓑,推車搬沙,忙的不亦樂乎。還有些圍在棚屋外,人人手裡端著木碗,繞著那口飄著香味的大鍋排隊。
這是縣裡送來了?每過一旬,本縣的孫縣令就會前來工地察看,同時帶來些野,給修路的役夫打打牙祭。這是小恩小惠不錯,但是效果驚人。這麼多流民,就沒一個不恩戴德的。有這樣民的縣,此縣的縣治也極為安穩。大旱之中,連一起民變也未發生。
作為縣外道的承辦人,陳悅跟孫縣令也極為稔。只是現在明明還不到一旬,怎麼縣令就來了工地?也是害怕雨天生變嗎?
心裡暗自揣測,陳悅並未停下腳步,很快就找到了被一堆吏員簇擁著的縣令。見到陳悅,孫縣令笑道:“陳郎來的正好,我正想延人去請呢。”
Advertisement
陳悅有些吃驚:“可是出了什麼事?錢糧不足嗎?”
孫縣令擺了擺手:“陳郎勿憂,路修得極好,再過三日便能完工。若是沒有陳郎相助,這路怎能修得如此順暢?前幾日刺史府剛剛頒下命令,要嘉許捐助的諸位賢良。本亦不敢怠慢,命人刻石立志。今日前來,正是為了豎碑。”
豎碑?什麼碑?陳悅半是忐忑,半是茫然,跟隨孫縣令前行幾步,來到了路邊。只見一座三尺高的短碑,立在道旁。
此去十裡,海陵陳悅捐修。元啟二年,久旱傷民,此路活人一千二百餘。
短短兩句,平實無華,然而陳悅已經看不清其後的文字了。他只覺中哽咽,兩眼酸,險險都要落下淚來。接下這段路,為的是什麼?不過是賺取錢糧而已。雖然大半年練,日日擔驚怕,這條路在他心中的意義早已不同。但是路終歸是路,他從未想過,用來修路的糧食,其實是救了那些衫襤褸,起早貪黑的役夫。
這些人來自哪裡?不是徭役,亦非徵召,只是流民。是失去家園,無田可種,顛沛流離的百姓。而他,給了這些流民工作的機會,讓他們有一屋存,一飯果脯。這,便是活人命了。
他救了一千多人,只憑這條路!
大半年的辛勤,大半年的憂煩,在這一刻,統統化作烏有。陳悅甚至覺得,自己已經拿到了最好的報酬。這碑會隨著道路的暢通,永永遠遠留在此地,每一個經過的路人,都能看到他的功績。而他的名姓,也會落在這小縣的縣誌之中,說不定千載之後,亦有人能夠尋到蹤影。他只是個商賈,出小姓,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可貴?
見陳悅激的難以自己,一旁孫縣令又道:“等到此路修,十年之,除了驛站,只有陳郎能在此設店。刺史府也配了幾樣貨品,陳郎可以擇一選購,據說有三年專賣呢。”
Advertisement
什麼?!陳悅也不顧失態,淚都未,猛地抬頭來。且不說開設邸店的權利,只是三年專賣,就是一筆讓人垂涎的厚利。這可比之前所說的,要厚太多了!
孫縣令已經斂起了面上笑容,長袖一斂,恭恭敬敬向陳悅施了一禮:“幸虧有陳郎,大災年間,此縣才能安然無恙。本也要多謝陳郎。”
這是他的肺腑之言。修路救得只是流民嗎?其實不然。役夫上穿的,手上拿的,屋裡用的,不都是從鄉人手裡收購所得。這些品的流通,也為鄉人們提供了多餘的錢糧,讓他們能在災年安然度日。大災之年,無一民,這樣的記錄放在履歷上,何等耀目!而這,都是由陳悅承接了道路而來。若是他半路走了,自己能撐得下來嗎?恐怕未必。
因此這一拜,真心誠意。
陳悅是個白,哪見過一縣之長向他行禮?連忙納頭對拜。然而這一拜間,他突然想起了早年在書中學過的一句。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如何?可謂仁乎?”“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當年子貢與仲尼的對答,他並不能明白。然而今日,只一條路,就救活了千人。冀州上百條路,幾萬夫役的勞作,又是怎樣的壯舉?能在大災之年,救濟萬民,是否才是真正的聖人之為?!
也許自己能來到冀州,才是此生最正確的選擇。他的家人,他的族親,也該搬來此地。若是能落戶在這自家修的道旁,才最好不過!
※
當日驚雷之後,晉就接連下了三日的大雨。乾涸已久的土地,徹底得到了滋潤,也讓懷恩寺的香火,旺盛了十分。
然而有人依舊沒有選擇寺拜佛。坐在窄小的邸中,謝鯤斜倚榻上,悠閒的逗弄著繈褓中的稚子。
Advertisement
“阿兄,你又來把尚兒抱出來了。不怕阿嫂怪罪嗎?”走進屋中,就看到這副景,謝裒笑著調侃道。
“我剛剛吹奏一曲,尚兒還蹈舞相迎呢!”謝鯤笑的得意。這是他去歲才添的子,取名謝尚。此子機敏可人,才一歲就顯出靈秀,深得謝鯤喜。
謝裒不由失笑:“晉喜降甘霖,旁人都急忙去寺裡叩拜,也只有你會閒躲在家中。”
“這可不是閒。”謝鯤又掐了掐兒子的臉蛋,“若是人人都去懷恩寺,梁公怕是還要不喜呢。”
只是一句,謝裒就聽出了弦外之音。梁公信佛,人人皆知,但是晉場中人,也有不人心裡清楚,梁公其實更重儒。可以信佛,可以修道,但是為,必須有政績。而只要能夠勝任自己的職務,究竟信的是什麼,他從不在乎。
也正因此,謝鯤遵從了以往的好,繼續研習黃老道學,也會在閒暇時邀人清談。分毫沒有湊上去改信佛釋的意思。但是不論是學道還是清談,都跟之前在王衍手下時截然不同。好歸好,理政任事,才是本職。
在樂平國磨勘了兩載,又經歷了一場大旱,他終於被提拔為晉令,等到明年開春,就能走馬上任。這可不是樂平史能夠比擬的。當年任晉令的葛洪,如今已經是魏郡太守。等到梁公手下的地盤更大,說不好還要升任。
這個晉令,實在是求之不得的差遣!
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出人意料的擢遷,謝鯤的行事,才越發謹慎。
深知兄長,謝裒歎道:“可惜豫州、兗州新換了刺史。原本還有人說,郗治中、葛太守能升任刺史呢。”
當初的別駕孫禮,已經了冀州太守,郗鑒和葛洪這樣的心腹,挑撥也是早晚的事。誰料朝廷作迅速,飛快更換了刺史。使得剿滅石勒的莫大功勞,了為人作嫁。如此行徑,自然有人會抱不平。
謝鯤倒是全然不在乎:“梁公不爭,自有他的道理。只要甘霖一降,誰還在乎區區刺史?”
這話說的有些輕狂,但是一語中的。懷恩寺開殿求雨,便得大雨傾盆,就算是揚州的天子,能夠做到嗎?只這一場雨,就變了人心。
刺史,早已不再重要。
“阿兄……”聽兄長這麼口無遮攔,謝裒有些無語。
“你到該想想自己,求賢院並非久留之。”謝鯤話鋒突然一轉,“或是學溫太真,或是學祖符辰。唯有任,才是本。”
溫嶠如今已經了刺史府,為郗鑒副手,祖臺之更是出任司工參軍,仗六司要職。兩人的年紀,跟謝裒仿佛,卻都位高權重,讓人豔羨。
在並州,養不易,為才是正理。
謝裒一怔,立刻鄭重的點了點頭。他也是謝氏子弟,自當擔起肩頭責任。
見弟弟點了頭,謝鯤微微一笑,不再說這些正事,又開始逗弄兒子。謝裒搖頭苦笑,也湊了上去。
窗外,雨聲漸稀,風中。
作者有話要說:
謝尚是謝安的從兄,也是謝氏崛起的奠基人之一。
田余慶:陳郡謝氏在東晉發展的三個階段,分別以謝鯤、謝尚、謝安三個人為代表。謝鯤躋玄學名士,謝尚取得方鎮實力,謝安屢建外事功。
猜你喜歡
-
完結365 章
炮灰男配手撕假少爺劇本
榮絨死了。 為了賺錢給自己看病,他在工地刷外牆,安全繩脫落,高屋墜亡。 死後,他才知道原來自己是一本耽美抱錯文裡的假少爺。 書中,他為了得到男主週砥,死纏爛打。 真少爺被找到,他被掃地出門。 落一個眾叛親離的下場。 再次醒來。 榮絨回到了他二十歲,回到他大哥榮崢生日那天。 也是在他哥的生日宴上,因為他哥一個朋友出言侮辱了周砥,他在他哥的生日宴上大鬧了一場。 重生麼? 社死的那一種? — 榮崢是誰? 榮氏集團總裁,一個不近女色的工作狂,就連日後的周砥都得敬畏三分的人物,書中人設最叼的工具人男配。 榮絨:他還能再搶救一下! 榮崢目光冰冷,“怎麼,還想要我跟周砥道歉麼?” 榮絨手持紅酒酒杯,低低地笑了,“哥你說笑了。哥可是榮氏集團的太子爺。週砥也配?” 週砥:“!!!” 眾賓客:“???”
80.8萬字8 33659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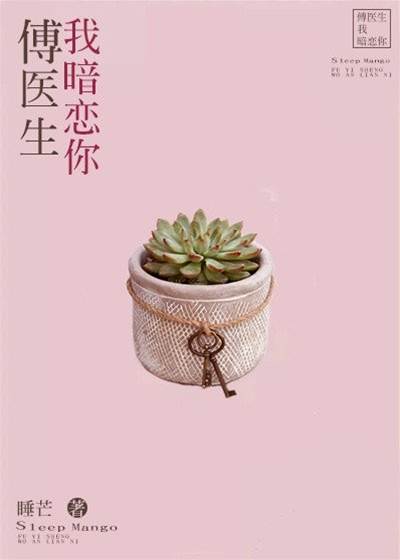
傅醫生我暗戀你
暗戀傅醫生的第十年,林天得知男神是彎的! 彎的!!!! 暗戀成真小甜餅,攻受都是男神,甜度max!!!! 高冷會撩醫生攻x軟萌富三代受 總結來說就是暗戀被發現後攻瘋狂撩受,而受很挫地撩攻還自以為很成功的故事……
44.4萬字8 7319 -
完結305 章

病美人替身不干了
沈郁真心爱一人,不惜拖着病体为他谋划、颠覆王朝,死后才知,他只是话本里主角受的替身,活该赔上一切成全那两人。 重生归来,一身病骨的沈郁表示他不干了。 这人,谁要谁拿去。 他则是代替了庶弟进宫做那暴君的男妃,反正暴君不爱男色,况且他时日无多,进宫混吃等死也是死。 进宫后面对人人都惧怕的暴君,沈郁该吃吃该喝喝,视暴君于无物。 青丝披肩,双眸绯红,难掩一身戾气的暴君掐着沈郁脖子:“你不怕死?” 沈·早死早超生·郁略略兴奋:“你要杀我吗?” 暴君:“?????” 本想进宫等死的沈郁等啊等,等来等去只等到百官上书请愿封他为后,并且那暴君还把他好不容易快要死的病给治好了。 沈郁:“……” 受:在攻底线死命蹦跶不作不死 攻:唯独拿受没办法以至底线一降再降
70.2萬字8 16421 -
完結114 章

貌合神離
你有朱砂痣,我有白月光。陰鬱神經病金主攻 喬幸與金主溫長榮結婚四年。 四年裏,溫長榮喝得爛醉,喬幸去接,溫長榮摘了路邊的野花,喬幸去善後,若是溫長榮將野花帶到家裏來,喬幸還要把戰場打掃幹淨。 後來,溫長榮讓他搬出去住,喬幸亦毫無怨言照辦。 人人都說溫長榮真是養了條好狗,溫長榮不言全作默認,喬幸微笑點頭說謝謝誇獎。 所有人都以為他們會這樣走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溫長榮的朱砂痣回來了,喬幸的白月光也回來了。
32.8萬字8 90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