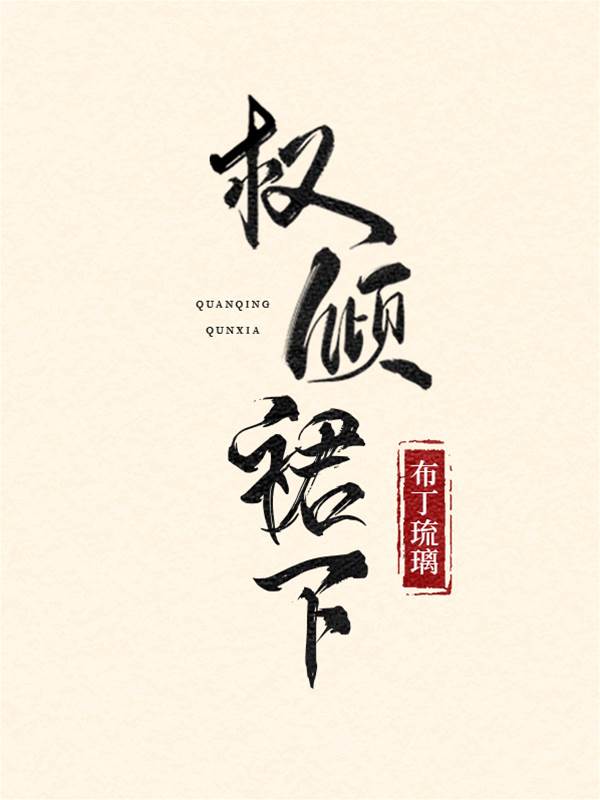《吉時已到》 076 太子的八卦之心
“彼時城池前后失守,各族大小部落恨不能趁機一舉瓜分我大盛疆土,急報頻頻京,諸位為此日夜宮商議應對之策,朝堂上下為此惶惶……敢問若無定北侯平定晉王之,接管營洲,三年收回五城,大大威懾了北地異族,振我大盛軍士人心士氣,又何來今日之穩固!如此赫赫功績皆是靠得拼搏而來,所謂‘貪’功之說究竟從何說起?”
此言讓站出來彈劾蕭牧的眾員皆面微變。
“其三——”太子言及此,看向了立于文臣之首的姜正輔:“姜大人也道當年北地形勢混艱難,為穩固局面才讓定北侯接管,如此也等同是肯定了定北侯的功勞——若只因些不知真假的揣測,便妄加遏制治罪于功臣,豈非是要寒了眾武將之心?北地五城初收復,若便急于施如此于過橋拆河無異之行徑,朝廷威信究竟何在?日后誰人還敢有報效之心?”
他語氣不重,然其中字字鋒利。
殿一時寂靜可聞針落。
一位是當朝太子,一位是中書令姜大人……
而眾所皆知,姜大人曾任太子傅之職,教習過太子功課——
而今師生對峙殿……
面對當今儲君,姜正輔面依舊威嚴:“殿下,此事不可只觀表面,當為長遠計!”
“吾知姜大人是為大局慮,然而若只憑揣測來否定定北侯之忠心,戕害良將能臣,又與因噎廢食何異?”
“殿下所求乃仁義之策,本無錯,只是也要講求因時制宜——對待此等擺在眼前的患若不盡早扼除,難道要眼睜睜看著其一味坐大,以致來日無可挽回嗎?”姜正輔定聲反問。
“可若弄巧拙,反倒反良臣,使得北地局面失控,屆時又當如何應對?”
Advertisement
“若當真會因己過被罰,而行造反之舉——那恰可說明定北侯暗藏不忠之心已久,藏此禍心者,遲早有一日會因種種因而歧途,難道要讓下至朝臣上至陛下百般遷就忍耐于他,以防此況發生嗎?須知一味退讓不可取!”
“姜大人此言實在有失客觀!”一名史趁機站了出來,目不斜視地道:“當年晉王之中,姜大人膝下獨子因自薦前往勸降晉王,而不慎喪命。彼時多有傳言,道是令公子淪為晉王人質,用以脅迫定北侯退兵,定北侯未允,才致使令公子喪命于晉王刀下——”
這段舊事被提及,太子無聲握了袖下十指。
方史無視著姜正輔漸漸寒下的臉,聲音依舊抑揚頓挫:“單不論傳言真假,縱是為真,有人傷亡亦是兩軍戰之常態,姜大人痛失子,令公子為朝捐軀,自是可嘆可敬可憐之事——可姜大人若為此遷怒定北侯,頻頻加以針對詆毀,如此公報私仇,未免過于罔顧朝綱,人不齒!”
這番話讓殿氣氛愈發張冰寒。
“本從未詆毀過蕭牧!所言字字句句皆實!”姜正輔一字一頓道:“反倒是閣下,單以區區揣測便來污名本,倒更像是有失客觀的那一個!史臺進言,如今竟全靠臆測了嗎?”
方史還要再言,卻被龍椅上的一陣咳聲打斷。
“……好了,諸位卿勿要再因此事爭執……”皇帝呼吸有些不勻地道:“此事,朕會細細權衡思慮,朕不會姑息養,卻也更加不會戕害忠臣……”
聽著這一如既往地模棱兩可之言,眾臣唯有應合著:“陛下圣明。”
姜正輔等人也只有緘默下來。
皇帝側的掌事太監見狀適時開口:“諸位大人可還有其他事要奏?”
Advertisement
姜正輔抬手,面容繃:“臣等無本要奏。”
旋即,便有監高唱“退朝——”之音于殿回。
百跪拜叩首,恭送皇帝。
待帝王為監所攙的影消失,眾臣方才先后起。
四下起嘈雜之音,姜正輔退出大殿,轉步下漢白玉階。
“老師留步。”
一道聲音自后傳來,姜正輔駐足,回頭看去。
面容溫潤、約二十四五歲的年輕人正朝他抬手施禮:“方才于殿于老師多有頂撞之言,還老師見諒。”
姜正輔抬手還禮,面稍緩:“殿下言重且折煞老臣了,朝堂之上各抒己見而已,無可厚非。”
太子再施一禮:“老師大量。”
二人一同往前走去,姜正輔到底還是道:“有些話,方才在殿上老臣不便言明,營洲當下如同一漩渦,各方勢力聞藏寶圖三字而……而營洲地關鍵,毫馬虎不得……”
說著,腳下微頓,似微微回頭看了一眼宣政殿的方向,聲音得愈低,卻越發肅然:“陛下龍欠安,正是關鍵之時……如此關頭實在不宜出任何差池,北地之事,殿下還是早做決斷為好。”
“吾明白老師的苦心,寧可自己背負諸多非議,也要為吾、為大盛謀長久計——”太子神態恭儒,言語間卻著堅持:“但吾認為,定北侯并非心懷不軌之人,愈是關鍵之時,吾愈不愿見有錯冤忠臣之事發生。”
約聽出他后半句話中所含之意,姜正輔收斂神,道:“看來臣已無甚是可以教給殿下的了。”
“老師所授,已足夠吾用終。”
姜正輔垂眸抬手:“不敢當此言——臣尚需前往政事堂料理公務,便先告辭了。”
Advertisement
“老師慢走。”
太子目送姜正輔離去,于原注視那道背影良久。
直到監尋上前來:“殿下……”
“回吧。”太子負手,轉而去。
其回至東宮時,正遇吉南弦于廊下安排今夜值宿之事。
“殿下。”吉南弦上前行禮。
“可得空陪吾手談一局嗎?”太子含笑問。
“此乃微臣之幸也。”
吉南弦直起,跟在太子后進了書房。
監很快擺上棋盤,奉上茶水。
房門被合上,二人對弈間,太子說起了早朝之事。
吉南弦認真聽著,卻并不多言。
“定北侯如今陷藏寶圖傳言之中,不僅各方勢力虎視眈眈,朝堂上下對其不滿之聲也日漸鼎沸,如此境地,吾很擔心他是否能頂得住這諸般力……”
“所以殿下才于早朝之上直言回護,為的便是平衡那些不滿之聲,以緩定北侯當下境之艱——”
說白了,也是怕將人給急了。
當今太子殿下,從來都不是只會心慈手之人。
“是也不全是。”太子不聲,落下一子:“南弦,你如何看待定北侯蕭牧此人?”
他與吉南弦年紀相仿,時也曾有些集在,私下于稱呼上便親近些。
“臣與這位蕭侯素未謀面,倒是無從評價。”
太子搖了搖頭,笑嘆口氣:“你總是這般謹慎的……”
吉南弦聞言也笑了笑,旋即道:“于大局而言,臣的確不宜妄下結論,但臣之幺妹在信中倒是稍稍提過蕭侯幾句……”
“吉小娘子?如何說?”
“道是蕭侯治下百姓安居樂業,舍妹這般心與之亦能相甚歡,可謂頗為投緣了。”
“哦?相甚歡?不知是哪一種相甚歡?”
Advertisement
太子目含好奇,忽然滿臉的八卦之——須知蕭侯不近的傳言已久,他也是有所耳聞的!
吉南弦輕咳一聲:“應只是字面意思罷……”
沒聽到想聽的,太子有些失,很快卻也笑起來:“吉小娘子的子吾是知道的,能與其投緣之人,必然也是個妙人了!”
再落子之時,忽而道:“就私心而言,吾并不懷疑蕭牧的忠心。”
這干脆到稍顯“天真良純”的話,讓吉南弦頗意外:“殿下與定北侯有過集?”
“不,只三年前其京領賞之際,吾曾見過一面……”太子笑了一聲,道:“說來的確古怪,正因這一眼,便吾覺得十分合眼緣。”
吉南弦愈發驚訝了,旋即不知想到什麼,也目笑意:“據舍妹所說,這位蕭侯樣貌俊,堪比神仙……”
“倒也對!”太子笑著道:“如此樣貌者,任誰見了,怕都會覺得合眼緣了……看來吾也只不過是塵世間一淺之人罷了。”
話音落時,角笑意也變得淺淡凝滯了。
再著眼前的棋局,只覺恍惚周事變,時瞬移,面前與之對弈者,也變幻了模樣——
一聲仿佛從昔年傳來的喚聲在耳邊響起——
‘殿下,該你了——老規矩,拖延至十息未落子,可就算認輸了!’
太子著‘他’,笑了笑。
若論生得好看,不得就要提一提他‘面前坐著’的這位年郎了。
年不過十四五歲,已有冠絕京師之名,本就生得一幅頂好樣貌,又因出鼎盛武將之家,灌溉出一蓬英氣,眉宇間意氣風發,如初升朝般奪目。
那個自習武,打馬穿過繁華的東長安街,錦佩劍,任誰見了都要稱一句“時小將軍”的年……這世間,再也尋不見了。
或者說,當年那四位形影不離的年,皆尋不見了。
四人先后去其三,僅還在這世間活著的一個他,也早沒了昔年模樣。
“殿下?”
吉南弦的聲音,讓太子自往事中回神思。
棋子落在棋盤之上,發出“啪嗒”一聲輕響。
吉南弦正思索著方才這位太子殿下的異常之時,只聽對方又拿難掩好奇的語氣問道:“南弦,方才你說……令妹夸贊蕭侯樣貌堪比神仙?還說了些什麼,能否給吾展開講講——”
吉南弦:“……!”
……
天將晚,姜正輔出宮歸家,剛下了轎,進府門,便習慣向迎上前的家仆問道:“姑娘今日如何?可有按時吃藥用飯?”
“回郎主,姑娘一切皆好,聽院使說,今日胃口也不錯,早早用了晚食,此時大約已歇下了。”
姜正輔微放心了些,點頭道:“近來天寒,飲食起居,讓底下的人都務必仔細伺候著。”
“是。”
待罷了兒之事,姜正輔回院更罷,便去往了書房。
“大人,這是營洲送來的書信……”一位幕僚先生捧上一則信。
姜正輔拆開了看,微微皺眉:“此人多是無用了些——”
“倒也不能全怪此人辦事不力,只能說蕭牧行事太過謹慎……”幕僚勸說道:“當下營洲城被蕭牧治理得如同鐵桶一般,再想安眼線已是不能,此人已是最好用的一顆棋了……”
姜正輔不置可否,轉念想到今日早朝之上的不順,眼神明滅不定了片刻。
“回信,告訴他,本的耐心已經不多了,接下來……”
晚風自窗乃灌,恍若在竊聽屋之人的低聲談話。
……
另一邊,永長公主召宮,此時已來至皇帝寢宮外。
“長公主殿下可算來了……陛下等候您多時了。”掌事太監上前行禮,親自將人迎殿,邊低聲說道:“陛下自今日早朝后,便起了熱,待到晚間,便一直念叨著想見您……”
永長公主披著錦裘,聞言眉間憂頗深。
隆冬天寒,殿之中燒著地龍不便開窗,便積攢了些苦藥氣。
“姑母。”
守在龍榻邊的太子向來人行禮。
永長公主微一點頭,來至龍榻前,福行禮:“永參見皇兄……”
“永來了啊……”皇帝躺在那里,聲音虛弱地道:“昶兒,你先退下……朕同你姑母有話說……”
“是,兒臣告退。”太子行禮罷,抬眸之際,下意識地看向長公主。
長公主朝他微微點頭,示意他不必擔心。
太子這才緩緩退了出去。
皇帝讓掌事太監屏退了殿中的宮人,單獨和胞妹說著話。
“永,朕近來總會夢見時之事,夢到,朕,正輔,你,還有他……我們四人來遲,被吉太傅罰站頂書……你知道嗎,朕于夢中亦在苦思……”
他和永長公主乃是嫡親兄妹,皆是已故皇太后所出,年紀僅差兩歲,時一起讀書識字,相伴長大。
或正因永長公主與他共同經歷過時到時的那段時,于是當他于這孤寂深宮中獨自“念舊”時,便總會想到這個妹妹。
想到是想到,真正因此將人到跟前時,卻是頭一遭。
永長公主覺得,這大抵是要“歸功”于皇兄此時起著熱,神思實在是有些糊涂之故。
在床榻邊的鼓凳上慢慢坐下,嘆息般問:“皇兄在苦思何事呢?”
“朕想不通……他究竟為何要背叛朕!背叛他立下與朕一同守護大盛江山的誓言,背叛我們一同長大的手足誼!”
縱是時隔已久,縱是病中,提及此,皇帝的神亦眼可見地激起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81 章

愛妃在上
愛妃,良宵苦短,還是就寢吧。某王妃嬌媚軟語,伸手輕輕地撫摸著某王爺的臉頰:王爺,咱們不是說好了,奴家幫王爺奪得江山,王爺保奴家一世安穩,互惠互利,互不干涉不是挺好嗎!愛妃,本王覺得江山要奪,美人也要抱,來,愛妃讓本王香一個…王爺您動一下手臂行嗎?王爺您要好好休息啊!某王妃吳儂軟語。該死的,你給本王下了軟骨香!呵呵,王爺很識貨嘛,這軟骨香有奴家香麼?
56.1萬字7.67 24331 -
完結272 章

邪王獨寵:傾城毒妃狠囂張
金牌殺手葉冷秋,一朝穿越,成了相府最不受寵的嫡出大小姐。懲刁奴,整惡妹,鬥姨娘,壓主母。曾經辱我、害我之人,我必連本帶息地討回來。武功、醫術、毒術,樣樣皆通!誰還敢說她是廢柴!……與他初次見麵,搶他巨蟒,為他療傷,本想兩不相欠,誰知他竟從此賴上了她。“你看了我的身子,就要對我負責!”再次相見,他是戰神王爺,卻指著已毀容的她說,“這個女人長得好看,我要她做我的王妃!”從此以後,他寵她如寶,陪她從家宅到朝堂,一路相隨,攜手戰天下!
48.8萬字8 25055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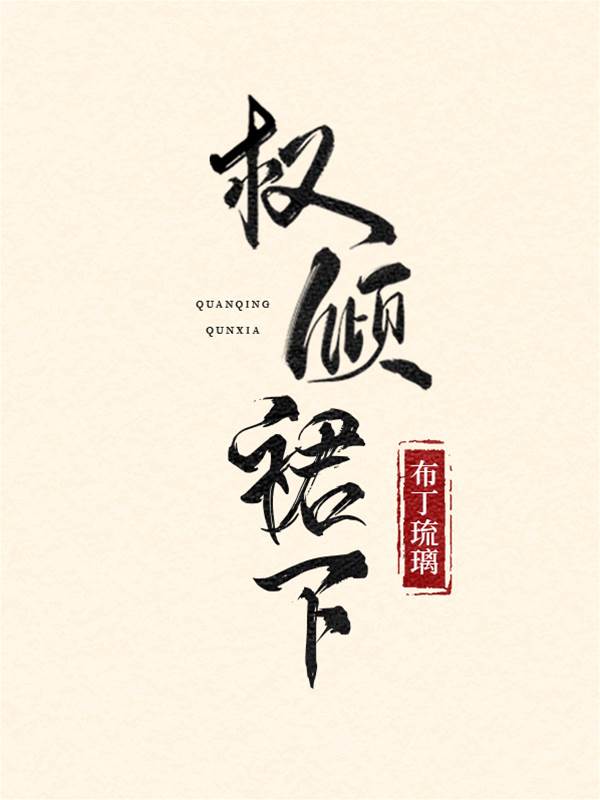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1779 章

快穿:病嬌大佬他好黏人南卿二二
南卿死亡的那一刻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能有一具健康的身體。死后,她綁定了一個自稱是系統的東西,它可以給她健康身體,作為報答她要完成它指定的任務。拯救男配?二二:“拯救世界故事里面的男配,改變他們愛而不得,孤獨終老,舔狗一世的悲劇結局。”“嗯。”不就是拯救男配嘛,阻止他接觸世界女主就好了,從源頭掐死!掐死了源頭,南卿以為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可是男配們卻一個個不粘世界女主粘
247.7萬字8.18 20931 -
完結63 章

長燁無月
【和親公主vs偏執太子】【小短文】將軍戰死沙場,公主遠嫁和親。——青梅竹馬的少年郎永遠留在了大漠的戰場,她身為一國公主遠嫁大晉和親。大漠的戰場留下了年輕的周小將軍,明豔張揚的嫡公主凋零於大晉。“周燁,你食言了”“抱歉公主,臣食言了”——“景澤辰,願你我生生世世不複相見”“月月,哪怕是死,你也要跟朕葬在一起”【男主愛的瘋狂又卑微,女主從未愛過男主,一心隻有男二】(男主有後宮但並無宮鬥)(深宮裏一群女孩子的互相救贖)(朝代均為架空)
20.9萬字8.18 17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