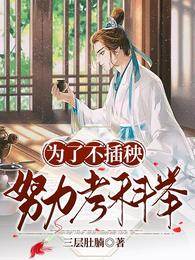《臨高啟明》 第210節 4大家魚
臨高啟明第二百一十節 四大家魚
想到關有德以前是“裝家”,陳五仁又問起魚花的事來:“關兄,我聽說九江的魚花皆從西海(西江)裝撈,為何不直接售于造家塘飼養?何需經裝家之手?”
關有德道:“老先生果然是心思細之人,疍戶撈上來的魚花不純,其中各魚種皆有,切不可隨意混養,否則一塘之恐無類。裝家之功在于將疍戶撈的魚花分類撇開,只留鯇、鰱、鳙、鯪,稱為四大家魚。”
如何將魚花分開,這自然就是裝家的了,多為裝家世代傳襲,不示人。
作為本地人,陳五仁對四大家魚的概念還是有的。唐朝之前,漁民養的品種主要是鯉魚,由于唐朝皇帝姓李,李鯉同音,而以“鯉”象征皇族,不能捕,不能賣。因此,漁民不得不尋找新的養品種,鯇就是草魚;鰱就是鰱魚,也白鰱;鰱則是大頭魚,也花鰱;與長江流域不同,九江鄉民不養青魚,而是養俗稱土鯪、鯪公的鯪魚,這是華南地區特有的品種。到了明初,四大家魚配合養已經非常。
“倘若我族養魚,一畝之塘當畜魚多?”陳五仁問。
跟在一起的鐘吉聽著這等弱智問題,笑道:“凡池一畝,畜鯇三十,鰱百二十,鳙五十,土鯪千余尾。”
“為何土鯪之數相差如此懸殊?”發問的是天地會廣州地區的推廣經理林文,他印象中臨高可不是這麼養的。
鐘吉道:“兄臺有所不知,常言道;‘鯪魚不可養’,鯪魚喜熱,難以越冬,到秋冬季則十不存一,不越冬則不,不則價賤。”
“哦?四大家魚賣價還不一樣?”陳五仁問。
“每年略有不同,但總而言之,價以鳙、鰱貴,因其易長而不費草。鯪難長、有重至一斤者,又必歷冬寒才,而鯇費草,故價賤。”鐘吉答道。
Advertisement
“鯇費草多?”林文問。
“每鯇百尾,日需草百斤。鯇食草,而鳙、鰱食草之膠,或鯇之糞亦可。”鐘吉道。
作為天地會的干部,林文在臨高接過澹水魚養,他知道鰱魚和鳙魚都是濾食魚,一般用鰓濾取水中的浮游生,也喜歡食用豆餅、麥麩等飼料,由于沃的水滋生更多的浮游生,因此這兩種魚喜歡追逐沃的水,常在水中上層活。草魚屬于植食魚類,主要吃草,也吃部分谷、豆餅、蠶蛹、蚯引等,喜歡在水的中下層游覓食。土鯪最小,屬于雜食魚類,常常食用高等植的碎屑、底部的腐質,往往活在水的中下層。
水中層的草魚留下的大量食碎屑和糞便,是浮游生的絕佳養料,大量繁的浮游生又給鰱鰱提供了大量的食,底層的土鯪則對上、中層魚的食殘渣進行最后的清掃。后三者的存在使得食殘渣、浮游生不能大量富集,保證了魚塘水質清新。不同水層的魚追逐食,攪水,又增加了水中的溶解氧。因此,四大家魚的配合養是農業技史上的一次巨大飛躍,對有限的水進行了較為徹底的利用。
陳五仁問鐘吉:“不知買夏花當如何運回香山?”
鐘吉道:“香山有耕種家,魚市,老先生當雇人運回。賣于近的,則魚花大,賣于遠的,則魚花小。陸行者挑以兩籮,悠揚其肩,力使籮或上或下,激其水作波瀾,使魚如在池塘中,又行二三里,沉籮于河,以換新水,則魚得其。若水行者,則以魚花舟載魚,舟旁兩水車晝夜轉水,使新水舟,而宿水不留,然后魚花不病。九江至香山水運便利,老先生既是大戶人家,當以水運為佳。若是向我預訂,我可代先生尋一魚花舟送至貴鄉。”
Advertisement
“哦?魚花現在是何價格?”
“其實魚花與魚的價格差不多,”鐘吉出右手四手指,道:“每百斤鳙、鰱四兩銀子,鯇二兩,鯪一兩。”
考察組又不是真要買魚花,陳五仁聽了打起哈哈來,“夏花上市尚有些時日,不急不急,待我返鄉安排挑基,事之時定來尋鐘兄。”
“無妨,買賣不仁義在。”
陳五仁想起來之前掉的一件事,問關有德:“敢問關兄,四大家魚的魚花是如何篩選開的?”
關有德見他不訂魚花,又這麼一問,心中有些不悅,臉上雖然沒有表出來,但回答的語氣有些直白:“老先生的問題未免太多了,魚花,細如針,一勺輒千萬,唯九江人能辨之,撇‘花’乃我裝家吃飯的手藝,歷來都是家傳之法,從不外傳。”
陳五仁在臨高待久了,養了不懂就問為什麼的習慣,關有德這麼一說,他才意識到不妥。古代但凡有點技含量的手藝,基本上都是家族傳承或者師門傳承,而且傳男不傳,生怕兒出嫁將技帶到夫家去了。學徒則要跟師傅當牛做馬,充當若干年的免費勞力,才能從師傅那里學得手藝,當師傅的往往還要留一手,不然怎麼會有“教會徒弟死師傅”的俗語。
但在臨高,除了數機,哪個元老不是恨不得把所有知識都給手下的歸化民灌下去,生怕他們學不會。但凡到喜歡問為什麼的歸化民,技元老都是歡天喜地得如同中了大獎,捧在手心里當個寶。兩相對比,陳五仁不勝唏噓,差距為什麼就這麼大呢?
在魚花市晃許久,此時太已經升到頂,氣溫漸高,關有德是個藥罐子,覺有些力不支,便向考察小組告辭:“莫老爺,我子有些乏了,頭昏腦脹的,就不陪諸位了,還見諒。”
Advertisement
《騙了康熙》
莫魚駐守九江已經兩年,知道關有德所言不虛,也就不留他。關有德和鐘吉離去之后,林文才對陳五仁說:“陳科長,撇花的方法沒問到就算了,今后咱們靠人工繁育,不同品種的魚卵從一開始就分開了,也就不存在撇花這個環節了。他們愿意守著這個就讓他們守著吧,最好帶到棺材里去。”
陳五仁點點頭,“確實,不過首長叮囑我們務必搞清楚九江鄉魚花生產的所有環節,肯定有他的道理。看來這個事沒那麼容易搞清楚了。”
莫魚一聽是首長的吩咐,道:“這個簡單,下次有哪個不長眼的裝家落在我手里,我一定讓他說得一清二楚,否則別想從我手里熘走。”
陳五仁道:“莫兄,元老院向來依法治國,刑訊供可是要分的。”
“謝陳科長提醒,不用刑我也能讓他們老老實實代,嘿嘿……”莫魚笑起來。
“其實我之前聽農業部的首長提過撇花的原理,大上是據不同魚種生活在不同水層的習來進行區分,剩下的就是練度的問題了。”林文道:“通常浮在最上面的是鳙魚,中間的是鰱魚,稍下的是鯇魚,最下層的是鯪魚。把魚花放在竹筐后,讓它們游一兩小時,然后用木制涂白漆的魚碟將水輕輕攪,據各種魚在水中的不同層次,從上到下把魚撇出來。”
陳五仁道:“原理和實還是有區別的,別忘了除了四大家魚,里面還混有其他魚種,有些魚種生活在同一水層,魚花又細如針,要區分開來并不容易。”
林文道:“無所謂了,反正都是要進棺材的手藝。就目前探訪的信息來看,九江的澹水魚養技并不比我們更強,雖然這里已經代表了土著的最高水平。”
Advertisement
“小林子,你這話可是真的?”莫魚有些吃驚,雖然他很早就跟了元老院,知道元老院不管做什麼事都比本地人做得更好,但他沒想到連養魚這種事元老院也有技優勢。
林文道:“可不是!就拿四大家魚的投放比例來講,臨高每畝至投放一百尾草魚,鯪魚也就五百。他們投的草魚才三十尾,說明他們沒有足夠的草料,鯪魚卻要投放一千,這是還沒有索出鯪魚的越冬技。但最大的問題還在基塘比例上……”
莫魚聽林文竟然對九江鄉的基塘比例提出了質疑,好奇心頓起,問道:“正確的基塘比例應該是多呢?”
“沒有正確不正確,只有合適不合適。”林文也不賣關子,道:“臨高的基塘比例是‘六水四基’,而這里是反過來的,‘四水六基’,魚塘的生產力沒有發揮到最高。而且據我觀察,本地單口魚塘的面積大多在五畝以下,而臨高的魚塘要求在七畝到十畝之間。不過,‘四水六基’應該是與本地人的生產模式相適應的,既然桑基魚塘,蠶桑業對漁業同樣存在影響。”
莫魚聽了若有所思,道:“有道理,九江之利,多藉魚苗,次蠶桑,次禾稻,次圓眼,次芋。若是魚塘面積小了,基多塘,收益自然不足,確實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 加書簽 +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1548 章

重回八零小富妻
季清穿越到八十年代,搖身一變成了獨自帶四孩,被婆婆欺負到投河的小可憐。這還不算,她身上居然還揹著“破鞋”的名聲?季清擼擼袖子,拿財權、鬥妯娌、趕婆婆、搶房子、正名聲,風風火火全部拿下。唯一讓她犯愁的,是眼前這個突然冒出來的奇怪男人。不是要休她嗎,乾嘛把她壓在牆角醬醬醬醬。麵對一見麵就火急火燎的帥哥,季清嚥下一口口水,艱難表示:帥哥,雖然我是你老婆,但我跟你不熟好嘛!
148.4萬字8 132806 -
完結315 章

穿到明朝考科舉
現代大學生崔燮穿越了,穿成了明朝一個五品官的兒子,可惜剛穿越過來就被父親驅逐回遷安老家。他帶著兩個仆人在小縣城里住下來,從此好好生活,好好賺錢,好好考科舉,一步步回到京城,走上青云之路 本文有很多章讀書考試的內容,枯燥的八股文比較多
110.9萬字8.18 16152 -
完結4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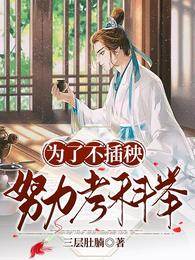
為了不插秧,努力考科舉
現代SSS級研究員猝死穿越到大興朝,身子一直體弱多病,養到六歲才被允許在地裏撿稻穗,被曬的頭腦發蒙的李景覺得他這身體以後務農,懸,當即決定讀書考科舉,這他擅長,插秧還是交給專業的人吧! 第二年,彼時已取名李意卿的某人自詡身體康複,興致勃勃要插秧。 “怎麼腳癢癢的”李意卿腦子裏閃過不好的預感,從水裏抬起腳。 “謔” 隻見一隻黑色蠕動的水蛭趴在他的腳趾縫裏吸吮著。 “啊”李意卿抓著手裏的稻苗快速跑上岸。 是時候頭懸梁錐刺股了,他要把書都翻爛了。
86.6萬字8 19474 -
連載526 章

開局大帝之上,閣下要如何應對
【無敵文 殺伐果斷 鎮壓當世 橫推萬古】林天母胎穿越神州大陸,成為荒古世家繼承人。他生而知之,並覺醒混沌聖體,修煉百年成就絕世大帝,震古爍今。林家一門雙帝,傲視天下,睥睨四海八方,號稱萬古不朽世家,於人間全無敵!為了突破更高境界,林天閉關修煉,大夢十萬年,再醒之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具石棺裏麵。他破棺而出,看到的卻是……“林家沒了?”林天懵了。他感覺隻是睡了一覺而已,居然就成了林家老祖,而且還是個光桿司令!林家人呢?難道都死光了?
93.7萬字8.18 154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