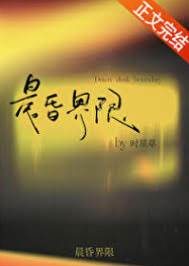《軍婚蜜寵:少帥大人讓一讓》 第169章真的很想
“你現在可是在我邊,我有什麽好吃醋的?要吃醋也是你的小友吃醋。”薑紅茶不以為意地打開午餐盒,放好筷子,“吃吧,剛剛從餐廳買來的。”
梅夏文看見薑紅茶雲淡風輕的樣子,心裏又了。
這個人向來知道如何激起他的好勝心……
三口兩口吃完午飯,梅夏文就拉著薑紅茶“一起睡午覺”。
……
“霍,這是最近幾周的照片。”霍紹恒的勤務兵範建將梅夏文和薑紅茶親茍且的照片放到霍紹恒的辦公桌上,“您打算怎麽做?要不要給念之發過去?”
霍紹恒一手夾著煙,一手拿起那些照片翻了翻,淡淡地說:“發過去幹嘛?這種照片,未年,不能看。”
隻要梅夏文不去國,霍紹恒本不會手。
再說梅夏文是顧念之自己挑的,就算是個渣賤男,也得自己去發現。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這個學分,得顧念之自己修。
霍紹恒在這方麵幫不了。
他將這些照片扔到一個專門的屜裏,隨手上了鎖,揮揮手讓範建出去了。
九月底的C城,正是秋老虎的時候,這幾天一天比一天熱。
霍紹恒靜靜地坐了一會兒。
他材偉岸高大,將一張高背椅填得滿滿地,俊到令人窒息絕的容帶著幾分剛毅決絕,在嫋嫋白煙中若若現。
夕的餘暉從百葉窗的隙裏灑落進來,在地上畫下一道道橫欄,像是不過去的階梯。
“霍?”世雄敲了書房的門。
霍紹恒將煙撚熄了扔到煙灰缸裏,“進來。”
“喔噢,霍,最近怎麽煙得越來越多啊?”世雄聞到一屋子的煙味兒,用手招了招,有些張,“是出了什麽事嗎?”
“沒有。”霍紹恒指了指自己麵前的位置,“坐。你有事?”
Advertisement
“沒事就好。”世雄坐了下來,開始嬉皮笑臉:“我是剛才見到範建了,聽說他拍了一些……嗯……很勁的照片,我來霍這裏開開眼界,提高一下抗**的業務水平。”
霍紹恒打開屜,將梅夏文和薑紅茶的照片扔給他,“看吧,跟白斬似的,恐怕提高不了你抗**的水平,但是能提高你抗惡心的水平。”
世雄接過來,興致地一張張翻看,一邊看,一邊評點:“嗯,是白,也沒什麽,確實像白斬,但是這的材不錯,瞧這高難度作都能做,應該是老司機。”
霍紹恒:“……你懂得真多。”
“跟念之學的,您知道,我要照顧,必須要學這些網絡語言啊,不然會有代。”世雄頭也不抬地說道,終於細致地看完了所有照片,嘖嘖稱讚:“拍照的是範建吧?這小子的角度和影把握得越來越好了,有幾張選景黑白錯,都能當藝照了。”
“有嗎?”霍紹恒眉頭微蹙,“你不覺得惡心?”
“……我覺得不錯的,兩人的材都比普通人好多了。”世雄嘿嘿直笑,賊眉鼠眼地打量霍紹恒:“……霍,您不會是功能失調了吧?這可不好,還是要保證健康。男人***起就是健康的標誌。”
霍紹恒唰地一下將煙灰缸往世雄臉上扔過去。
世雄側頭躲過,笑著道:“開玩笑,開玩笑。不過我說真的,霍,您不打算結婚了嗎?您今年二十八歲了吧?”
霍紹恒的行蹤他的生活書們最清楚。
這六年來,他沒有一天是自己的時間,從來沒有見過他跟任何私下往,當然更沒有朋友。
“管好你自己。”霍紹恒看都不看他,打開自己的電腦開始工作:“給我查查行程,把念之生日前後兩天空出來。”
Advertisement
“喔咧!您要去國給念之過生日?!我也去好不好?!念之十八歲生日啊!是個大日子!”世雄眼前一亮,滿臉地看著霍紹恒。
“嗯,你當然也要去。”霍紹恒點點頭,“都是看著長大的。”
當年那個十二歲張到神經質的胖乎乎的小姑娘,如今真是完全變了個模樣。
十八歲生日不僅對顧念之,對他們這些人來說,也是一個重大的日子。
霍紹恒要去國給顧念之過生日,肯定不能以他的真實份去。
不過這對特別行司來說,本不是問題。
世雄辦這種事早就駕輕就了。
……
兩周之後,何之初終於回來了。
他風塵仆仆地下了飛機,第一件事就是去國會山大廈看顧念之在做什麽。
顧念之卻不在撥款委員會辦公室。
“Mary,我的學生呢?”何之初微笑著將一個小禮放到Mary的辦公桌上。
Mary指手畫腳,非常誇張地說:“你是問顧吧?去別的辦公室聊天去了。這幾天沒有什麽事,經常去竄門,這裏的人都認得,是一朵歡樂的小玫瑰。”
何之初雖然還在笑,但是額頭的青筋已經約出了痕跡。
好啊這小丫頭片子,不肯好好工作,還到竄,真是欠收拾。
何之初轉直直地走了出去。
……
他站在海洋通行自由委員會辦公室的門口,兩手在兜裏,看著一個穿香奈爾小套的俏子,在一群隻穿黑白西裝的議員和工作人員當中特別醒目。
這子正是顧念之,坐在海洋通行自由委員會主席約翰邊,笑容滿麵地跟他閑聊。
這兩周以來,顧念之在撥款委員會幾乎沒法工作,因為賬號出了問題,後來完全不能用了。
Advertisement
何之初不在,又不願意去找溫守憶,索什麽都不做了,每天在各個委員會裏晃悠,學著黃師兄自來的本事,很快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跟大家打一片。
各位議員和工作人員在工作之餘,能有個俏伶俐的東方小姑娘說說話,聊聊天,還是很高興的。
“約翰先生,您確定國真的要退出國際海洋公約?可是我知道,當初國還是這個公約的起草人之一啊?”顧念之忽閃著一雙大眼睛,恰如其分地表現出智商不在線的樣子。
“你這麗的小腦袋是想不明白這個道理的。”約翰笑嗬嗬地搖頭,打開電腦調出一份文件給看,“知道這是什麽?”
顧念之皺了皺眉,湊過去,看見一份非常古遠的掃描文件出現在約翰的電腦顯示屏上。
那文件的紙張都發黃了,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
看了看文件的落款,菱角紅圓圓地張了起來,“啊?居然是上個世紀的文件?!”
“對,當年的國聯,你知道吧?我們國還是發起國呢,最後因為議會反對,所以我們沒有加。”約翰哈哈大笑,“有意思吧?我告訴你,國際政治就是這樣,別指有所謂的法律和公平。一切都是實力說話,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利益。如果加公約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那就肯定加。現在這個公約阻礙了我們的國家利益,還待在裏麵幹嘛?任人宰割嗎?”
“……你不覺得一個國家這樣出爾反爾,有些丟人?”顧念之瞥了約翰一眼,“國耶,超級大國。”
約翰傲慢地翻了個白眼,“我管別的國家怎麽看我們?不服去死。”
顧念之朝他出大拇指:“霸氣!不愧是西楚霸王!”
“什麽是西楚霸王?”約翰十分好學地追問。
Advertisement
顧念之唔了一聲,正盤算如何把西楚霸王最後自刎的下場委婉地表達一下,就聽門口傳來幾聲清冽悉的咳嗽聲。
顧念之訝然回頭。
何之初玉樹臨風的站在門口,但是臉上的表如同北極寒冰,視線冷冷地落在顧念之上,像是要將凍雕像。
卻一點都不在意,也不害怕,笑嘻嘻地起快步走到他邊,仰頭驚喜地說:“何教授,你終於回來了!我想死你了!”
何之初滿腹的怒氣被顧念之這一聲激的招呼打得煙消雲散。
他出手,拉著的胳膊,對這個辦公室的人點點頭,帶著轉離去。
黃師兄知道何之初來了,趕追了出來,卻發現走廊上已經空空如也。
何之初已經帶著顧念之出去了。
“何教授,您終於回來了。唉,這兩周我是度日如年啊。”顧念之的小特別甜,各種暖心的話不要命地往何之初上招呼。
何之初的角越翹越高,滿臉的冰霜融化得幹幹淨淨。
他們去顧念之的辦公室拿了的小背包,然後帶上了勞斯萊斯,吩咐司機:“回莊園。”
顧念之這才不安地說:“……何教授,您剛回來?”
何之初點點頭,“剛下飛機。”說著扭頭仔細打量吹彈得破的俏麗麵龐,“你過得不錯啊,我看胖了不。”
“啊——不是吧!”顧念之雙手捂著臉,張起來,“看來又要減了,晚上回去不吃晚飯。”
何之初白了一眼,“小孩子減什麽?小心長不高。”
“我已經夠高了,不用再長高了。”顧念之堅持,“再長就要橫著長了。”
何之初的目落到穿著的一雙高跟鞋上,“咦?連高跟鞋都會穿了?”
顧念之了腳,有些不好意思,“那是為了配我上這套套……”
何之初忍不住手的頭,“真的很想我?”
“真的很想。”顧念之使勁兒點頭,“您不在,溫助教可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
接著,blahblah又告了溫守憶一狀。
何之初聽得麵越來越黑,最後慢吞吞地說:“……你想我,就是想我回來給你撐腰?”
“何教授真聰明,一語中的!”顧念之給他歡喜點讚,“您再不回來,我這半年也是白搭,什麽都沒法做。”說著,把的賬號出了問題的事,也說了一遍。
何之初沒有接話,一個人靠在後車座上,有些無奈地了眉心。
就知道這小沒良心的本不是想他,隻是想要借助他的手,整治別人而已……
“何教授?您累了?”顧念之坐不住了,“還是讓我回去吧。您多歇兩天。”
何之初放開手,角抿得的,一雙瀲灩的桃花眼越來越淡漠,跟他涼薄冷冽的神配合得天無。
他看了一會兒,問道:“我兩星期不在,你就什麽事都沒做?”
“我試圖做了,我也找到了您說的那個原因,但是我的賬號後來就被降到跟遊人一樣的權限,本什麽都做不了。”顧念之聳了聳肩,“您不信,可以自己去查。”
何之初二話不說拿出手機,先往國會那邊打了一圈電話。
很快證實了顧念之的話。
國會那邊接電話的人對何之初非常客氣,笑著保證:“隻要何先生您簽個字,我們馬上放開您學生的權限。”
“嗯,我明天簽。”何之初弄清了始末,也沒有再苛責顧念之了,他斜睨著:“你怎麽不去找溫助教?這種事,也能擺平。”
“……我不想跟打道。”顧念之直言不諱地說,“您又不在這裏,萬一又挖個坑給我跳,我哭給誰看?”
何之初噗嗤一聲笑了,繼續的頭,“你現在逮著機會哭給我看了?”
“我哪有哭?我是正正經經告狀好不好。”顧念之錯開頭,避開何之初的手,“您不要再我的腦袋了,我就快滿十八歲了。”
何之初回手,麵冷了下來,“我知道,不用你提醒我。”
顧念之其實真的有事要提醒他,但見他一副不想說話的樣子,隻好悻悻地閉了,偏頭去看車外的風。
勞斯萊斯一路安靜而平穩地將他們送到了何之初在龐馬克河附近的莊園。
大鐵門往兩邊打開,出一條通往前方白大宅的柏油路,路旁都是綠茵茵的草地,草地上零星砌著幾個花圃。
有西班牙裔的園丁在花圃裏修剪枝椏。
見勞斯萊斯駛進來,大家都停下手裏的活兒,對著大車招手。
顧念之好奇地看著這一切,扭頭對何之初說:“何教授,做律師能掙到這麽多錢?!”
就算能,也應該是等到何之初七老八十,才有這麽多錢吧?
可看他的履曆,他才二十八歲啊!
再能幹,他是如何在短短的三年之賺到這麽大的家?
何之初看出的疑慮,但是不打算給解。
他冷著臉先下車,然後站在車邊,給顧念之打開車門,讓下車。
不管是勞斯萊斯的司機,花圃裏麵的園丁,還是迎上來的管家,都看傻了眼。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05 章

晚安,蘇醫生
作為一名醫術精湛的外科醫生,卻被人用威脅用奇葩方式獻血救人?人救好了,卻被誣陷不遵守醫生職業操守,她名聲盡毀,‘病主’霸道的將她依在懷前:“嫁給我,一切醜聞,灰飛煙滅。”
35.7萬字8 19772 -
完結209 章

日日招惹,矜貴男主被勾纏失控了
【極限撩撥 心機撩人小妖精VS假禁欲真斯文敗類】因為一句未被承認的口頭婚約,南殊被安排代替南晴之以假亂真。南殊去了,勾的男人破了一整晚戒。過後,京圈傳出商家欲與南家聯姻,南家一時風光無限。等到南殊再次與男人見麵時,她一身純白衣裙,宛若純白茉莉不染塵埃。“你好。”她揚起唇角,笑容幹淨純粹,眼底卻勾著撩人的暗光。“你好。”盯著眼前柔軟細膩的指尖,商時嶼伸手回握,端方有禮。內心卻悄然升起一股獨占欲,眸色黑沉且壓抑。-商時嶼作為商家繼承人,左腕間常年帶著一串小葉紫檀,清冷淡漠,薄情寡欲。卻被乖巧幹淨的南殊撩動了心弦,但於情於理他都不該動心。於是他日日靜思己過,壓抑暗不見光的心思,然而一次意外卻叫他發現了以假亂真的真相。她騙了他!本以為是自己心思齷鹺,到頭來卻隻是她的一場算計。男人腕間的小葉紫檀頓時斷裂,滾落在地。-南殊做了商家少夫人後,男人腕間的小葉紫檀被套入了纖細的腳踝。男人單膝跪地,虔誠的吻著她。“商太太,今夜星光不及你,我縱你欲撩。”從此,做你心上月。
31.5萬字8.18 15202 -
完結156 章

掌心獨寵:錯撩權勢滔天的大佬
【雙潔 先婚後愛 頂級豪門大佬 男主病嬌 強取豪奪 甜寵 1V1】人倒黴,喝涼水都塞牙去中東出差,沈摘星不僅被男友綠了,還被困軍閥割據的酋拜,回不了國得知自己回敬渣男的那頂「綠帽」,是在酋拜權勢滔天的頂級富豪池驍“能不能幫我一次?”好歹她對他來說不算陌生人“求我?”看著傲睨自若的池驍一副不好招惹的模樣,沈摘星咬牙示弱:“……求你。”聞言,男人突然欺身過來,低頭唇瓣擦過她發絲來到耳邊,語氣冷嘲:“記得嗎?那天你也沒少求我,結果呢……喂、飽、就、跑。”為求庇護,她嫁給了池驍,酋拜允許男人娶四個老婆,沈摘星是他的第四個太太後來,宴會上,周父恭候貴賓,叮囑兒子:“現在隻有你表叔能救爸的公司,他這次是陪你表嬸回國探親,據說他半個身家轉移到中國,全放在你表嬸的名下,有900億美元。”周宇韜暗自腹誹,這個表叔怕不是個傻子,居然把錢全給了女人看著愈發嬌豔美麗的前女友沈摘星,周宇韜一臉呆滯周父嗬斥:“發什麼呆呢?還不叫人!”再後來,池驍舍棄酋拜的一切,準備入回中國籍好友勸他:“你想清楚,你可能會一無所有。”池驍隻是笑笑:“沒辦法,養的貓太霸道,不幹幹淨淨根本不讓碰。”
28.6萬字8 15484 -
完結578 章

億萬寵婚:神秘老公狠兇猛
他是A市帝王,縱橫商界,冷酷無情,卻唯獨寵她!“女人,我們的契約作廢,你得對我負責。”“吃虧的明明是我!”某宮少奸計得逞,將契約書痛快粉碎,“那我對你負責!讓你徹底坐實了宮夫人的頭銜了!”婚後,宮總更是花式寵妻!帶著她一路虐渣渣,揍渣女,把一路欺負她的人都給狠狠反殺回去。從此人人都知道,A市有個寵妻狂魔叫宮易川!
106.2萬字8.18 5443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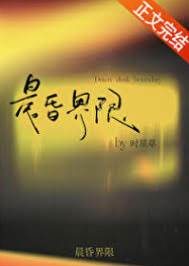
晨昏界限
林霧有些記不太清自己和陳琢是怎麼開始的,等她後知後覺意識到事情變得不對勁時,他們已經維持“週五晚上見”這種關係大半年了。 兩人從約定之日起,就劃分了一條明顯的,白天是互不相識的路人,晚間是“親密戀人”的晨昏界限。 而這條界限,在一週年紀念日時被打破。 - 人前不熟,人後很熟的故事TvT
27萬字8 56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