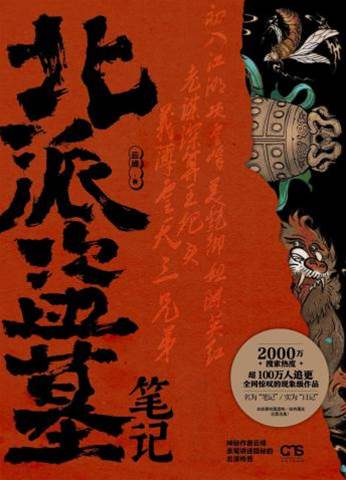《我是陰陽人》 第104章 好壞事 還700鑽鑽更2000推薦
“你是?”他好像還沒做好準備聽這個答案。[
我點下頭:“我是,說的好聽點人,其實就是雙人,你明白了嗎。”
他的眼神隨即就忘我的口去:“所以。你的那個,是假的?”
這麼被人看很不舒服,我護住口,後退了一步:“當然是真的!只是你有的我也有而已!”
程白澤的臉僵了一下:“我有的……你也有?”
吐出一口氣,我站到他面前:“反正就把話說開了吧,,可能幾百萬裡出我這麼一個,但這也不是我自己能選擇的,你要是覺得我怪異,從今以後可以跟我保持距離。反正……”
“我沒覺得你怪。”程白澤直接出口,指了指我的臉:“你看你看上去眉清目秀的,誰說你怪了,你總得給我幾秒鐘接的過程不是,我說的人不是你說的那個層面的,我是指你的,我師父曾經說過,我要找的就是個……”
我敢發誓,他這是說禿嚕了,挑挑眉:“你師父讓你找人?是不是就是你說要殺的那個?!”
他有些無語的看著我:“當然不是了,我說的殺人是開玩笑的嗎,的確是要找個人,但是有事要問他。我師父曾經跟他錯過了,所以,想讓我去找。”
“是嗎。”我手了自己的?子:“那興許就是我啊,你要殺的就是我吧。”
“姑,我那次真的是跟你開玩笑的,咱不當真行不。”
我忽然很想笑。看著他:“那你把那個金剛杵送我,我就不把你那話當真了。”
他哭喪的臉瞬間恢復正常,“算了,你就當我要殺人吧。警察是不是要來了,咱們倆下樓吧。”說完,他轉頭就走。
Advertisement
“哎!”我追上他:“也許你要找的人就是我啊,的嘛,那既然你師父都讓你來找我了,你是不是得把那個金剛杵送我。”
“不是你!!”
他猛地一嗓子嚇了我一跳,我看著他完全冷下來的臉,張了張:“不是我就不是我唄,大不了我不要了,看你那樣兒,你激什麼啊。”
……
“哎。真生氣了啊,我還得謝謝你呢,要不是你的法,我還救不了雪梅姨呢。”
“程酒窩?”
“程先生?”
我像個傻子似得圍著程白澤打轉兒,直到他僵下來的臉緩解了,才輕輕的呼出一口氣,暗暗地說要不是看你幫了這麼大的忙我纔不哄你呢!
“馬龍。”
他看著我忽然張口,我眼的看著他:“你不是還生氣吧,我不就要個金剛杵嗎,我知道貴重,大不了我……”
“你真不是。”
我愣了一下,顯然沒在一個頻道:“不是什麼?”
他吐出一口氣:“你不是我要找的人,我要找的人應該跟你很像但不是你,我師父說了,如果我看見那個人,第一眼的時候會看見他頭上的的。”
我訕訕的笑了笑:“我知道自己不是,我就是一山裡出來的,哪裡會有人找我啊,我就是跟你開玩笑呢,沒想到你會生氣,你別在意,我謝你的,今天的忙都靠你幫我了。”
他長久的看著我,忽然笑了起來,把臉往我面前湊了湊:“哎,我在生氣一會兒你能不能像剛纔那麼哄我,再試一次啊。”
“滾!”
我看著他頃刻間便喜怒無常的臉滿是無語的白了他一眼,他是裝的啊?但是不得不說,他這樣子倒是避免了很多我們之間的尷尬,新認識就吵架其實不得勁兒的,尤其他那一嗓子,我還真嚇到了。
Advertisement
雖然我表面上什麼都不太在乎,有些大咧,但是心卻是細碎敏的,我知道誰對我是真好的,我很謝他,我們萍水相逢,只是在昨天下午見了一面,今天他就能過來幫忙,還取來金剛杵給我救急,所以,我覺得他是個好人。
就在我們倆你一言我一語說著的時候,門鈴響了,我跑故去開門,看著小姑父跟幾個警察一起站在門外,小姑父看著我滿臉的張:“喬喬,你沒事兒吧,什麼白骨,你沒被嚇到吧!”
我指了指地下室方向:“就在地下室了,你們去看看吧,我剛開始看也嚇壞了!”
小姑父點點頭,顧不上一旁的程白澤跟著警察趕到了地下室,一看見牆上的骨還有掉在地下的,小姑父當時就懵住了:“怎麼會這樣啊,怎麼會有這種東西啊!”
我忙不迭的在旁邊解釋就說自己在樓上聽見怪靜了,然後就打開這個門下來看了看,當時忽然一陣,我很害怕,覺酒櫃後面的牆皮開始落,約的出來什麼東西然後我就把酒櫃推到一旁,牆皮就都落下了下來,看見的就是這個畫面了。
基本上就是合合理的胡編造,說完後我看著小姑父繼續張口道:“小姑父,你不是說這家的主人都去國外了嗎,那這骨頭是誰的啊。”
“這地下室是景康自己挖的啊。”小姑父裡唸叨著,看著警察已經往袋子裡裝那些白骨了,看來是準備拿回去化驗,驗吧,我心裡想著,一驗就知道是被王水腐蝕過的了,到時候再一查,劉景康想跑也跑不了。
“這家的原主人現在去哪個國家了。”看來小姑父已經跟警察說了我的況了,所以警察看著小姑父直接出口問道,小姑父有些著急:“我給他打個電話,問問他到底怎麼回事兒。”
Advertisement
“先不要打,如果案件跟他有關就不要打草驚蛇。”警察隨即在旁邊開口說道。夾介反。
小姑父擺了一下手:“沒關係,我知道怎麼問,就當我平常瞎聊了,要不然你們不也得知道他現在的位置嗎。”
聽小姑父這麼一說,警察便也不再多問,示意小姑父可以打了,我也看向小姑父,想聽聽那個那個劉景康現在過得是有多滋潤。
接通後小姑父一直說的是英語,我約的聽出來大概接電話那個不是劉景康的本人,隨後小姑父的臉就變了,一臉驚訝的樣子,又說了幾句話後應了兩聲ok就掛斷了。
“對方現在在哪裡?”
小姑父一臉不敢相信的樣子看向警察,張了張:“我給他診所去的電話,接電話的護士說他一個小時之前已經死了,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死狀很恐怖,好像是到了很大的驚嚇,那個護士已經報警了,說景康死的時候,一隻手的手指頭全被自己割下來了……”他說著說著就有些崩潰,蹲下:“怎麼會這樣啊!!”
“你不是說他跟他的人在一起嗎,現在打給他的人。”
小姑父搖搖頭:“我剛纔問了,那護士說從沒見過他的妻子……”
聽到這,我心裡已經瞭然,看來是方雪梅找過去了,所以,劉景康也得到了他的報應。
警察點了一下頭:“這樣,我們先把骨帶回去化驗,林小姐,最近我們希你不要離開本市,必要的時候可能要麻煩你配合調查。”
我點頭,這是正常的,只是那個劉景康太便宜他了,怎麼能就這麼死了呢,應該讓他去坐牢,讓他多遭遭罪,否則,他永遠不會知道自己錯了。
Advertisement
警察把地下室封了,小姑父跟我說讓我上他那去住,怕我在這住害怕,其實他不知道,現在反而是最乾淨的,我搖頭,跟小姑父說我閨過來了,我們兩個人在這作伴兒不害怕,小姑父的心不太好,叮囑了我兩句就跟著警察走了。
等他們一走,程白澤看向我:“看樣子現在找你出去吃飯也不可能了,你還得照顧你那朋友,那我也先回去了,有空我再給你打電話。”
我嗯了一聲,送他到門口:“謝謝你啊。”
“呦呵,你還客氣上了啊。”他笑了笑:“不過,我可不可以問問你哪天生日啊,等你過生日的時候作爲你的朋友我好給你裝備禮啊。”
作爲先生,我對問個人信息這些東西還是很謹慎的,看了他一眼:“你還不如說直接想給我卜一卦呢,幹嘛那麼虛僞還說要送我什麼生日禮。”
他有些尷尬:“好吧,我是想跟你看看,你要是介意的話我就不看了。”
我手直接把兜裡的臨時份證遞給他看了一眼:“想看你就看看吧,既然你現在的水準這麼高,那就順便給我看看我這個駁婚煞怎麼破。”
“哎……”沒等他說話,我直接關上了門,我知道自己氣的沒有道理,因爲這事兒我也的對他做過,而且最起碼人家明著說,我是著做的,但是被一個道行高的師揹著算自己的命,總覺得有點被窺**的覺,還是小不爽的。
……
三天了。
方雪梅那件事之後過去了三天了。
一件好事,一件壞事。
好事就是劉景康這案子定了,因爲骨就是方雪梅的,再加上他撒謊說妻子出國,只要稍微一查,他就敗了,但是他死了,所以這個案子定了也沒什麼大意義,我說的好事是指房子,因爲方雪梅死了,而劉景康又在國外死亡,而且還是不正常死亡的,需要走很多程序,因此,短期,沒人來管別墅的事,我跟許金可以暫時的放心住在這裡了。
壞事就是,許金居然病的很重。
當天晚上醒過來的,醒來後就一直髮燒,我怕燒出病,只好給背到醫院去,直接就在醫院裡住下了,醫生說之前一直神高度張,再加上沒吃什麼東西,太弱導致的,我知道這只是一方面,主要還是怪我,已經那麼虛了,在被方雪梅上一下肯定就抵抗不住了——
而這不是最鬧心的,最鬧心的是許金因爲折騰這麼一次把闌尾炎折騰犯了,醫生建議說做手,還一直在強調這是個小手,做完之後就再也不會因爲闌尾遭罪了。
我一咬牙,那就做吧,其實做這個手滿打滿算全下來也就三千多塊,我了一千五的押金,兜裡就剩兩百塊錢了。
許金被推薦手室的時候我一直笑著鼓勵:“沒事!我在外面等你,一會兒就好了啊!”
等手室門一關上,我就鬧心了,我的三千塊在這裡不到一星期就快花沒了,而且現在還缺最一千五,我坐在手室門口撓抓耳撓腮,,還是忍不住給姥爺去了一個電話,自從那天我坐天給他打電話他沒接之後,事一個接一個,我也沒再打,一想到自己這麼給姥爺打電話是爲了要錢,總覺得有些丟人還有過意不去。
我想好了,姥爺要是沒在屋不接就罷了,我就自己再想想別的辦法。
“喂,龍啊。”
接了。
我心裡一:“恩,姥爺,你幹嘛呢。”
“哎呀,這兩天鬧騰啊,你可算是去市裡了,你爸爸的廠子出事兒了,著火了,還把兩個工人燒壞了,現在人家屬天天上門來要錢啊,一張就要二十多萬,我看著都跟著著急啊,這一的大泡啊!”
我一聽就了,站起:“姥爺,那他們沒做什麼過激的事吧,工廠怎麼還會起火啊,找到原因了嗎。”
“正在查呢,你放心,他們不進屋,就是天天在外面喊,還說要找電視臺,就爲了跟你爸要錢,你爸要把車賣了,好像還不夠,這今天把你小姑父也找回來了,放心吧,你小姑父到時候能幫忙啊,你就在那邊還好的,別擔心家啊。”
“恩。”我心裡一沉,要錢的話打死也說不出口了。
“我聽你咋不開心呢,是不是在那待得不好啊。”
“好。”我笑了笑:“大丫也過來了呢,我們倆還能做個伴兒,我就是擔心你,你要注意啊,我爸的事你別跟著心,什麼難關都會過去的。”我是人:
“那就好,先不說了,電話費也貴,你錢夠花吧,不夠跟姥爺吱聲啊。”
“夠。”我笑著應著,看著許金還在手中的紅燈:“姥爺,我這邊兒要去吃飯了,到時候再給你打過去啊。”
“哎,好,多吃點飯啊,別挑食。”
“我知道。”
掛下,我嘆了一口氣,小姑父也回去了,這錢怎麼辦啊,想著,我翻著通訊錄裡僅有的兩個人,找到程白澤的電話撥了過去,醞釀了半天,尋思怎麼開這口借錢,結果,他沒接。
我開始坐不住了,許金得住差不多一個星期的醫院,所有的費用都得在出院時補?,也就是說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想著,我看向旁經過的護士:“你好,我想問一下,人才市場你知道在哪裡嗎?或者說,哪裡有找臨時工的活?”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