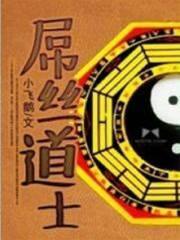《亡人孀》 第三百三十三章 鬼眼先生的打算
只注視著眼前的蠅頭小利的人,才是真正目短淺的傻瓜。鬼眼先生自北境之戰名,到現在已經有一千年,抗過了天衰,抗過了天人五災,以幾乎永生的姿態生活在司酆都旁的藏山小院上,本來過的愜意。
可偏生有人看不得清凈。或者說,是天道不與他清凈。因果樹之死,只有極數人知道,不巧,鬼眼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詐死離開了獨孤琴和獨孤淵之間的爭奪,可到底還是得回來一趟,看個究竟。
馮二端著一盤冒著熱氣的打鹵面,一臉殷勤地端了過來。西紅柿丁噴香,跟潔白的面條糾纏在一起,上頭撒了把碧綠的香菜,端的是香味俱全。
鬼眼先生一雙赤紅的眼眸贊許地看了過去,,大方地闊綽出手,拍了兩張錢。
這樣的飯食,在世間并不稀奇。可到了司,就是最稀奇的吃食,只有在嘉陵這樣的走私販子開的店中,或許才能嘗上兩口新鮮的飯食。
馮二拿了錢,放了串鑰匙,說了房間名,機靈地回告退。鬼眼先生拿了雙筷子,有滋有味地吸溜著噴香的面條,連臉上的霾都似乎散去了一些。
吃完面條,鬼眼先生心中也布好了局,謀劃好了章程。不不慢地起,吩咐馮二給他的熱水溫著,竟然直接又戴上了兜帽,轉迎著暗的幽靜走了出去,又朝著酆都的方向而去。
馮二見多了奇奇怪怪的人,早就習慣了只按吩咐行事,不該看的不多看,不該問的也不多問。可這個人……
馮二想起一雙赤紅的鬼眼,不自地打了個寒,決定伺候好這位爺,同時把一切東西都攔在自個兒的肚子里頭去。不是什麼人都有福氣消得住這幾張錢,他馮二已是命大。
Advertisement
酆都作為司的十座主城之首,鎮守著獨孤家族和諸多鬼差勾魂,在一片黑暗中,街道都撐起了點點的燈火,街上依舊有來來去去的鬼,一直保持著笙歌繁喧,何不盡歡。鬼眼先生踏著幽暗的與玄妙的步伐,神不知鬼不覺就閃進了查腰牌的大門,直直地往一個方向走去。
他在酆都住了千年,雖然沒怎麼挪過窩,卻對酆都也是極為悉。
今日開鬼市,有個人往常不會隨意出來,可今日必定會出來。
逢五逢時開市,街上的鬼便要多一些,竟然還帶了些世間的煙火氣息。能在酆都長住的,都是已經不在乎前塵往事,又不愿去投胎了的鬼。他們要麼修了鬼道,要麼就做些小生意,酆都倒也算得上是繁華。
鬼眼先生的兜帽遮住了眼睛,不不慢地朝酆都的另一側走去。
他邊始終懸掛著一盞跟螢火蟲似的小燈,照亮著前面的路,就算黑暗并不能遮蓋住鬼眼先生的眼睛,也不妨礙他視。可到底是為人類喜的習,這麼些年,鬼眼先生還是改不過來,周一定要有一盞燈。
唯一一次全然的黑暗,就是在獨孤琴上山來尋他的時候。
鬼眼先生漸漸走到了酆都城郊,一片枯萎的朽木的土地旁。鬼眼先生摘下了兜帽,略一思索,鼻子一,出一個悵然的笑容出來。
他出手來,連手也是屬于讀書人的手。
瘦削而蒼白,指腹卻帶著一層薄薄的繭子。
鬼眼先生極快地打出幾道法印,不多時,平地之中,忽然出現了一扇門。
自己欠的賬,果真還是要自己來算……鬼眼先生嘆了口氣,手推開了門。
滿鼻茉莉芬芳。幾乎是一瞬間,一柄雪亮的劍就架到了鬼眼先生的脖子上,一個詫異的聲音遠遠傳來。
Advertisement
“鬼眼先生……?”對方顯然也很驚訝。
“獨孤公子,別來無恙。”鬼眼先生含笑,出一手指頭來,慢條斯理地推開了一個死侍架在他脖子上的劍鋒,面不變,含著笑,剛要手跟面蒼白的獨孤淵打個招呼,只是向著端坐在離他不遠的院子下的一張藤椅上的獨孤淵出的手……卻帶著掌力和暗勁!
只是,鬼眼先的這一掌剛剛出,就被一人半途沖出來攔下。
鬼眼先生掌勁一泄,腳下向后開兩丈,停下后向攔他那人看去,獨孤淵前擋著剛才那個為了不傷及他命,沉默地收回了劍的死侍,鬼眼先生剛剛一掌,如無意外就會拍到這死侍腦門上——他特地為獨孤淵準備的一掌!可偏偏這死侍力量運用的也極為巧妙,鬼力吞吐間卸去了鬼眼先生那一道暗勁,臉被黑霧包裹住,看不出神來。
只不過,僅此一手,孤前來的鬼眼先生就不得不在心中暗暗贊上一聲。單論邊的護衛,這個死侍也要甩了獨孤琴邊的那呼延的修羅族王子不知多。
“紀。”獨孤淵淡淡開了口,卻示意紀放下指著鬼眼先生的劍,分明他如今依舊痛徹心扉的傷口是由鬼眼先生造,可如今他言語之間卻是對鬼眼先生的維護。
“鬼眼先生與我沒有大仇,先生是中人,不必如此。”
紀沉默著放下了劍。
獨孤淵坐在藤椅上,手中還抱著一個茶杯,看著神平淡自若的鬼眼先生的臉,微微一笑,笑的客氣而又疏離:“來者是客,座。”
言談間,竟然完全沒有跟鬼眼先生算賬的意思。
鬼眼先生近距離地打量著獨孤淵,都是蒼白而俊俏的年輕人的相貌,只不過鬼眼先生的目犀利,獨孤淵卻依舊帶著沉定冷凝端坐自若的氣勢。
Advertisement
“此行唯吾一人,生死有命。”鬼眼先生收回了目,昂首站著,微微一笑:“我來,與你賭一場。”
藏山小院上發生過的事,這兩個聰明人中的聰明人都沒有再提,因為彼此也都知道,是在做戲。
即便獨孤淵心口的傷口還在作痛,即便鬼眼先生古井無波臉下藏著還未發的氣勢。可獨孤淵知道,鬼眼先生既然膽敢孤前來,談笑自若,他就一定有能全而退的本事和手。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