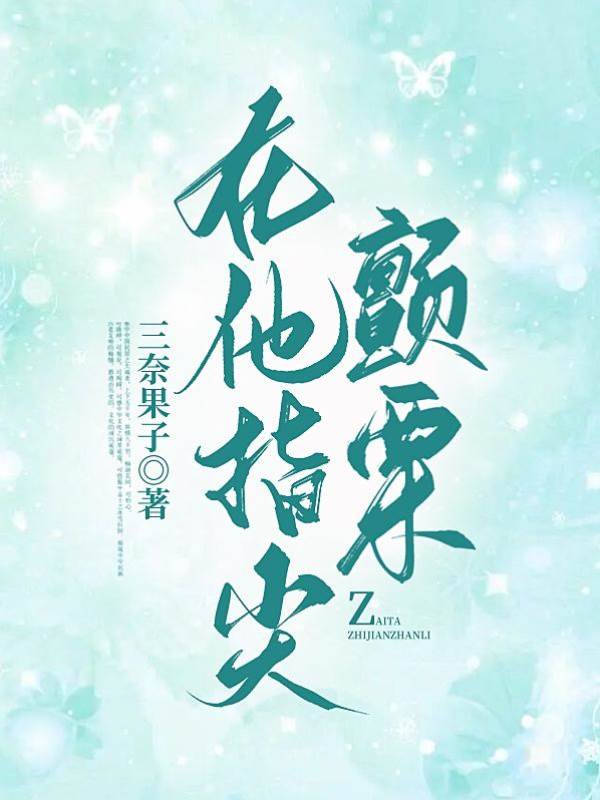《月光似你溫柔》 第48章:顧夕顏,你就是個白癡
顧夕從頂樓上下來的時候,整個人都魂不守舍的,一個人,一生的幸福就那樣被毀了,的心里,哽得有點難。
盡管不是親手毀滅的,可卻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就像是閔敏說的,是害了。
安永心看見顧夕下來,立即沖了上去,抱著顧夕看有沒有傷,馬上,就看見了顧夕的腳踝紅腫的厲害,怒了起來,“閔敏,你這個賤人,居然敢打我家夕。”
“沒有。”顧夕急忙去拉著安永心,不讓罵閔敏。
“還說沒有,你的腳都腫了這樣,你不要怕,我給你報仇。”
“是我自己弄的。”顧夕搖了搖頭,揪著安永心的手,拉著,“安永心,我想走了,我想回家,你陪我回去好不好,我一個人好害怕。”
不敢面對閔敏了,從沒想過,會有那種遭遇,在穿著婚紗要嫁給裴宣的時候,會被人抓著,溜溜的關在籠子里,像貨一樣被人打量。
不敢想,要是裴宣沒有及時趕到的話,閔敏的下場會是怎麼樣的。
如果說,的幸福是要另外一個人用自己一輩子沉淪在痛苦之中來換的話,寧愿不要那個幸福。
“顧夕。”安永心不懂,“你怎麼了?你怎麼能繳械投降了呢?明明你才是正室,明明你才是裴夫人,你怎麼能讓一個小三的這麼狼狽的離開呢?”
“我沒有狼狽,安永心……我只是不想在爭了,真的,我不裴宣了,一點都不他了,現在我看到他就想要躲他,生怕他繼續纏著我了,所以我要把他讓給閔敏,讓他以后都不要在纏著我了。”顧夕紅著眼睛,好難過,“安永心,你其實不知道,我是有多壞……我早就知道裴宣和閔敏兩個人是真心相的,可我就是橫一腳,把裴宣從閔敏的邊搶了過來,讓他們兩個相而不得。”
Advertisement
“可我呢,我什麼都沒有得到,一個人守著孤零零的房子過了五年……一個人的任,讓三個人都痛苦,永心,你說,我是有多壞!”
安永心越聽越生氣,閔敏這是給夕灌的什麼迷魂湯,竟然讓這麼快就繳械投降了,可當事人都投降了,此時再說都沒什麼用了。
陳母聽著,就說了起來,“顧夕,你既然知道是因為你當年的任導致三個人都痛苦,現在你就應該知道你不應該再出現在裴宣的面前,要是沒有你,裴宣今天也不會傷躺在病床上。”
安永心罵了起來,“你胡說,明明是你們家閔敏不要臉,知道我家夕和裴宣結婚了繼續纏著他,說什麼真、什麼相在前,還不是小三一個。”
“別說了,別說了……求求你,不要再說了,這是我和們之間的事,你就不要再手了。”
滾燙的小手拉著安永心,祈求不要在說下去了。
安永心要氣瘋了,“我在幫你啊,顧夕,你的腦子到底是怎麼長的,我幫你你不幫我也就算了,還在這里扯我后,該不會是你被蔡俊打腦殘了吧!”
“沒有……沒有……永心,我只是不想再繼續下去了,這一切都是我的錯,是我任、是我不顧一切的纏著他,要是沒有我的話,他們早就幸福了。”顧夕彎,說了起來,“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你就不要再繼續下去了,帶著我離開醫院吧,我的腳好疼。”
“腳疼就去看醫生,這里有我呢,我就不信我還打不倒一個小三。”
“永心,我的腳真的好疼,你扶我走吧,沒有你,我走不了路。”
拉著安永心的手,倉皇的走,好害怕面對閔敏,一想到自己害得閔敏差點被當做貨賣掉,的心就好哽。
Advertisement
走出醫院的大門,顧夕就像失去了所有的力氣一樣,坐在花壇邊上的柵椅上,掀開,才發現自己的腳踝已經青紫一片了。
“夕,你的腳怎麼這樣了,我去給你拿藥。”
“別去,永心。”顧夕住了安永心,不讓去醫院,“我的腳沒事,就是有點點疼,等下我自己回去上藥就好了,我家里有云南白藥,它對扭傷很有效。”
“還有,謝謝你這麼幫我。”
“我就是看不慣們那副樣子。”提起們,安永心就氣了起來,“小三就要有小三的樣子,我的姐妹們雖然想著攀龍附,可沒有誰會到正室面前搞事,偏生們不一樣,在你這個正室面前搞事,搞得自己很有理一樣。”
“小三們的名聲都被們搞壞了。”
顧夕沒有說話,只是了腳踝,安靜的看著遠,“永心,你為什麼那麼執著去找那些豪門子弟,他們其實,沒有你想象的那麼好。”
在顧家還沒有破產的時候,顧夕見過很多豪門子弟,他們玩車玩人,表現得風度翩翩,可里,誰也不知道做過什麼壞事、有過什麼齷齪。
只有裴宣是不一樣的,他和別的豪門子弟不一樣,他溫儒雅,又有能力,靠著自己的一雙手,打下了一個偌大的AR集團,這大約也是為什麼會在那麼多豪門子弟中,一眼相中裴宣了吧。
“我知道,如果可以,我也不想去做,可顧夕,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你那樣順心如意的。”安永心眺遠,“有時候,生活中的許多事,都會著你去做一些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在顧夕和安永心談話的時候,蔡俊提著袋子從醫院里追了出來,在里面的時候他就看見了顧夕的腳踝傷的厲害,可偏生不是省心的,都意識不到自己的腳疼,沒有去看醫生的想法,他只能自己急忙去找醫生,要了好幾種治療扭傷的藥。
Advertisement
在發現顧夕之后,他二話沒說,直接沖了上來,摁住的腳,把藥一腦的全拿了出來,劈頭蓋臉的罵了起來,“顧夕,你是個白癡嗎?自己都傷了還不知道去看醫生,你以為自己的腳是鐵打的不會斷掉?”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300 章

穿成大佬的反派小嬌妻
醜到不行的沈從容穿書了。穿成膚白貌美,身嬌體軟,一心隻想給老公戴綠帽子的富家小明星。每天想著要蹭熱度,捆綁上位的娛樂圈毒瘤。全娛樂圈都知道沈從容矯揉造作,最愛艸小白花人設直到某個視訊上了熱搜……眾人眼中的小白花徒手乾翻五個大漢。網友狂呼:妹妹!你崩人設啦!當晚,癱在床上的沈從容扶腰抗議:「人家體弱,你就不能心疼心疼?」薄翊挑眉,摸出手機開啟視訊:「體弱?」沈從容:嚶嚶嚶……她要找拍視訊的人單挑!
186.5萬字8 14320 -
完結1181 章

分手后,她藏起孕肚繼承億萬家產
葉芷萌當了五年替身,她藏起鋒芒,裝得溫柔乖順,極盡所能的滿足厲行淵所有的需求,卻不被珍惜。直到,厲行淵和財閥千金聯姻的消息傳來。乖順替身不演了,光速甩了渣男,藏起孕肚跑路。五年後,她搖身一變,成了千億財…
205.2萬字8.18 79263 -
完結357 章

心聲暴露後,瘋批千金作成小心肝
【穿書 讀心術 吃瓜 沙雕 1v1】溫顏穿書了,穿成為了男主,竊取聯姻老公司墨衍文件機密、惡毒又作死的女配。她還綁定了一個吃瓜且讓她做任務的係統,她需要獲取司墨衍100好感值,才能活命。不近女色、且早就對她厭惡至極的司墨衍,直接提出離婚。“老公,我們不離婚,以後我隻愛你好不好?”【公司被搶,腰子被噶,要不是為了活命,我才不想撩你這個短命鬼呢!】“大哥,你別被這個女人蠱惑,我支持你跟她離婚。”她掃了眼司墨衍當導演的二弟。【戀愛腦,綠帽龜,難怪最後人財兩空,還被送去非洲挖煤,最後慘死在異國他鄉。】“大哥,這個女人就是個禍害!”她掃了眼司墨衍當翻譯官的三弟。【被人陷害,頂罪入獄,最終病毒感染折磨至死,慘。】司家小妹瑟瑟發抖:“大哥,其實我覺得大嫂挺好的。”大嫂的心聲,應該不會詛咒她了吧!【小姑子人還怪好嘞,隻可惜遇到渣男,流產四五次,家暴還出軌,最後買巨額保險將她——】溫顏隻想盡快完成任務走人,哪知司家人都能聽到她心聲,還跟著她一起吃瓜。最終炮灰命運得到改變,她也完成任務。她拍拍屁股走人,冰山老公將她抵至牆角:“誰讓你撩完就跑的?”“你不是要跟我離婚嗎?”
70.6萬字7.82 16658 -
完結10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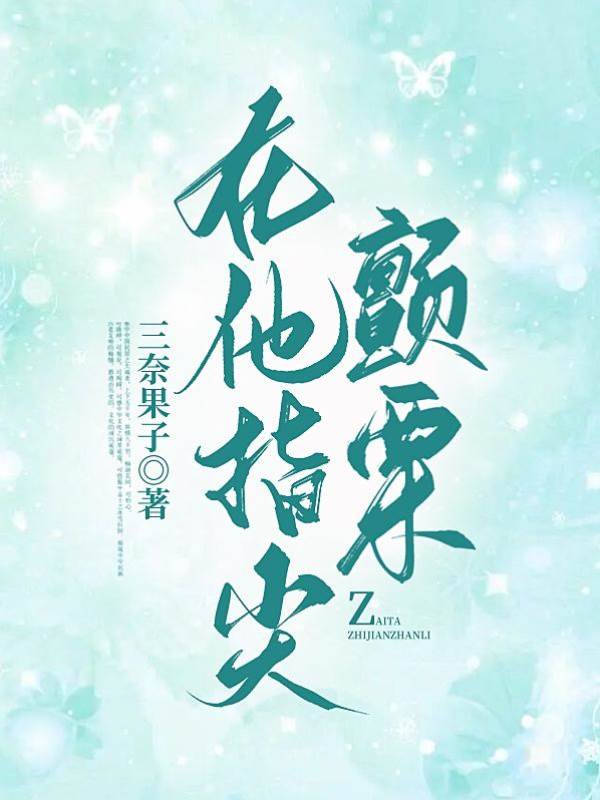
在他指尖顫栗
【美豔釣係旗袍美人VS清冷矜貴貧困大學生】【欲撩?甜寵?破鏡重圓?雙潔?暗戀?豪門世家】他們的開始,源於荷爾蒙與腎上腺素的激烈碰撞她看上他的臉,他需要她的錢他們之間,隻是一場各取所需的交易蘇漾初見沈遇舟,是在京大開學典禮上,他作為學生代表正發表講話他一身白衫長褲、目若朗星、氣質清雅絕塵,似高山白雪,無人撼動驚鴻一瞥,她徹底淪陷人人說他是禁欲的高嶺之花,至今無人能摘下可蘇漾不信邪,費盡心思撩他,用他領帶跟他玩緊纏遊戲“沈會長,能跟你做個朋友嗎?”“蘇漾,”沈遇舟扣住她亂動的手,“你到底想幹什麽?”“想跟你談戀愛,更想跟你……”女人吻他泛紅的耳朵,“睡、覺。”都說京大學生會主席沈遇舟,性子清心冷欲,猶如天上月可這輪天上月,卻甘願淪為蘇漾的裙下之臣然而蘇漾卻突然消失了多年後,他成為醫學界的傳奇。再見到她時,他目光冷然:“蘇漾,你還知道回來?”房門落鎖,男人扯掉領帶,摘下腕表“不是喜歡跟我玩嗎?”他親吻她,偏執且病態,“再跟我玩一次。”“沈遇舟,對不起。”男人所有不甘和怨恨,在這一刻,潰不成軍他拉住她,眼眶發紅,眼裏盡是卑微:“別走……”沈遇舟明白,他是被困在蘇漾掌中囚徒,無法逃離,也甘之如飴
20.8萬字8 2982 -
完結93 章

錯加老板微信后
林淺聊了一個虛擬男友,每天對他口嗨浪到飛起,享受着調戲的快樂。 【在嗎,看看腹肌】 【我們之間有什麼事不能躺你身邊說嗎?】 【你嘴這麼硬,讓我親親就軟了】 但他續費太貴了,一個月期滿後,他答應了做她男朋友,攻略成功的林淺忍痛刪了他。 可下一秒,公司大群裏,那個冷肅嚴苛人人懼怕的總裁幕承亦,在衆目睽睽下@了她。 【@林淺,給我加回來】 林淺:……! — 林淺後知後覺自己當初加錯了微信,這一個月撩的一直都是她恐懼的大老闆慕承亦。 人怎麼可以捅這麼大的簍子? 她好不容易鼓起勇氣跟他說實話,卻被他“約法三章”了。 慕承亦:“雖然我同意做你男朋友,但我沒有時間陪你吃飯,你也不可以要求我陪你逛街,更不準強迫我跟你發生親密關係。” 林淺:…… 慕承亦:“但作爲補償,我給你幾家米其林餐廳的儲值卡和SKP購物卡,每失約一次就分別往裏面打10萬。” 林淺:我願意! 其實這個戀愛您本人沒必要親自到場談的! 每天沉醉於紙醉金迷快樂中的林淺,爲了不露餡,只能硬着頭皮繼續撩。 幾天後卻發現自己被騙了,他根本沒失約過幾次! 下班不管多晚都要跟她一起吃飯; 下暴雨也要陪她逛街; 每天還把她按在辦公室的門上親! 一次酒後,她沒抵住他的美色,佔了他的便宜。 第二天晚上,想死遁逃走的林淺被攔腰抗回了牀上,高大身影欺壓而下,調出她手機裏的虛擬男友購買記錄,聲音沉暮透着寒氣。 “說說看,哪個是你買的虛擬男友?” 林淺:“……你。”
23.3萬字8.18 1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