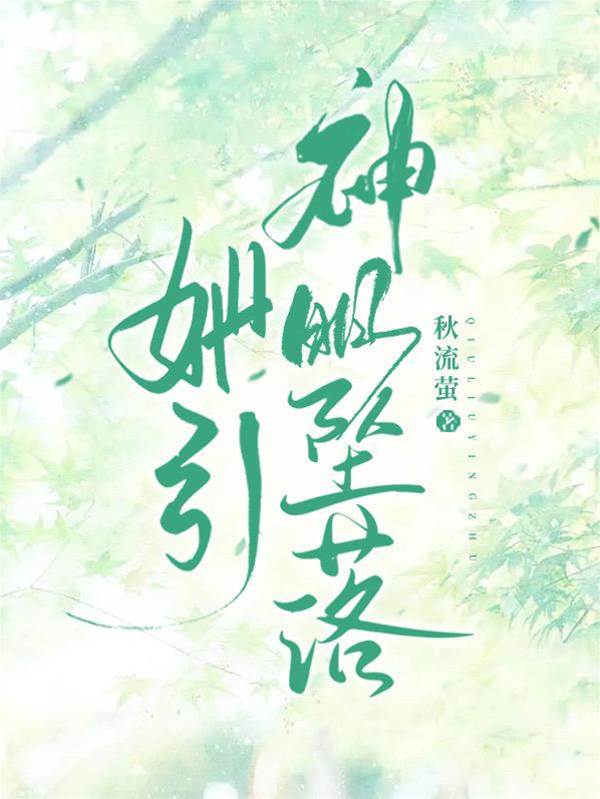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替罪情人:我曾愛你比恨深》 第六十四章 我要她啊
蘇澈應聲看去,姑姑手中照片上展示的是一條紅寶石項鏈,簡單的鑲嵌工藝,除卻凈度澤顯鮮亮外看不出有何特別之。略略疑的向姑姑,“這是哪里來的?”
“這話我問你啊,照片上的項鏈在哪里?上次我去你家找過,沒有找到,肯定是你藏起來了。”
原來自己剛回家時虛掩的鐵門和里被翻得七八糟全都是眼前這個所謂親人做的,蘇澈心下升起幾許厭惡,皺眉道:“既然如你所說是我藏起來了,那麼現在又怎麼能指我拿出來給你?”
實際上,蘇澈本沒有見過照片上這條項鏈。父母出事的時候不過14歲,完全沒心思也沒可能關注母親的首飾這種細節。
蘇澈的回應是姑姑從沒有想到過的,怔了半晌才回神過來,免不了又是指天咒地的一番痛罵。面對不講道理的責難蘇澈慣常的安靜沉默,可后的安慕希卻不是那種逆來順的子,撥開蘇澈的手憤憤上前。
“天拿著下三路顯擺自以為技高一籌,娘來賤去的罵人敢你是特別有優越了還,是沒這些還是不用配能自繁有分裂啊?孫大圣都沒你自信,你簡直就是宇宙起源,盤古開天。真是可惜舞臺不夠大,要不我給你找顆白菜?”
一席話不帶氣的說完,蘇澈姑姑臉都掛不住了,跳著腳又要破口大罵。
安慕希隨即甩了個白眼過去,跟著接道:“說你胖還上了,這是現場表演你的臉不要你了?沒人圍觀會不會很失落,幫你吆喝捧個人場好不好?”
今年20出頭,自詡這輩子的技能點都點在了上。大一就加了校辯論團,不過個把月就榮升為正式一辯手,了們大臨床新生之。不過平素面對的都是正經辯論,基本沒遇到過蘇澈姑姑這種中老年婦的潑婦式罵街。
Advertisement
雖沒有經驗,但安慕希腦子轉得快,采取了迫盯人戰。開口就開口,閉就閉。蘇澈姑姑其實不太聽得明白不帶臟字的回擊,只是語速沒快,氣勢沒強。每每開口就被堵回去,往返幾次氣的渾發抖,終是忍不住要行使暴力,“賤丫頭,你家大人沒教你說話懂禮,我來教你。”
“你沒有這個資格。”這一掌并沒能夠落下去,被蘇澈攔住了。
迎著蘇澈沉郁的,姑姑心下一凜,莫名心虛的避開了視線。跟著松開了的手,轉自往前走去。
“蘇澈!”后,那中年婦人見狀忙忙將喚住,滿眼哀傷,“治你妹妹的傷要很多錢,還沒有社保,全部都是自費,我和你姑父也是沒辦法撐下去了。”
聽到吳茗瑜的況,蘇澈腳下微滯。在自己都拋棄自己的那些黑暗年月里,是吳茗瑜一封封沒有時效的信件給了親人間的關,陪著熬過了那1000多個日夜。乃至遇上這場火災也是因為小表妹要幫慶祝,于于理,蘇澈在這件事上都難辭其咎。
于是沉了片刻,終是不忍道:“項鏈我是真的沒有見過,錢的話……”
聽出蘇澈又要圣母心,安慕希張開雙臂沖過去將護在后,“呸呸呸,要錢沒有要命一條。”
蘇澈姑姑眼見有了轉機心下正自竊喜,不防安慕希這個程咬金又躥了出來。因為那條項鏈的事顧忌蘇澈不敢太過分,瞪了安慕希一眼沒好氣道:“這是我們的家事。”
“說得好聽,家事。捫心自問,你有把當過家人嗎?”安慕希自小儒家典籍熏陶,知道以德報怨的下一句是以直抱怨,并力行。
Advertisement
眼見姑姑的臉孔漲了豬肝,蘇澈再次搶白開口道:“我過兩天會打兩萬塊到茗茗賬戶上,暫時就只有這麼多了。”
說完,再沒管,扯著安慕希那匹韁野馬徑自走了。這丫頭還各種不樂意,恨鐵不鋼的叨叨:“蘇姐,你知道你那姑姑說的真假啊?還沒錢,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爸媽那時候留了多錢下來你還聽瞎忽悠。”
“樂樂。”蘇澈突然停下腳步輕喚的小名,安慕希怔了怔,“啊?”
邊掛了抹笑意,想到方才的場景就有些忍俊不,“我今天學到了一課,原來罵人還能這麼晦的,要不要送顆白菜給。”
“這個嘛,其實和這種老阿姨對峙真的是很沒就,恐怕本聽不懂。”話雖這麼說,但安慕希整個人表現的就是得瑟二字。
“可是你還是把氣得話都說不出來了。”蘇澈依舊眼眸含笑。
“那是能力太差,不管辯論還是打仗首先不能被人帶了節奏,這是兵家大忌。”說到這里,安慕希突然話鋒一轉,“我看你就不要想忽悠我了,過兩天又要給別人送溫暖兩萬,也不考慮下自己還剩多了。對了上回你讓我打三千還曹姐,說只借了你兩千。一個禮拜翻一半,這高利貸真好賺。”
蘇澈垂了眸,“只要等到孩子生下來,我會繼續找工作的。”
“我覺得你已經是圣母癌晚期骨,沒得救了。”看了好半天,安慕希無奈的嘆了口氣。
蘇澈走了幾步,扭頭道:“可你是將來的醫生啊,不應該想辦法救死扶傷嗎?”
面對的調侃,安慕希頗意外的挑了挑眉,“不,我沒有這個能力。”
Advertisement
伴著滿街霓虹影,兩人緩緩往回走。有一搭沒一搭的廢話,恍惚間似乎將時轉回了十多年前,還是不識愁滋味的年時期。夏日午后看見的不是父親那淌滿了的菜刀,也沒有母親冰冷的尸。
半夜蘇澈自床上坐起,因為小肚筋疼醒。本想扶著墻壁站起來緩解疼痛,不過卻因腳下無力跌倒,還帶翻了床邊矮柜上的臺燈。隔壁房間的安慕希被驚醒,忙忙開門進來,看到臉慘白跌坐在地上忙忙過來攙扶。因為這一跤見了紅,當即要送醫院。
因為在市院見習,安慕希還是決定將帶到市院。在急診門口意外撞見值夜的鄭文揚,看著蘇澈臉慘白也心知不妙,二話不說上來抱了蘇澈就往急診中心走。連掛號都省了,一路刷臉卡走后門。
檢報告出來,超聲波檢查完結,醫生判定有先兆流產的癥狀,需要辦理住院手續。安慕希就被打發去辦住院,蘇澈則在鄭文揚一路護送下先行安穩躺在了病床上。
“孕13周,孩子發育迅速,母親要加強補鈣和各種營養,怎麼你不知道買本育嬰書的嗎?”他在護士臺那邊要了杯水在旁邊坐下,一臉肅穆遞了給。
“對不起。”垂了眸接過水,臉上泛熱。
確實并沒有想過去買本書之類的,因為安慕希拍著脯說自己能照顧。
此時那丫頭打著噴嚏進來了,鄭文揚扭頭看了一眼,嫌棄道:“你冒打噴嚏怎麼還進來?趕出去,一會傳染到蘇澈怎麼辦?”
“哦,好的。我馬上就出去。”安慕希將手中繳費單據放在了蘇澈床腳,轉自踏出病房。走了兩步,后知后覺轉回去,“我沒有冒啊。”
“打噴嚏就是快了,難不你打噴嚏還是有人想你啊?”
“對啊,我媽想我,我爸想我,不行嗎?單狗注孤生!”
聽著安慕希的人攻擊,鄭文揚冷笑出聲,“說的你好像有人要一樣?!”
話落,原本還垂著頭憤莫名的蘇澈跟著開了口,“對啊,我要啊!”
這下突擊嚇得鄭文揚差點被自己口水嗆死,“fuck。”
一個自然是答案比較引人遐想,另一個最重要的是,他覺到蘇澈變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4114 章
罪妻來襲:總裁很偏執
易瑾離的未婚妻車禍身亡,淩依然被判刑三年,熬過了三年最痛苦的時光,她終於重獲自由,然而,出獄後的生活比在監獄中更加難捱,易瑾離沒想放過她,他用自己的方式折磨著她,在恨意的驅使下,兩個人糾纏不清,漸漸的產生了愛意,在她放下戒備,想要接受這份愛的時候,當年車禍的真相浮出水麵,殘酷的現實摧毀了她所有的愛。
361.9萬字8 2360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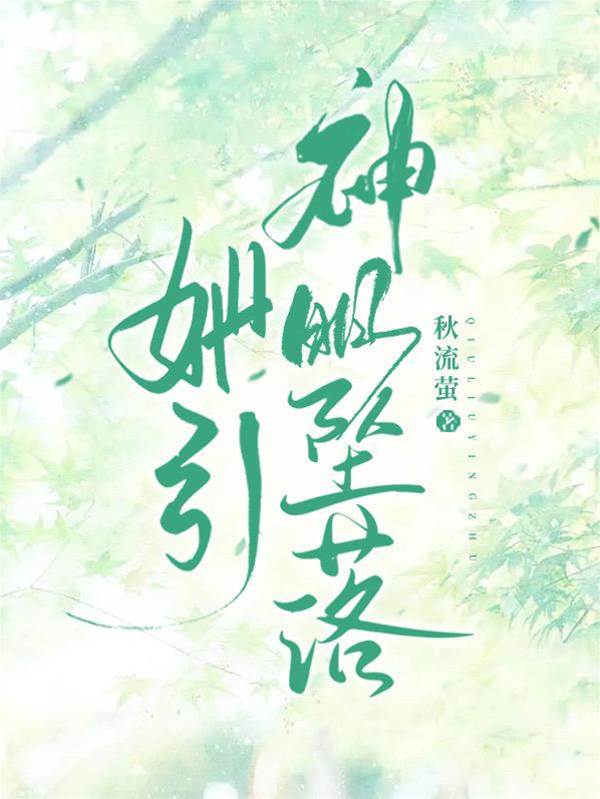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311 章

昨夜燈暖
三年前,蕭叢南被迫娶了傅燼如。人人都道,那一夜是傅燼如的手段。 於是他一氣之下遠走他鄉。傅燼如就那樣當了三年有名無實的蕭太太。 一夕鉅變,家道中落。揹負一身債務的傅燼如卻突然清醒。一廂情願的愛,低賤如野草。 在蕭叢南迴國之後。在人人都等着看她要如何巴結蕭叢南這根救命稻草的時候。 她卻乾脆利索的遞上了離婚協議書。
51.4萬字7.82 115868 -
完結120 章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小說簡介:宋家那個土里土氣又蠢又笨的真千金,忽然轉性了。變得嬌軟明艷惹人憐,回眸一笑百媚生。眾人酸溜溜:空有皮囊有啥用,不過是山里長大,
22.5萬字8.46 5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