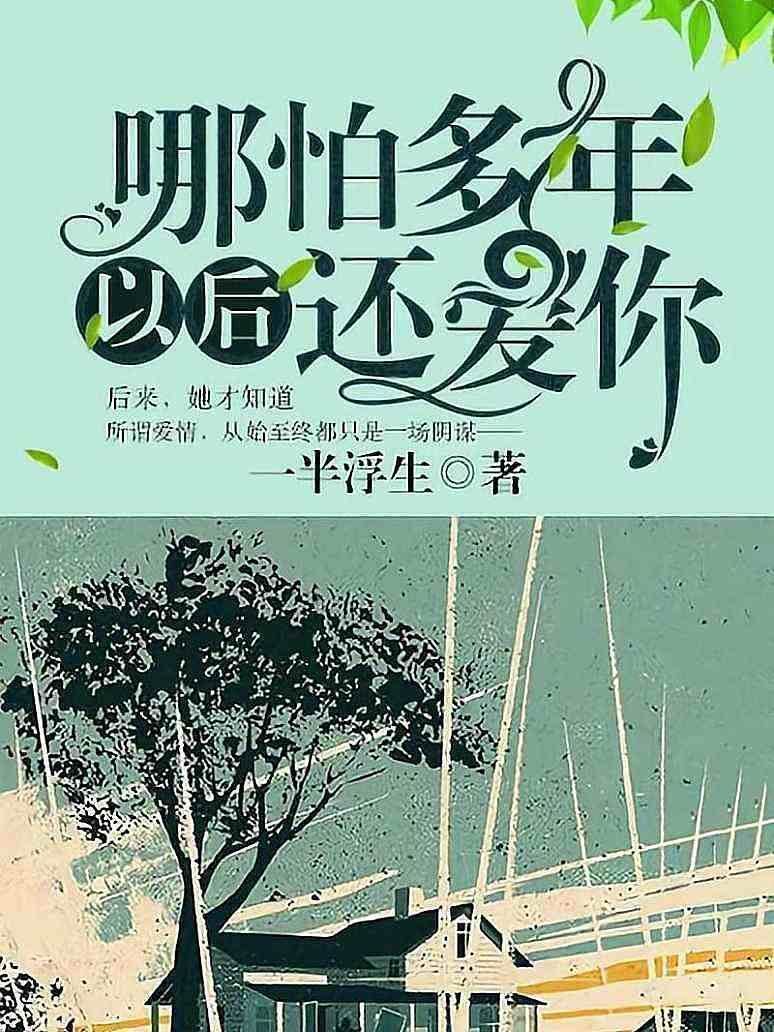《萌寶來襲:神醫媽咪美強辣》 第七百二十一章 很多年秘密
楊年便表沉沉的盯著楊禹城,臉很難看,直接質問道:“你這麼晚回來,是給那個方明慧做手去了。”
“是啊,您怎麼知道?”楊禹城意外。
這件事他好像沒告訴過楊年,而且他經常很晚回來,楊年也沒有擔心過。
“你別管我是怎麼怎麼知道的,那樣一個人,有什麼好救的。”
楊年一開始原本是想要了方明慧的命,但方明慧運氣好,當時車禍的時候出現了點小狀況,只斷了一條。
為免引起懷疑,他也沒二次出手。
原本以為人殘廢這事也算了了,哪知道林出手救治。
這違背了他的初衷,而且還讓林這麼勞累,楊年收買護士,故意讓方明慧二次傷,原本這次已定局,又冒出個方老來。
楊年也才知道,方老竟然還有這麼一門親戚,如果早知道……
“爸,就算方明慧人惡劣,但我學醫就是為了治病救人,而且治療完之后,就一切隨緣了。”
Advertisement
“愚昧。”楊年冷哼道:“如果殺了你全家的仇人傷了,你也要救麼?”
楊禹城被這話給問的愣住了。
而且他覺得今天的楊年特別怪異,一直以來,楊年給他的覺都是慈和好父親的形象,可是這次卻突然變了一個人一樣。
陌生的他不敢認。
“爸,你今天到底是怎麼了,是誰惹你生氣了麼?”
楊年頓了一下,才回神道:“沒事,只是想起了一些不痛快的往事。”
原來是這樣。
楊禹城知道楊年心底有一段難以去除的記憶,大概是今天心不好,由方明慧的事聯想到了什麼不好的回憶吧。
“爸,您不好,還是早點休息。”
“也好。”楊年也愿多說,站了起來。
但不知道是站的太久了還是不好,整個人晃悠了一下,楊禹城趕上前將人扶住,正好扶著左手。
Advertisement
袖上,出手腕上一塊難看的疤痕,糾結在一起,看起來十分恐怖。
那是燙傷,楊禹城以前也看到過,沒多想過,可是今天看見不知怎麼的就想起了方老說的那個買毒藥的人。
這麼巧都是左手?
而且這些年楊年的左手雖然看著好像沒事,但其實不能提重,一些復雜的事左手都不能做,好在是左手不是右手,還不至于影響生活。
楊禹城多看了一眼,忍不住問:“爸,你手臂上的燙傷很嚴重,是什麼時候燙傷的?”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看著手腕的傷疤,楊年眼神郁道:“我被仇家陷害,家里放了一把大火,你養母和你的妹妹就是在那場大火中沒的,我沖進去想要救們,最后這手被砸到燒傷了,后來逃出來,什麼都沒剩下。”
楊禹城心里也很難,這件事他也是知道的。
想了想道:“我姐也是皮損,是硫酸造的,您這是被火燙傷,林在這方面很厲害,您看要不要讓給您治療一下。”
Advertisement
“不用了,這傷疤我要留著,讓這傷時時刻刻提醒我,當年的仇恨。”
出人意料,楊年拒絕了。
一般人知道有機會修復的損傷,都是會答應的。
見楊禹城愣在原地,楊年道:“好了,時候不早了,你早點休息,我也睡了。”
“好的,爸。”楊禹城楞了一下回神。
楊禹城看著楊年的背影,忽然覺得自己好像沒有真的了解過這個養父,養父上有很多年。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6 章

他只對她溫柔
你已經是我心臟的一部分了,因爲借走的是糖,還回的是心。—— 宮崎駿 文案1: 請把你的心給我。—— 藍晚清 當我發現自己愛上你的時候,我已經無法自拔。 —— 溫斯琛 愛上藍晚清之前,溫斯琛清心寡欲三十年,不嗜賭,不.好.色。 愛上藍晚清之後,溫斯琛欲壑難填每一天,賭她情,好.她.色。 文案2: 在T大,提起生物系的溫教授,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姓溫,但人卻一點溫度都沒有,高冷,不近人情,拒人千里。 但因爲長得帥,還是不少美少女貪念他的美色而選修他的課,只是教訓慘烈,一到期末,哀嚎遍野。 後來,大家都明白了,溫教授?適合遠觀,不適合褻玩。 然後,學校貼吧一個帖子火了,「溫教授性子冷成這樣,做他女朋友得有多慘?」 底下附和聲一片—— 不久,學校貼吧另一個帖子也火了,「以前說心疼溫教授女朋友的人,臉疼嗎?」 底下一溜煙兒的——「疼!特碼的太疼了!」
19.7萬字8 16870 -
完結569 章

閃婚后發現老公是首富大佬
霍斯宇人帥多金,性格冷清。 本以為自己嫁了個普通人,沒想到對方竟是隱藏大佬,身家千億。 關曉萱慫了,她只想過平凡的生活。 霍斯宇將人緊緊圈在懷裡,語氣喑啞: “想跑? 你已經嫁給我了,這輩子都跑不掉! ”
62.8萬字8.09 194371 -
完結572 章

神秘愛人:總裁,晚上見
老公背著她在外養小三,婆婆竟打算讓小三代替她生子?士可殺不可辱,所以她也光榮的出軌了。只是她萬萬沒有想到,那男人竟然是她老公的…… 離婚之日,便是她訂婚之時,她簽完離婚協議,轉身嫁給了全城最有名的富二代…… 他一步步逼緊:“女人,只要寶寶不要爹,你說我要怎麼懲罰你才夠……”
98.9萬字8 85239 -
完結2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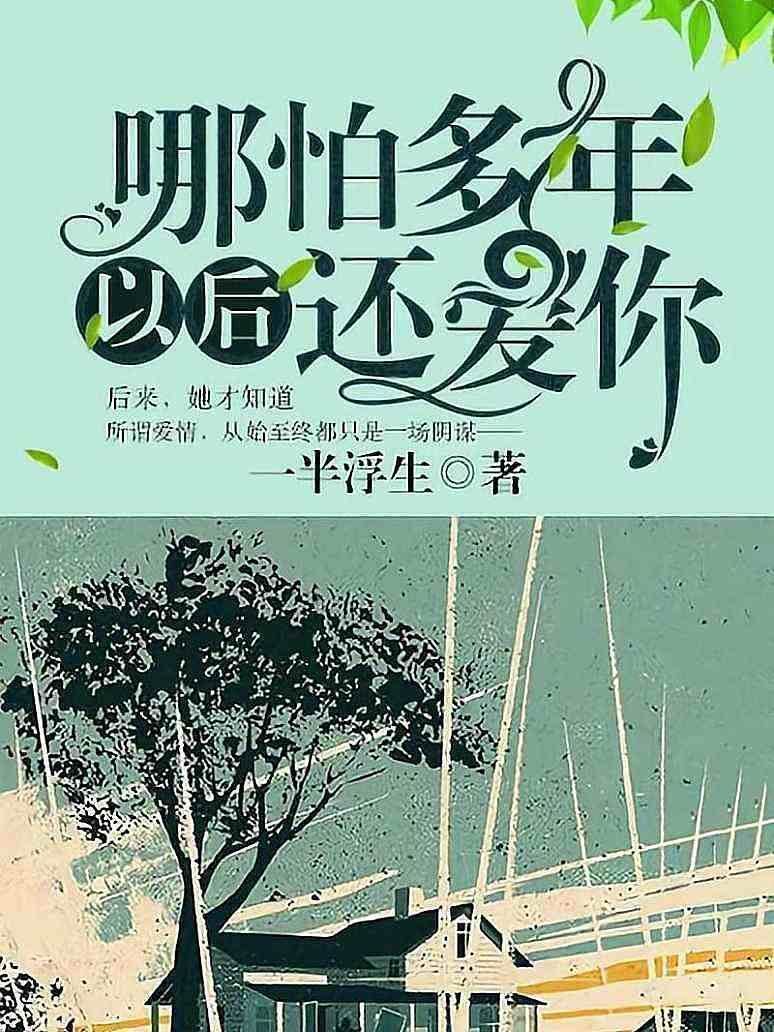
哪怕多年以后還愛你
“生意麼,和誰都是談。多少錢一次?”他點著煙漫不經心的問。 周合沒有抬頭,一本正經的說:“您救了我,我怎麼能讓您吃虧。” 他挑眉,興致盎然的看著她。 周合對上他的眼眸,誠懇的說:“以您這相貌,走哪兒都能飛上枝頭。我一窮二白,自然是不能玷污了您。” 她曾以為,他是照進她陰暗的人生里的陽光。直到最后,才知道,她所以為的愛情,從頭到尾,都只是一場陰謀。
107.8萬字8 3589 -
完結64 章

網戀到一見鐘情對象的下場
【雙男主+一見鐘情+雙向奔赴+HE】【霸總攻江野×音樂主播受宋時慕】 小透明音樂主播宋時慕是音樂學院的一名優秀大學生,直播間常年蹲守一位忠粉,次次不落地觀看直播,準時打賞高額禮物。 線下見面時,宋時慕發現這位忠粉竟然就是他在開學典禮上碰見的一見鐘情的對象~ 【小劇場:直播間高呼讓主播賣萌。 宋時慕無奈捂臉,擺手強調三連:“主播是正經人,主播不會賣萌。” 忠粉江野:“真的?那昨天晚上向我撒嬌的是誰?” 直播間內:“哇哦~”】
11.5萬字8 3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