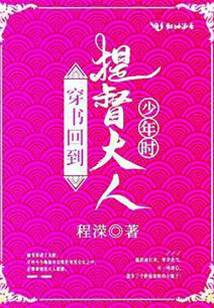《重生之嫡女不乖》 第55章
君逸之不滿地撇,“我這人最正經,最不說笑,你怎麼總是說我說笑?”
曹中睿氣得閉了,這個人不可理喻,這般時時針對我,聽說也與韓二公子不和,必定是因為無點墨,所以嫉妒我二人。
君逸之哼了一聲,背負雙手,溜溜達達沒個正形地走了過來。這種流裏流氣的走路姿勢,擱在他的上,卻是有別樣的風流倜儻的味道。兩名刺客也看直了眼,呆愣愣地看著他走到俞筱晚跟前,搖頭鄙視,“就沒見過你這樣笨的孩子,你要麼就跑快點,要麼就跟大夥兒在一起,要死也有個高的先頂著呀。你一個人跑到這來幹什麼?”
兩名刺客總算是回過了神,二話不說,舉著刀就沖了過來。之前一個孩子,他們還沒把握抓了能不能管用,這個絕的年一華麗飾,抓了他肯定管用!
俞筱晚很自覺地往君逸之後一躲,哪知君逸之卻是傻站著不,兩手揮,“快放箭!快放箭!”
俞筱晚都快氣死了,放箭,放了不會把我們兩蜂窩啊!
只得拉了君逸之轉就跑,夜間黑暗,又看不清路,腳下一空,整個人就栽了下去,還拖著君逸之也跟著一起栽了下去。
“二爺!”
“逸之!”
“晚兒!”
山坡上頓時作一團。
法源寺只是在山腳,地勢不高,這裏也不過就是片陡一點的山坡,不過也有兩三丈高,坡下有片小樹林,兩人滾到坡底,也就是傷了一點皮。
山坡上的戰役很快結束,大隊士兵高舉火把站到了坡邊,就有人要拿繩子綁在腰上跳下來,君逸之揚聲道:“無妨,準備兩頂簷子去山腳邊接我們吧。”說完問俞筱晚,“你可以走吧?”
Advertisement
俞筱晚點了點頭,秀眉卻皺一團,手掌上刺痛刺痛的,可能是什麼木刺紮了掌心。
君逸之暗暗朝天翻了個白眼,人就是麻煩。他氣氣地問,“哪裡疼就直說。”
俞筱晚搖頭,“不妨事。”堅持要走,然後想了想,又說,“謝謝你。
覺到下墜時有力道拖起了,所以並沒有撞到坡底的樹桿上,不然也得淤青一大片的。
君逸之斜眼看,“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俞筱晚眨了眨眼,沒說話。上回在潭柘寺,君逸之是用傳音同說話的,曾纏著蔣大娘,蔣大娘告訴,這得有很高深的力才行,可是剛才君逸之在山坡上時,表現得好象沒什麼武功,花拳繡的樣子……或許他有什麼原因要瞞,也無意去拆穿。
君逸之的眼睛不著痕跡地上上下下打量了幾圈,終於在半掩的袖,發現一些樹皮的痕,可能是手掌了傷。他從懷裏掏出火摺子,燃起來,魯地一把抓起的手,翻看了一下,撇了撇道:“幾木刺而已,我還以為多重的傷呢。”
俞筱晚面對他就是有些沉不住氣,這人說話太招人恨了,用力手,“我又沒說我傷了。”
“別。拿著。”他將火摺子往另一隻手中一遞,從頭上拔下束發的玉簪,用簪尖去挑木刺,裏還要嚇唬,“別,挑疼了可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瞧他的作似乎很魯的樣子,俞筱晚眼睛就半瞇了起來,牙齒也咬了,免得自己經不住疼,出聲來。可是落在掌心的簪尖卻很輕,大刺很快挑掉了,再一點一點地挑出深中的小木刺。
俞筱晚被他突如其來的溫弄得一愣,抬眸朝他看去。他半低著頭,長而卷翹的睫下垂著,在俊上投出扇形的影,臥蠶眉漆黑漆黑的,襯在白玉般的面孔上,說不出的好看,火在他如玉般散發著澤的臉上跳,或明或暗,總是道不盡的風華絕世。
Advertisement
他似乎發現在看他,唰地一下抬起頭來,亮晶晶的目就這樣盯著,“千萬不要迷上我,我的紅知己太多了,有點顧不過來。”
俞筱晚連忙低頭,臉上一陣發燒。這傢夥,怎麼什麼事都做得這麼理直氣壯,這種話也好意思說出口。
君逸之得意地複又垂下頭,仔細幫挑完了木刺,用指腹在掌心輕輕了,確認沒有網之魚,這才放開的手,一邊束發一邊揚起得意的面孔,“一點小事都幹不好,沒見過你這麼笨的人。”
這傢夥!俞筱晚前一刻才因他的指腹而,後一刻就立起了眉
君逸之已經在前面引路了,裏還要嘀咕,“真是倒楣,遇到你就沒好事。”
俞筱晚做了幾次深呼吸,不氣不氣,沒必要跟他計較。
等氣消了,謝的話也忘記說了。
兩人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前走,看山近,行路遠,這山坡底下走到山腳,也有幾裏地。冬夜黑得特別,手不見五指,只有一小團火折發出的昏黃的線,俞筱晚勉力舉高一點,免得走在前面的君逸之看不見路。
君逸之不耐煩地道:“你照好你自己腳下的路就了,仔細看我走的,跟著我的步子走。”
“哦。”俞筱晚也知道山路上有不坑,便仔細看著他的腳步,踩著他的腳印走。
君逸之回頭看了一眼,這才表示滿意,“就是嘛,笨一點就得聽話。”
去死!
俞筱晚朝他的背大翻白眼。
君逸之得意地哼哼,“我背上沒長眼睛,你翻白眼我也看不見。”
俞筱晚啞了,憋了半晌氣,忽然又覺得好笑,就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來。的笑聲跟銀鈴似的,清脆悅耳,君逸之也不勾起了笑,“笨蛋。”
Advertisement
俞筱晚被罵得有點悻悻的,“你怎麼知道我在翻白眼?”
“因為如果有人這樣對我說話的話,我肯定是會翻白眼的。”
俞筱晚又噗嗤笑了。兩人之間的氣氛莫名其妙就和諧了,俞筱晚也想起了道謝,“多謝你啊。”
君逸之不能再象之前那樣嗆,倒不好應對了,只“嗯”了一聲。
忽地又想到來時的事,俞筱晚便問,“其實你心腸不錯啊,你為什麼不扶一下貞表姐?”
君逸之的聲音立時冷了,“我討厭被人算計!”
俞筱晚一怔,是啊,若他扶了貞表姐,大道邊上,男擁抱,雖說貞表姐是庶出,但到底是家千金,他必須給貞表姐一個名分。之前自己只站在子的立場上來看問題,卻忘了被算計的人,要被加強一個妾室,心裏也是不痛快的。
君逸之正想問父親臨終前的事,俞筱晚忽地笑道:“快到了。”
前方已經有火了,也傳來了呼喚聲,君逸之就抿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33 章

偏執太子是我前夫/歲時有昭(重生)
容舒嫁顧長晉時,并不知他心有所屬,更不知她娘為了讓她得償所愿,逼著顧長晉的心上人遠嫁肅州。成婚三年后,顧長晉被當朝皇后尋回,成了太子,而容家一朝落難,抄家罷爵,舉家流放肅州。容舒連夜去求顧長晉,卻被他囚禁在別院。入主東宮后,他更是連夜去了肅…
54.7萬字8 88002 -
完結125 章

枕叔
赫延王府來了個姝色無雙的表姑娘,走路裙裾不動釵墜不晃,人人都夸她名門之儀。長輩有意選她當三郎媳。年關將至,赫延王府的主人封岌歸京。寒酥隨王府眾人迎他凱旋,卻在相見時,臉色煞白,禮數盡忘。沒有人知道,她赴京途中為求自保,是如何進了他的帳入了他…
46.1萬字8.33 60264 -
完結2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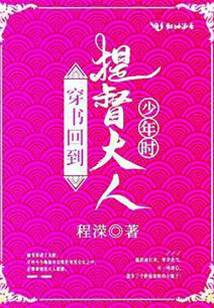
穿書回到提督大人少年時
她書穿成了女配,可憐兮兮地混在公堂的男男女女中,正等著知縣大人配婚。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按照劇情她注定是炮灰,超短命的那種。 她不認命,急切的視線在人堆裡可勁兒地扒拉,終於挖掘出他。 夭壽呦,感情這小哥哥,竟是男二! 連女主都無法覬覦的狠人! 這位爺有秀才功名在身,卻被至親算計,入宮成為殘缺不完整的太監。 他生生地熬過種種苦難,任御馬監掌印太監,最後成了人人敬畏的提督大人。 他曾顛沛流離,人人嫌惡,也曾位高權重,人人討好。 成為看盡人生百態,孑然一生的權宦。 但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壽終正寢! 只要她抱緊他的大腿兒,定能擺脫螞蝗般的至親,待日後做了大宦官之妻,更是吃香的喝辣的,還不用費勁巴拉的相夫教子。 小日子簡直不要太美好,撿大漏啊! 他一朝重生,再回少年時,尚未入宮,更未淨身。 眼下,他還是小三元的窮秀才,父暴斃而亡,母攜家資再嫁。 他浴血歸來,渾身戾氣,可一時善心,就多了個嬌嬌軟軟的小娘子! 說啥他這輩子也不淨身了,好好地考科舉,走舉業,給她掙個誥命夫人做,再生幾個小崽子玩玩兒……
44.7萬字8 23041 -
完結1362 章
相公高中后我決心跑路
白心月穿書了。 穿成了科舉文男主韓文旭的童養媳,全文中最傻的炮灰。 原主作天作地不說,還想偷韓文旭的束脩逃跑,被韓家人抓住后,不出三章就一命嗚呼…… 白心月撓頭:這個路線,我不走。 生活本來就舉步維艱,還有個該死的系統不停瞎指揮! 白心月握拳:我要反抗! 穿到原主偷束脩的橋段,白心月掏出僅有的三文錢,嬌羞的用腳尖畫圈圈:“我給相公存點束脩。” 面對原主嫌惡的顧母,白心月主動示好:“母親,我以后肯定孝順你。” 碰上不搭理原主的韓文旭,白心月一邊計劃逃跑,一邊繼續羞答答的叫:“相公,辛苦了。” 利用金手指,白心月努力賺錢,成功收編顧氏一家,就連冷面冷言的韓文旭也 “心月,待我科舉中考,娶你可好?” 嗚呼?這……自己逆襲成女主了?
245.3萬字8 138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