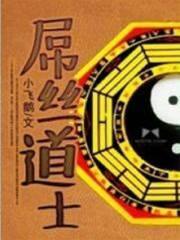《麻衣神相》 第246章 木家火毒
那山嶺層層疊疊,嶺下是一塊平地,平地右側然而高,似乎連著一個窄小的口。
口站著一人,滿頭白髮,披肩散落,恍如皓雪覆首;其著一皁,上下纖塵不染;一柄拂塵倒握手中,低垂,那不是別人,正是以了塵師太自居的木菲明!
木菲明對著口而立,其後不遠乃是兩個子,其一明眸皓齒,形容清麗極致;另一個子巧笑嫣然,容驚豔無雙。這兩人正是木秀和木仙!
我稍作打量,便發現有些不對勁,木秀和木仙雖然都是坐著,但是木秀的子僵直,而木仙卻很放鬆,再仔細端詳時,便能發現木秀面有慍,而木仙渾不在意。
我略一思忖,便料想到木秀極有可能是被封了道,而木仙卻無礙。
木秀和木仙後不遠,全都披著綠的木賜默然而立,打在他臉上,將其皮映襯的慘白一片。
在白天,沒有噬魂鬼草那邪惡魂力的掩飾,其俊俏的容在我眼中變得更加清晰和真實,他那雙藏著不盡惆悵和落寞的眼睛,依然滿是怨恨、乖戾的厭世神。
木賜後站著兩個瘦削的漢子,一人神冷漠,面上廓分明,眼中戾氣深重,乃是田飛田老大。
還有一人神恭順,但周也有殘忍之氣,卻是一直跟在田飛邊的任老六。
這兩個人怎麼也在這裡?
而且還和木家人混在一起?
“金頭蜈蚣!火毒蜈蚣羣!”
表哥忽然低聲道,臉已微微變了。
我把目從田飛、任老六上移開,這纔看見木賜腳下昂首立著一條巨大的蜈蚣,其饅頭大小的金頭顱在太下熠熠生輝,兩條顎肢如生鐵鑄就的鐵杵一般,五十對步足恍若一個模子裡造出來的鐮刀,枝枝杈杈地在它那如披鎧裹甲的斑斕下。
Advertisement
金頭蜈蚣的前方,有一個偌大的低窪,猶如一片陷坑。
那低窪足有兩尺之深,其中麻麻的全部是緩緩蠕著的猩紅小蜈蚣,遠遠去,如一片水,朝著中央涌!
我的目瞟向那一大片慢慢蠕著的猩紅蜈蚣羣中間,不由得大吃一驚,因爲蜈蚣羣的最中央,竟盤膝坐著三個人!
這三人均是面朝外,背朝,環一圈,相互依靠在一起,每個人都是雙盤膝,一手訣,另一隻手著一張黑紙符,橫於前。
三個人的眼睛都似閉非閉,鼻翼一不,恍如老僧定。
與我正對的一人,皓髮如雪,長眉長鬚,即便是坐在那裡,其魁偉的材也顯無,是太爺爺!
當我的目掃過他那舊的發白的道袍時,心底驟然一,其口竟有一片斑斑暗紅的跡!
我順著太爺爺往其子左側往去,一個俏生生的影秀眉微蹙,滿頭青縷縷散,我不又是心頭一,那是江靈!
江靈挨著的是一個著紅道袍的長鬚道人,其肩頭有一塊蒸騰的雲氣圖案,那圖案下方還繡著一片翻落的楓葉。
此人我見過,在仙枯旁,落崖的前一刻,與太古真人一道趕來的中年道士,江靈的師父,茅山紅葉!
太爺爺、江靈和紅葉道長,他們三人竟在一起,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更讓我詫異的是,眼前的形勢顯然是他們三人於極其危險的境況!
“火毒蜈蚣很厲害嗎?”我憂心忡忡地問表哥道。
表哥點點頭道:“蜈蚣本爲五毒之首,最猛,毒最烈,但卻仍是蟲,所以一般只能在夜間行。但是你看這些蜈蚣,在烈日之下卻依舊如此活躍,顯然是變異種類,不是毒之,而是毒之,這與我家的阿子倒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就是靈家族才能培育出來的火毒蜈蚣!你看那三人膝前……”
Advertisement
聽表哥如此說,我便仔細往他們膝下去,只見距離他們膝蓋不遠的地上,竟有一大圈晶瑩剔、狀如琥珀的粘稠。
我悚然容道:“那是毒?”
表哥點點頭道:“那三人不知道使了什麼辦法,讓火毒蜈蚣不能近,所以火毒蜈蚣拼命強攻,在自己能達到的最近距離,將毒盡數吐出,那毒只要越積越多,恐怕遲早會突破被困三人的防線。”
我看火毒蜈蚣羣距離太爺爺他們三人最近的距離只有三尺左右,三尺之外,不計其數的火毒蜈蚣已經圍攏一個大圈,雖然進展緩慢,但是它們正前仆後繼地將圈子一點一點小!
表哥道:“這三人也不知是什麼來歷,竟被木家如此死死相,奇怪的是,木家的人又只是用火毒蜈蚣進攻,而他們的人卻不手……”
表哥自顧自地說話,而我心中確實憤怒至極,江靈一直未歸,太爺爺尋人也未回,原來是在此難!
“哥……”我沉聲喊道。
“哎。”表哥應了一聲,繼而詫異道:“你的臉怎麼這麼難看?”
我緩緩道:“被困的三人裡,老道士是我太爺爺陳天佑,孩兒是我的人江靈,中年道長是江靈的師父茅山紅葉。”
“啊?元方,你剛纔在說什麼?”
表哥瞠目結舌地看著我,一時間有些反應不過來。
“我不是開玩笑的。”我補充道。
表哥有些醒悟似的道:“我現在知道木家人爲什麼這麼爲難他們了,木家本就是陳家的世仇,自然不會放過陳家的親人。”
我目不轉睛地盯著太爺爺他們,道:“哥,咱們衝上去,把他們救出來。”
Advertisement
“你別!”
表哥低聲喝道:“咱們兩個恐怕不行,按最樂觀的形,你能對付木賜和那兩個漢子,我能對付那兩個丫頭,還剩下一個看上去最厲害的帶發老尼姑,給誰?萬一不蝕把米,沒救得了他們,又把咱們搭上去了,怎麼辦?”
表哥說的有理,我對付木賜尚需費一番工夫,再加上田老大、任老六,幾乎不可能取勝;而沒有阿子的協助,表哥與木仙的水平應該是半斤八兩,還剩下一個最厲害的木菲明,極難理!
我雖然心燥,也不能不聽,當下只能是焦急地冒汗。
表哥忽然道:“我覺有些奇怪,那個老尼姑一直盯著那個小山幹什麼?還有他們爲什麼不趁著天佑道長他們自顧不暇時以人力配合火毒蜈蚣合擊?還有那個長相清秀的孩兒,怎麼好像是被制住了的樣子?”
我道:“那老尼姑木菲明,是木賜的父母輩人,極其厲害;那兩個漢子,一個田飛,一個任老六,也是極厲害的角;那兩個孩兒就是木賜提到過的兩個兒,木仙和木秀,木秀應該是被點了道,是我的好朋友,或許是不願意與太爺爺他們爲敵才被制住的。”
“好朋友?”表哥若有所思地看了阿秀一眼,然後又看看我,沒有說話。
我心中頗有些不是滋味,口裡說道:“我也奇怪,他們若是趁著火毒蜈蚣困太爺爺的時候,猛下殺手,以木菲明和木賜的手段,應該能很快取勝。還有,木菲明一直盯著那口,是做什麼?”
表哥嘆口氣道:“你倒是沒說話,把我問你的問題又重新問我了一遍。”
我默默無語,我突然發現,有親人在邊的時候,我往往不及獨一人時冷靜,甚至於不會真正地思考問題了。
Advertisement
我努力使心穩定了一些,太爺爺他們到現在並未出事,只要我想出辦法,這局面就還能挽救。
呆了片刻,我腦海裡靈一閃,忍不住道:“哥,不對呀!”
表哥道:“怎麼?”
我道:“咱們到這裡是小花鼠引得路,也就是說老舅在這裡,可到現在,怎麼連老舅的影子都沒看見?”
表哥看了看草叢裡那五隻做臥伏狀態並瑟瑟發抖的花鼠,沉默片刻,道:“我早就想到這個問題了。只是那金頭蜈蚣以及火毒蜈蚣羣實在是花鼠的剋星,這五隻小東西只敢把咱們帶到這裡,便再不願前進一步了。這是趨利避害的本能,就連我也無能爲力。”
我看了看那五隻花鼠,然後悠悠道:“或許我能猜到老舅在哪裡。”
表哥訝然一聲:“嗯?”
我用努了努木菲明所在的方向,道:“或許老舅就在那個小山裡。”
表哥臉一變,驚詫道:“不會吧?”
我篤定道:“這應該就是木菲明一直盯著那山口的原因。”
表哥也慌了,他喃喃道:“那麼小的一個口,怎麼會在那裡?木菲明這是要做什麼?父親爲什麼不出來?”
我道:“若木家和陳家是世仇,那麼和陳家聯姻、同時又是靈家族的蔣家,豈不更是木家的敵人?”
表哥額頭上的汗一下子就滴落下來,脣都有些微微抖。
我連忙安道:“哥,我也只是推測,不一定是真的。而且退一萬步來說,即便真的是這樣,木菲明還不放鬆警惕,這就說明老舅沒事!”
表哥的臉這才稍稍放鬆,他上下牙齒一,咬的“嘎吱”作響,恨恨道:“我現在才明白金頭蜈蚣爲什麼三番兩次吃掉給我引路的花鼠了,原來是要斷了父親的救兵!還有那個木賜上次與我拼鬥時道知道我是誰了,原來他也早就知道我父親!這些個混蛋!要是父親有什麼差池,我蔣家就把木家從地球上永遠磨去!”
正說話間,木菲明忽然揚聲喊道:“蔣明義,他們三人就快不行了,你難道真見死不救,還不出來嗎?”
我和表哥同時變,老舅果真在那裡!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70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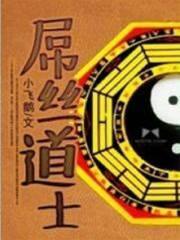
屌絲道士
一個尿尿差點被電死的男人,一個運氣差到極點的道士!他遇到鬼的時候會惹出怎樣爆笑的事端?各種精彩,盡在屌絲道士中。
182.8萬字8 7023 -
完結259 章

13路末班車
我是13路末班車的司機,每晚11點我都要跑一趟郊區。此書有毒,上癮莫怪! 。 。 。在這本小說裡你可能發現一向猜劇情百發百中的神嘴到了這居然頻頻打臉,你可能讀著讀著就會問自己“咋回事?咋回事?”請別懷疑人生,繼續往後看。 “懸”起來的故事,拯救書荒難民!
71.1萬字8 8113 -
完結725 章

陰婚纏身:鬼夫賴上門
被唯一的親人賣去窮山村,我差點被七十歲老漢強奸! 死里逃生卻遭遇靈異,一個巨大的陰魂要了我的第一次…… “女人,你注定是我的人!”吃干抹凈,他竟然霸道的宣布了對我的主權,而我,怎麼可能嫁給鬼丈夫?鬼夫賴上門,如何是好。。。。
137.5萬字8 11417 -
完結561 章

詭墓密碼
作為盜墓賊的兒子,我沒想到,挖的第一座墳,竟是我爸的墳,墓中的一枚古玉讓我深陷泥淖。女真疑冢,苗疆禁地,古遼迷霧,絕壁雪山……我追尋父親的足跡,卻深陷進縈繞千年的危險迷團。每個人都不可信任,每個人都有不能說的秘密,每個人都在幫我,也都在害我……當《永樂大典》殘卷,揭開所有真相,我才明白:有種宿命,即便歷經千年,也無法逃脫。
107.8萬字8.18 14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