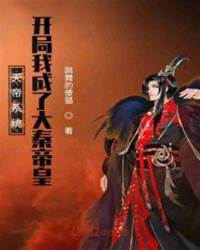《上品寒士》 六十二、美人如花隔雲端
?六十二、人如花隔雲端
皇帝司馬丕和靜皇后同日駕崩,擇吉將於六月初五甲子日出葬,魏晉多有「禮教豈為我輩而設」之狂放任誕,但在帝后出殯前無論士庶軍民皆不得婚姻嫁娶、歌舞飲宴,這是最起碼的,然而姑孰城卻好似國中之國,一切如舊,姑孰溪南岸的酒寮娼肆並未關門大吉,照樣有尋歡作樂之人,只是了軍府的吏將校而已,市井小民本不知道皇帝司馬丕駕崩之事,說起來還以為是穆帝司馬聃呢,司馬聃就是去年五月駕崩的,皇帝更換頻繁,姑孰百姓都記不住,只知道桓大司馬坐鎮姑孰已經四年,桓大司馬政令寬簡,.
桓溫一貫的策略是,不輕易都、不擅離軍隊、不落人口實,老持重、循序漸進,所以帝后駕崩,桓溫以危急為由,依舊不建康,只派長子桓熙赴京向臺城宮闕哭臨致喪,而同時,他與郗超之間的信使往來頻繁,對朝堂之事了如指掌,桓溫表奏征西參軍郗超為中書侍郎、荊州刺史桓豁監荊、揚、雍諸軍事、江州刺史桓沖監江州八郡諸軍事、並假節,朝廷不能不允,詔令將會在帝后出殯後下達,同時,會詔拜揚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王述素與桓溫不睦,朝廷征王述主臺城,也是為了制衡桓溫,朝廷既答應桓溫奏請郗超為中書侍郎諸事,桓溫自也不便反對王述為尚書令,朝廷與世家大族聯合起來,目前還能勉強維持與桓氏的微妙平衡,桓溫現在就是想打破這種平衡——
桓溫將陳之所陳的便宜七事和謝玄、陳之共擬的《強軍策》傳遞給郗超參謀,郗超對《強軍策》尤為讚賞,他知道陳之沉穩、謀定而後,既然陳之說可以煉製出更良的兵,那就不會是虛妄語,郗超請桓大司馬儘快施行,為第三次北伐早作準備,至於便宜七事,則要請桓溫奏請有司推行,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大閱戶人、實行土斷,郗超建議謝玄當此大任,陳之、祝英臺為輔,他事可緩,此事宜在今年推行,要雷厲風行、嚴其法,不能象往年檢籍那般敷衍了事,世家大族的利益非不可——桓溫深以為然。
Advertisement
郗超又向桓溫報告了敦請祝英臺西府之事,郗超已派人去了上虞訪,確認上虞祝氏無祝英臺此人,祝英臺就是謝道韞,此事已確然無疑,桓熙到建康之後,郗超又與桓熙一道去烏巷謝府拜訪,重申桓大司馬對祝英臺的慕之意,雖未見到那個祝英臺,但謝氏想必明顯到了桓溫施加的力,謝安要想朝為,就不能忤桓溫之意,因為恆溫徵辟祝英臺是名正言順之事,並非無禮要求,郗超只擔心謝氏在推託不得的況下會幹脆表明祝英臺的真實份,這樣桓溫只有作罷,但謝氏顯然不會這麼簡單理這種事,因為這樣,祝英臺固然是不用西府了,但謝氏聲譽已經到了影響,在謝氏看來桓溫也會覺得到了愚弄,何如讓謝道韞悄然西府,一年半載之後再稱病告退,這既不會與桓溫惡,又全了謝氏的聲譽,而且據郗超所知,謝玄似乎是贊其姊西府,想必謝玄與陳之好,深識陳之之才,又知其姊謝道韞一片癡心全繫於陳之上,是以有意讓陳之與其姊謝道韞多想,促二人姻緣,故而郗超建議桓大司馬,待帝后出殯之後,遣陳之建康再征祝英臺西府,然後由謝玄、陳之、祝英臺三人主謀大土斷事宜——
桓石虔、謝玄、陳之三人來到將軍府時,見沈勁也在,卻原來是桓溫以危急為由不能京為哀帝致喪,大司徒司馬昱與尚書僕王彪之等人商議,決定準桓溫所奏,詔以沈勁補冠軍長史,不待哀帝出殯,命沈勁先率自募勇士北上助冠軍將軍陳祐守,桓溫今日乃是為沈勁壯行。
簡單宴席之後,沈勁即拜辭桓溫,即日率眾渡江北上,桓溫命桓石虔、謝玄、陳之代他送沈勁一行至姑孰溪江口,由西府水軍船隻渡其過江,陳之見桓溫並未給沈勁補充兵員,隨沈勁渡江北上的依舊是沈勁從吳興帶來的千餘壯士,心裡暗暗一嘆。
Advertisement
沈勁與其手下勇士卻是意氣風發,與上次自發北上不同,此次是奉命而行,沈勁山是七品冠軍長史,其部眾皆有榮焉。
臨上船,沈勁與桓石虔、謝玄等人一一道別,臨到最後,執著陳之之手,說道:「陳掾力薦之恩,但沈勁不死,定當后報。」長揖到地,大步上船。
十艘西府水軍船隻將沈勁千餘人一次送過江去,炎朗照,船帆鼓風,兵船很快離南岸遠了。
陳之著江上的帆影,他知道沈勁諸人的結局,大約兩年後,陳祐以救許昌為名,率眾而東,只留沈勁五百人守,慕容垂攻陷,沈勁殉國。
陳之心道:「應該是可以固守的,但桓溫卻不派兵去救,這次沈勁北上,桓溫連五百軍都不肯助,難怪當年王猛不肯隨桓溫南下——」
桓溫第一次北伐時數敗秦軍,屯軍灞上,關中父老簞食壺漿來迎,北海王猛披著布來見桓溫,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桓溫驚嘆王猛之才,問:「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王猛對曰:「公不遠數千里,深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王猛話中的含意是說桓溫北伐非是恢復中原,而是意在威服江東,這說中了桓溫的心病,桓溫嘿然無以應,徐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任命王猛為軍謀祭酒,旋又遷高督護,可謂恩遇,但王猛辭而不就,不肯隨桓溫回江東。
史載王猛不肯南下是因為看清了桓溫必然要篡晉自立,擔心追隨桓溫玷污了自己清名,還不如繼續留在中原以待時變,其後苻堅即位,重用王猛,秦國大治,後世人稱「關中良相惟王猛,天下蒼生謝安」。
Advertisement
讓陳之略奇怪的是,王猛不願追隨桓溫卻願意殫竭慮輔佐氐羌人苻堅,臣事異族和輔佐桓溫篡晉都是同樣玷污清名的,那應該是個託辭吧,江東世家大族盤踞,王猛一介北地寒士,很難有作為,這才是王猛不肯南下的主要原因。
陳之融合了千后的靈魂,忠君思想淡薄,既然司馬氏可以篡魏,桓溫篡晉亦無不可,他輔佐桓溫並無聲譽上的顧慮,但現在的問題是,桓溫值得輔佐嗎?桓溫固然是雄傑,但年過五十,壽命也不長了,桓溫的幾個兒子都是庸碌無能之輩,不然的話桓溫也不會命其弟桓沖掌權,至於桓玄,現在還沒出世,也不知能不能出世,先且不論,他陳之若輔佐桓溫為帝,或可博得一時榮華,但桓溫一死,江左勢必大,他陳之作為桓溫的左右臂就首當其衝了,禍不可測——
當此之世,紛爭詭譎,前途茫茫,陳之也只有披荊斬棘前行,每一個岔路口都要權衡取捨,而目下,追隨桓溫則是最好的選擇,否則他就會象王猛怕來到江東一樣會一事無,陸氏郎也會是人如花隔雲端——
……
李靜姝自那日在姑孰溪畔陳之答應教授豎笛,此後數日一直未在陳之面前面,也未派人來獻拜師束脩禮,陳之心想:「那李靜姝可能就是不忿我拒絕教授簫,既已我答應,怨氣已消,或許就此丟在一邊了。」又想事恐怕沒有那麼簡單,總是心有芥,難以消除。
冉盛每隔五日便回姑孰城住一日,他隨軍練,日曬雨淋,面明顯就黝黑了,絡腮鬍子長得極快,往日單純的目也已變得沉毅,在軍營中絕無笑容,手下的十名軍士畏之如虎,只有在陳之和荊奴面前,冉盛還偶爾會流年的笑容。
Advertisement
荊奴對冉盛即將升任百人屯長非常高興,以冉盛的勇武,三年之升為千人部曲督應非難事,荊奴倒是沒有指冉盛有朝一日恢復大魏國,荊奴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冉魏的舊臣部曲幾乎被慕容氏屠戮殆盡,已無復國的基礎,冉氏本是漢臣,現在回到東晉效力正合其宜,有陳之照應,荊奴也沒什麼不放心的,他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荊奴在姑孰住了十日,五月二十一日帶著阿柱和兩名陳氏私兵回建康,見過陳尚之後再回錢唐,另兩名私兵則留在了陳之邊聽用,陳之給四伯父陳咸、三兄陳尚、嫂子丁微各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解釋了認冉盛為弟的緣故,說冉盛是穎川陳氏流亡到江左的,陳之知道族長四伯和三兄陳尚肯定有疑,可他也沒打算把冉盛的真實份告訴他們,這事知道的人越越好——
冉盛在書案邊侍坐,看到陳之給潤兒寫信,說了一句:「潤兒小娘子會奇怪得合不攏吧?」
陳之微笑道:「免不了會奇怪的,只怕以後相見時潤兒不肯稱呼你為叔父。」
冉盛出難得的笑容,說道:「還是象以前一樣小盛為好,不然的話,想到潤兒小娘子要我叔父,我都不敢回陳家塢了。」
……
來德留在了姑孰,荊奴離去后的次日,陳之便帶著來德去見桓溫,桓溫即任命來德為考工兵曹的佐吏,命來德負責製作反覆推拉式風箱,來德在陳家塢已經製作了十多個這種風箱,可謂駕輕就,當然,軍府的兵鍛冶所需的風箱要大得多,只要把尺寸放大數倍便可。
五日後,西府的第一座大型反覆推拉式風箱製,桓溫親自前往參觀,只見這種風箱由兩個大漢負責推拉,風力強勁,鼓得爐火純青,在場的鍛冶匠大喜,他們都知道只要爐火足夠旺,熔化鐵礦石就更純粹,打造的鐵則經久耐用,而且此時的鍛冶匠人已經掌握了炒鋼技和摺疊鍛打技,即百練鋼,現在有了這種反覆式風箱,東晉的鍛冶水平將越一大步。
六月初五甲子日,是哀帝和靜皇后出殯之日,桓溫率西府軍吏將校素服臨東門致哀。
六月初十午後,桓熙與郗超從建康回姑孰,同來的還有侍中張憑,張憑此行的目的是奉詔加征西參軍郗超為中書侍郎、荊州刺史桓豁監荊、揚、雍諸軍事、江州刺史桓沖監江州八郡諸軍事、並假節,還有一個使命便是奉皇帝司馬奕之命召桓溫朝參政。
郗超這次回來是搬取家眷去建康,此後郗超將在朝中為,當夜桓溫召郗超將軍府談,談的容不得而知,次日桓溫便上表朝廷,婉辭錄尚書事一職,不肯朝,同時上疏陳便宜七事,請有司推行。
侍中張憑傳過詔令后的次日便向桓溫辭行回建康,桓溫送其至白紵山,又命陳之代他再相送一程,張憑是張墨之兄,在建康就很賞識陳之,今見陳之在西府頗相得,也為陳之欣喜。
陳之送罷張憑回到凰山下寓所,卻見李靜姝派人送來了束脩禮:四脡脯、四條鯗魚、四甕秫酒、四匹束帛、四匹生絹、四匹蜀錦、四塊蜀玉——
陳之頓覺棘手,原以為李靜姝已忘了拜師學簫之事,沒想到久不見靜是為了等帝后出殯,國喪期間自不好吹管弄弦,李靜姝還真沉得住氣啊。
左朗來報,郗參軍拜訪。
陳之去迎郗超進來,郗超笑道:「此是安石公舊居,子重住得適意否?」不待陳之回答,又道:「子重,後日你與我一道赴建康,你奉桓郡公命再次徵召祝英臺西府,亦可順便見一見陸氏郎,此是差。」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57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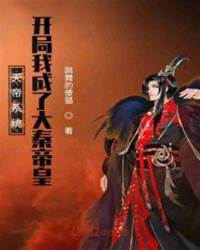
天帝系統:開局我成了大秦帝皇
贏玄穿越到了大秦,得到了天帝系統,成為大秦帝皇,開啟屬於他的大秦霸業。秦皇天威,鎮壓萬界。凡日月所照,天威所至,山河萬界,皆為秦土。大秦銳士,所向披靡。凡兵鋒所指,天下各國,聞風喪膽,無人可擋。贏玄君臨天下。朕是秦皇帝,萬古第一帝!
292.5萬字8.18 48070 -
完結3521 章

三國之經天緯地
人生低谷中的劉緯,機緣巧合下,穿越到了公元200年的三國時代,開啟了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 他由小到大,由弱變強,平南蠻、奪益州,收攏天下英雄豪傑,南攻劉備、孫權,北擊曹魏、五胡,最終一統天下,中興漢室! 這裡有權謀詭詐,也有兵法奇計;有超時代的技術,也有精彩的戰鬥畫面! 讓我們一同走進這個英雄輩出的亂世,共同見證那綺麗輝煌的宏偉大業!
706.6萬字8.18 70232 -
完結2866 章
回到古代當贅婿
一個從未出現過的朝代,一個穿越到婚房的倒楣大學生,一座神奇的圖書館,成就了一段舉世無雙的傳奇人生,當林寒以優雅的姿態走著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時,大寧朝上下對'妖孽'二字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 世上的道路千千萬,總要一條一條試試嘛。 林寒語。
690.6萬字8 1183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