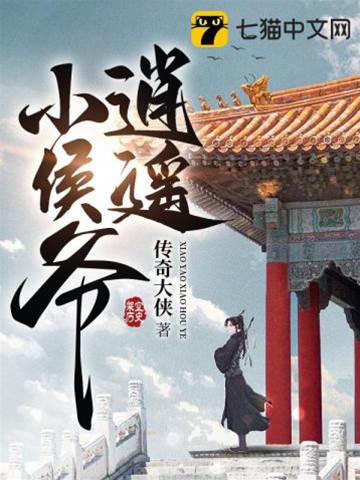《上品寒士》 五十六、耀武
?五十六、耀武
陳之是九品征西掾,軍府按定製撥給小吏一人為陳之理日常雜務,該屬吏名左朗,出寒門,年過三十猶是最底層的濁吏,謙卑已滲到骨子裏,對陳之是畢恭畢敬,辦事雖算不得麻利,好在言語不多、.
四月三十,西府休沐日,陳之來姑孰已經六天,算是安頓下來了,便分別給三兄陳尚、好友顧愷之,還有陸葳蕤寫了一封信,派來震送去建康,謝玄也派了一名信使與來震結伴回京,送信給四叔父謝萬和阿姊謝道韞。
來震剛出門,左朗進來稟道:「汝南周琳來訪。」
陳之與汝南周迥有過一面之緣,周迥亦是謝道韞求婚者之一,但這個周琳卻是沒有聽說過,問左朗,左朗也說不認得,只說是個十二、三歲年。
陳之便命左朗請那周琳進來,那周琳子裝束,和宗之差不多大,面如芙蓉,舉止得,見到陳之,恭恭敬敬行禮道:「家姊命我來謝過陳兄——」見陳之面疑問之,便解釋道:「我姊夫就是郗嘉賓,我前日自豫州來此看阿姊。」
陳之恍然,離京時郗超曾托他帶了一些品給其妻子周氏,陳之到姑孰的次日,便讓小嬋和黃小統把品給郗夫人周氏送去,郗超不在,陳之自是不便登門拜訪,只寫了一封書帖代為問候,沒想到郗夫人會讓其弟前來答謝,陳之曾聽郗超說過,其岳父周閔無子,以弟周頤之子周琳為嗣。
魏晉南北朝貴族子取名不俗,尤以皇后的名字為稀奇,曹丕的皇后名郭王、晉惠帝皇后賈南風、當朝皇太后褚蒜子、王獻之與司馬道福生的兒後來也做了皇后的名王神——所以,郗超夫人的閨名周馬頭也就不顯得過分奇怪了——
Advertisement
郗夫人周馬頭出汝南大族周氏,其父周閔至尚書僕、加中軍領軍,其祖父名氣更大,便是那個周伯仁,史稱「雖招時論,然瑕不掩瑜,未足韜其也」,陳之對這個周伯仁印象深刻,不只是因為周伯仁曾非禮紀瞻妾,而是因為周伯仁與王導之間的恩怨,當初王孰叛,王導因為是王敦族弟,怕牽連,跪在宮闕外請罪,值周伯仁宮,王導哀求說:「伯仁,我一家百口都要託付你了。」周伯仁毫不理睬,宮對明帝說王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留周伯仁飲酒,周伯仁喝得醉醺醺出宮,王導還在宮門前,又求周伯仁,周伯仁不答,卻噴著酒氣說:「今夜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於肘后——」,王導自然以為周伯仁不救他,甚恨之,其後王敦建康,徵求王導的意見,問是給周伯仁高做還是殺掉?王導都是一言不發,於是王敦就殺掉了周伯仁,後來王導料檢中書故事,看到了周伯仁救他的奏章,言辭人、殷勤切至,王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對諸兒說:「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王導是痛悔終生——
周伯仁就是典型的魏晉人,既高貴又放、既彷徨又執著,留給後人的教訓是:做了好事要留名——
陳之看到周琳就想起侄兒宗之,周琳比宗之大一歲,但稱呼陳之為陳兄。
「陳兄,」周琳說道:「久聞陳兄的豎笛曲是江表一絕,家姊和我都想聆聽一曲。」郗超時常誇讚陳之,桓伊楓林渡口贈笛一事,周馬頭、周琳姊弟都聽得耳能詳,周琳年紀雖,卻雅好音律,聽說陳之將西府,便從豫州趕來,一是看阿姊,二是想聽聽陳之的豎笛究竟有多妙聽——
Advertisement
陳之不是迂執的人,略一躊躇,說道:「好,何時去?」
周琳睜大眼睛道:「自然是早早益善。」
陳之含笑道:「那好,就現在去。」讓小嬋攜柯亭笛,又命黃小統去請謝玄與他同往。
郗超寓所並不在凰山下,而是與大將軍府毗鄰,都在城西,比軍府其他吏的住寬綽豪華得多,也凸顯郗超地位的超然。
郗夫人周馬頭自不便出來相見,由弟周琳代為應客,郗夫人周馬頭隔著屏風與陳之、謝玄二人略事問答,陳之便執柯亭笛吹曲子《憶故人》,才清吹幾聲,就聽得屏風後有人低聲說話——
陳之墨眉微皺,柯亭笛吹口離開邊,簫聲頓止。
屏風后的郗夫人周馬頭趕緻歉道:「陳郎君莫怪,有一客來訪,我去去就來,抱歉,抱歉。」足音急促,往後院去了。
陳之暗暗奇怪,這客怎麼從後院來?也不便問,對周琳道:「我吹罷兩支曲子便告辭。」
周琳道:「好,主要是我想聽陳兄的曲子。」
陳之便將《憶故人》、《紅豆曲》這兩支曲子各吹奏了一遍,簫聲清高而寂寞,彷彿暮春的向晚,夕西下,遠山青嵐,如霧繚繞;又彷彿夜風帶來的清香,沁人心脾,嗅之又杳然;更彷彿江南煙雨一般的思緒,迷濛纏綿,百轉千回——
屏風後足聲細碎,有數人來到,而後便悄然無聲,直至簫聲裊裊消散。
陳之清晰地聽得屏風后一聲嘆息,就是這一聲嘆息,也不勝宛轉之致。
陳之一愣,心道:「這是郗夫人周馬頭的嘆息嗎?不對啊,那位客的聲嗽怎麼有些耳?」
陳之不便久坐,即與謝玄一起告辭,周琳送出府門,這個十三歲的年對陳之是肅然起敬了,說道:「陳兄,在下想拜你為師學豎笛,不知陳兄可肯答應?」
Advertisement
陳之想著宗之也說過要向他學豎笛,現在卻遠隔千里,說道:「軍府沒有那麼休閑,不是吹拉彈唱之所,你既喜音律,我可以錄幾支曲譜贈你。」
離開郗超寓所,陳之與謝玄一路往凰山方向行去,謝玄問道:「子重可知郗夫人客是誰?」
陳之道:「不知。」
謝玄道:「郗嘉賓寓所與將軍府毗鄰,後園有甬道相連,這客大抵是桓大司馬眷,極有可能便是那李靜姝。」
陳之微笑道:「那我要退避三舍了。」
謝玄道:「西府兩大難惹之人,郝隆你算是惹過了,但這個李靜姝萬萬不要惹。」
陳之道:「阿遏此言何意,我去惹作甚!」陳之現在與謝玄關係又切了幾分,以阿遏相稱。
謝玄笑道:「子重,你還不知道你的豎笛曲有多麼魅人,當年——不提了。」心裏想的是:「當年我阿姊可不就是先被你豎笛曲迷住的嗎。」
「荒唐!」陳之笑道:「這麼說我得摔碎柯亭笛,絕口不再吹曲了。」
謝玄笑道:「那就是罪過了——子重,我方才所言倒不是開玩笑,桓大司馬召見屬吏議事,常以隨侍,就好比後漢大儒馬融,晚年居家教授時,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后陳樂,以此來品鑒學生德行、磨練學生心志——」
陳之笑了笑,心道:「夫子心否乎?我陳之不是那好之徒。」
……
五月初一正卯時,桓溫命門令史召集西府長史、司馬、參軍、從事中郎、兵、鎧、士曹、營軍、刺、帳下都督、外都督、掾屬,齊赴子城校場觀看演兵耀武。
姑孰子城長五百丈、寬三百丈,主要用於屯兵、以及軍械的製造和管理,軍士的眷屬並不住在子城,在姑孰城南有一大片土房是兵戶聚居區。
Advertisement
東晉沿襲曹魏實行世兵制,所謂世兵制,就是兵民分離,兵戶另立兵籍,朝廷和軍府嚴格控制,兵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世代當兵,曹魏時,士兵還要實行「錯役」制,就是說士兵服役地要與居家地分離,士兵若逃亡,其妻子要懲罰,西晉以來,這項嚴刑峻法廢除,士兵出征本來就不可能把妻室帶上,只是平時練兵屯田,居家不再分離而已。
自晉太康年間推行占田制以來,這些兵戶也大都有了田地,境雖較曹魏時有些改善,但依然是等同於農奴,淪為兵籍的是罪犯、流民和俘虜,這樣的士兵戰鬥力是不強的,所以桓溫又以募兵制來補充兵員,其麾下荊襄戰士戰鬥力最強。
辰時初,姑孰子城東北大校場,嚴鼓三通,角號齊鳴,穿青、赤、黃、黑四種的兩千步兵列四隊,練涵箱、魚鱗、四門等十種陣法,又有一隊五百人的騎兵自校場東南角直衝而來,巨大的馬蹄聲彷彿雷神的戰車滾過,眨眼間衝過方圓十里的大校場,各種兵盤旋飛舞,飛龍騰蛇之變。
桓溫好事功、重武力,練兵有過人之,伐蜀大勝和兩度北伐皆有斬獲並非僥倖。
桓溫立在點將臺上,著校場上往來馳驟的荊襄銳步騎,意氣風發,問邊的陳之:「陳掾,我西府如此雄師,可復中原否?」
陳之道:「定能大司馬之志。」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36 章

大唐之攤牌了朕真不是你爹
李二陛下出宮遇刺被救,救命恩人李易歡張口就叫:“爹?”見識了“仙器”、紅薯以后,李二陛下決定將錯就錯。魏征、房謀杜斷、長孫無忌以及程咬金等人,都以為陛下多了一個私生子,這皇位繼承人,以后到底是誰?終于,李二陛下忍不住了,找到兒子攤牌:“朕真不是你爹!”李易歡:“我還不是你兒子呢!”
126.3萬字8 10209 -
完結8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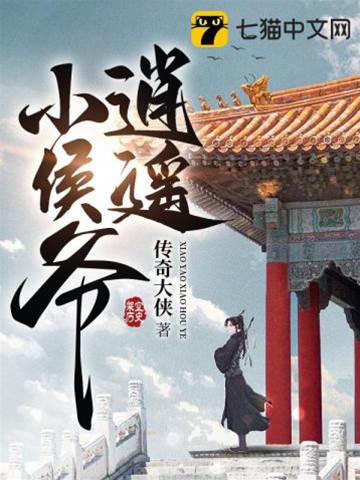
逍遙小侯爺
穿越古代,成了敗家大少。手握現代知識,背靠五千年文明的他。意外帶著王朝走上崛起之路!于是,他敗出了家財萬貫!敗出了盛世昌隆!敗了個青史留名,萬民傳頌!
148.9萬字8 98890 -
完結444 章

混在女帝身邊的假太監
一覺醒來,發現身在皇宮凈身房,正被一個老太監手拿割刀凈身是什麼體驗?徐忠萬萬沒想到,自己只是一夜宿醉,醒來后竟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還差點成為了太監,好在凈身時發生了點意外,讓他幸運逃過一劫。從此徐忠以一個假太監身份,混跡在女帝身邊,出謀劃策…
91.7萬字8 21123 -
完結254 章
三國:截胡劉備妻,我乃祖龍血脈
祖龍血脈贏武,三千兵馬起家,奪徐州,吊打劉備和呂布! 天下諸侯,盡皆震驚! “劉備、曹操、孫權,世家之患乃是天下大亂之本!” “你們沒有能力,也沒有魄力將世家門閥根除!” “讓我贏武來吧,以戰功論賞,恢復我大秦制度,才能讓天下百姓真正當家做主!” 贏武俯視江山,立下宏願。 一段可歌可泣的大秦重造之戰,正式拉開序幕......
44.5萬字8 87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