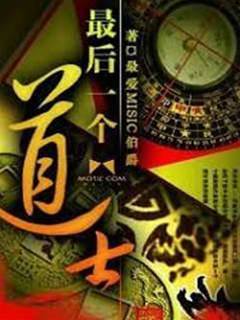《盜墓心經》 第315章 猛一下搭肩
因為有張如鐵跟王館長走在後面,北佬孫這會兒倒沒有biǎo xiàn 出毫膽怯來,看上去有些單薄佝僂的板,給人的覺倒也顯得意氣風發。<-.走在最後面的張如鐵是這麼認為的,而王館長心底卻是暗道:老夥計,又裝了。他是真懂zhè gè 多年相的老夥計啊。
北佬孫跟王館長認識的年份,估計沒有十年也有八載,所以對他的看法自然也是一目了然,就他眼下這裝勁,王館長用腳底板也知道,那是他做給後zhè gè 年輕人看的。
不過裝就讓讓他裝吧,反正也不是什麼壞事,一來能改變北佬孫zhè gè 投機派的形象,二來則是改善他們之間的guān xi ,畢竟來日方長,大家guān xi 融洽,才是走的長久之道。如果guān xi 疏遠了,或是看法偏見多了,那就不好了。
……
北佬孫一邊走,一邊拍打著地上的煙灰,還有是不是被刮起來的星diǎn火苗,不遠的蟻,由於長時間被螞蟻霸占,不知道是儲存有大量的油脂還是甜食一類的東西,烈火熊熊中,竟是散發出一香氣來,這種類似與烤螞蚱的wèi dào 伴著燒焦的氣息,讓三人都是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這要是烤,還真過癮。”
北佬孫放下jiǎo bu ,對後面大腹便便的王館長h道。張如鐵此時已經走到了最前面來,聽到北佬孫這句話,拍手稱贊道:“我h老孫啊,一直聽h你們老家廣東汕是粵菜的正宗,有時間hui qu ,也給我們一手,怎麼樣!”
Advertisement
“zhè gè ,當然是沒問題的啦。”北佬孫回道,“我跟你們h,我們廣東菜,最拿手的jiu shi ,基本什麼都能吃的,像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裡遊的,只要是我們能看到捉到挖到的,都可以拿來當菜吃。”
“不信!”
王館長雖然離開東北多年,依舊是直爽回應道。
“我介麼跟你們h吧,除了板凳長腳不能吃,棺材生黴不能吃,還真就沒有我們不敢吃的東西。”
“這我倒聽過。”
久居黔中,張如鐵自然是聽h過廣東人是什麼都敢吃,什麼都能吃的主。
“知道吧,我們廣東菜有一道很有意思的生吃做法,三,聽h過吧!”
王館長搖搖頭,他這些年雖然廣東去了不趟,倒還真沒聽過被北佬孫稱為三的東西為何。
“zhè gè 所謂的三啊,其實jiu shi 白鼠的一種生吃方法。其實~”
“等會兒,等會兒。”王館長聽到一個白鼠,又聽到一句生吃,立馬胃中已是翻江倒海襲來。
“你聽我把話h完啊,三,jiu shi 剛出生的xiǎo老鼠(活的)一盤,調料一盤。食用者用筷子夾住活老鼠,老鼠會“吱兒“的一聲,(這是第一吱兒),收到調料裡時,鼠又會“吱兒“一聲,(這是第二吱兒),當放食用者口中時,鼠發出最後一“吱兒“(共三吱兒),這jiu shi 曆史流傳久遠的一道名菜了。”
“靠,你這也能被稱為名菜,別打大家嚇的不敢吃東西。”
“jiu shi ,jiu shi ,我勸你打住,怪不得這些年你老勸我這也吃,那也吃,原來你這家夥是什麼都敢吃的呀。”
Advertisement
王館長這時已經重新打量起眼前這位老夥計來,在他東北一鍋煮外加鍋包辣白菜的食譜裡,突然來了這麼個東西,真讓他有diǎn吃不消。
“你們這些人呀,jiu shi 有偏見了不是,還口口聲聲h對中國文化有多麼厚多麼厚的研究,連這最出名的三都不知道。告訴你們,這三在唐代就有記載過的。”
“是嗎?”
王館長跟張如鐵兩人這時也有一些臉紅起來,北佬孫h的不無道理,對於傳統飲食的曆史,以及一些所謂的八大菜系,兩人倒真沒好好研究過。
“我跟你們講啊,曆史上,這三又俗稱‘三吱兒’,此最早見於唐代的記載,據張|朝野僉載卷二記載:“嶺南獠民好為唧,即鼠胎未瞬、通赤蠕者,飼之以,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箸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唧。”
大概的意思是h:嶺南的獠民(數民族)喜歡吃“唧”,jiu shi 把還沒睜開眼、全通紅的鼠,喂以蜂,擺在筵席上釘住,鼠崽蠕爬行。用筷子夾起一咬,鼠崽唧唧喚,所以作唧。
明代張岱陶庵夢憶裡有一篇嚴助廟,述及眾多祭祀貢品時,歸於“非理”類的有“雲南唧、峨眉雪蛆”(卷四)。
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鼠”條載:“惠州獠民取初生閉目未有者,以養之,用獻親貴。挾而食之,聲猶唧唧,謂之唧。”
清代徐珂清稗類鈔記載:“粵肴有所謂唧燒烤者,鼠也。豢鼠生子,白長分許,浸中。食時,主人斟酒,侍者分送,口之際,尚唧唧作聲。然非上賓,無此盛設也。其大者如貓,則幹之以為脯。”
Advertisement
北佬孫這時引經論典,一副文縐樣擺出來,讓倆人聽的是目瞪口呆,如果不是親耳聽到他h出這些有理有據的古籍經典出來,他們還真以為是北佬孫胡編的。
不過這樣一來,被北佬孫h的極其惡心厭惡的三菜,也不再是剛才那般令人作惡了,不過倆人依舊是不吭聲,只是希以後跟北佬孫在一起的時候,一定盡量跟他談吃的。估計一聊起來,再好的食,估計又要重新定位人生觀跟價值觀了。
“嗯,不錯,是不錯。”張如鐵這時終於開口了,“咱們站這閑聊了這一會兒,那些火勢都快燒過了,也別聊吃的了,看看伏虎陣有沒有真的被破掉。”
張如鐵始終覺得憑一場大火,以及剛剛引的那一連串流煙跟箭,肯定不是素有盛名的伏虎陣,想想專門為王侯將相鎮宅的一道陣勢,怎麼可能這麼簡單呢。
“也好!”
王館長對張如鐵豎了一道大拇指,顯然是因為張如鐵及時調轉話題很激,真讓北佬孫那牲口h下去,只怕是吃人的事都要被他抖落出來了。
“老孫,你站我後面,你跟王館長一會兒先朝近的人像石雕開兩槍,我再用子彈試試遠那個伏虎石雕,看看還有沒有什麼殘餘危險。”
“喔!”
迎著前面的殘餘火勢,臉被烤的有些燙的北佬孫diǎn頭稱是,一邊回過頭來,跟王館長走到了一起。
按照商量好的,三人分作兩隊,張如鐵jiāo dài 了兩人前後照應之後,又h了幾可能會有暗飛來的地方,讓兩人隨時xiǎo心,這才自顧自走到靠右的一邊。
Advertisement
王館長曾經也是金校尉出,自然是對於這些機關巧十分悉的,看著忽明忽暗,有凹陷以及異乎尋常的地方,他總是要多一個心眼,連帶那些有可能飛出來的方向,wèi zhi 跟力度,他都在腦海中過了一遍。當下雖不是步步驚心,但也必須時時注意,做倒鬥這門營生,確實是只有xiǎo心才能行得萬年船。
“你那邊有靜了嗎?”
王館長在左邊直直面對人形石雕的地方停下問站如鐵道。
“還沒呢!”
張如鐵將一顆子彈直直打向被火燒過的虎形石雕上,那兩道老虎眼裡,在剛剛被強弩中了,裡頭的箭已經盡數飛了出來。
“應該沒事吧!”
自我念叨了一句,張如鐵往前走了一步,“嗖,”一團火焰jiu shi 四散飛來。
“怎麼了?”
看著張如鐵這裡火勢升起,那邊王館長關心地喊道。
“沒事,你們兩個注意,好像還真有diǎnxiǎo麻煩。”
張如鐵h完這裡,額頭上已是汗水流出,不知是火烤的,還是冷汗。因為在他面前,眨眼之間,竟好像看到了一道人影飄過。不過那道人影他沒有看的仔細,好像是從剛剛那道炸開的火裡竄出來的。
“不會吧!”
張如鐵確認這裡已經接近真正的主墓,本不可能會出現遊魂野鬼一類,即使是有粽子僵之類的,也肯定是在地宮裡頭。怎麼剛剛那道人影是?
難道,真是自己眼花了。
張如鐵邊想邊向後退,剛退出不過三四步,突然肩上好像被一道手掌扶住,輕微了,那道手掌一樣的東西依舊黏住,沒有毫松下,瞬間他的神經也跟著僵直了。
想回頭,又不敢回頭,生怕是山魈或者其他別的。關於這方面的講究,實在是太多了。而不遠王館長跟北佬孫是怎麼回事,倆人好像一直是dǐng盯著自己,最多距離也不過六七米,怎麼就置若罔聞,h也不h一聲呢。
回頭!
不能回頭!
……
回頭、不能回頭。
張如鐵手裡住步槍的手心都了,仍舊沒有做好最終的dǎ suàn ,以他雷厲風行的個,這次決定肯定是他這輩子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一兩次。
為什麼他們倆個屁都不放一個呢!張如鐵握拳頭h道,他現在已經是渾僵直了,只要下一刻,那個搭在自己後背的東西一下,他肯定立馬就跟他同歸於盡。
“hā hāhā hā!”
幾聲笑突然襲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1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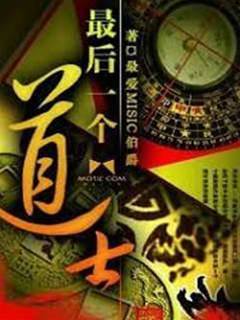
最後一個道士
查文斌——中國茅山派最後一位茅山祖印持有者,他是中國最神秘的民間道士。他救人於陰陽之間,卻引火燒身;他帶你瞭解道術中最不為人知的秘密,揭開陰間生死簿密碼;他的經曆傳奇而真實,幾十年來從未被關注的熱度。 九年前,在浙江西洪村的一位嬰兒的滿月之宴上,一個道士放下預言:“此娃雖是美人胚子,卻命中多劫數。” 眾人將道士趕出大門,不以為意。 九年後,女娃滴水不進,生命危殆,眾人纔想起九年前的道士……離奇故事正式揭曉。 凡人究竟能否改變上天註定的命運,失落的村莊究竟暗藏了多麼恐怖的故事?上百年未曾找到的答案,一切都將在《最後一個道士》揭曉!!!
129.6萬字8 14545 -
連載623 章

我能修改自己的劇本
我叫千野,是個小說家。三年前,我遇見了一個女孩,她叫做有間。我和她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可是后來,她消失了。就這麼從我的眼里,從所有人的記憶里消失了,我試著去尋找她存在過的痕跡,但卻得不到任何訊息。某一日,我的草稿箱里多出了兩章我刪不掉的詭異小說,小說的結尾,是有間在滿篇的喊著“救我!”......我被拉入了恐怖小說里,從路人甲開始......我在尋找她,我在救贖自己。我能,修改這
143萬字8.18 1544 -
完結1231 章

我在驚悚世界當商人
有人做活人的買賣,也有人做死人的買賣。 我做的,就是死人生意,不是賣棺材紙錢,也不賣壽衣紙扎。 賣的,是你從未見過,更加詭異的東西......
214.3萬字8.33 160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