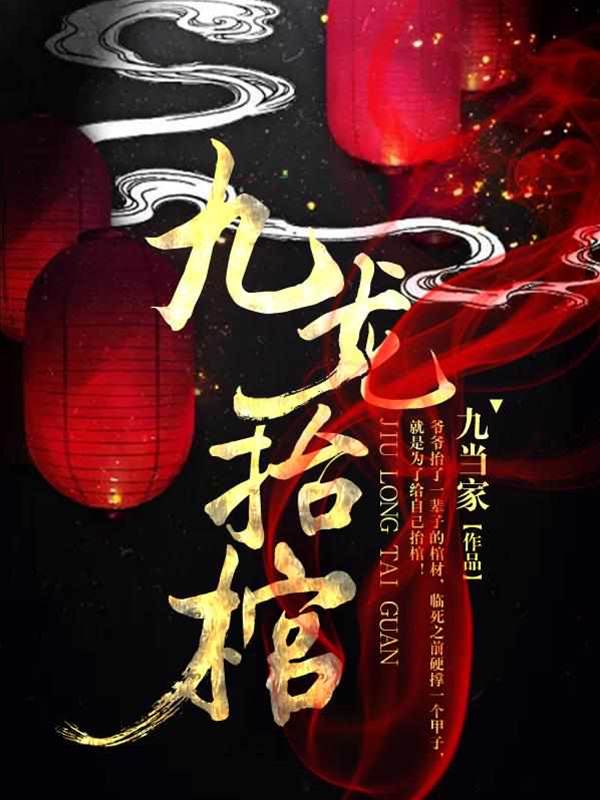《麻衣相師》 第162章 黑白雙煞
這沒頭沒尾把人也弄張,我就讓他直接說人話。
他越過我肩膀往後看了看,確實也沒看見什麼,這才小心翼翼的說道:「十二天階的玄家你知道嗎?」
玄家……是聽過一次,是上次馬元秋領著那幫武先生圍攻瀟湘的時候聽到的——說是玄家曾經在小葫蘆島發現了龍,去了八十個好手,結果被團滅了。
程星河點了點頭:「沒錯,就是那個玄家——玄家最出名的,是看兇風水。」
顧名思義,所謂的兇風水,是葬了先祖之後,會搞得家破人亡,甚至斷子絕孫的風水。
一般人都喜歡好地方,當然對這種風水避之大吉,可偏偏有的時候,一些先生或者老眼昏花,或者本事不到位,就把兇風水看好風水了。
好比說有一個富貴家族遷墳,當時也是一個宗師級人看的,找的是在兩座斜山之間,取其意為「白鶴亮翅」,鶴主吉祥,翱翔九天,平步青雲,葬在這裏,長輩長壽閑適,小輩仕途發達。
富貴家族當然十分滿意,重謝了宗師。
可是過了不長時間,宗師去世,而這家人也猛地就遭到了變故,先是仕途阻,棺場失利,被競爭對手強勢打,家族也出現了,到了自相殘殺的地步,可以說左右夾擊,幾乎真的要斷子絕孫——一直搞到了那個家族的小輩要被送到外姓人家裏寄養。
到了這個地步,也就只能凈等著滅亡了,可這個時候,玄家的當家玄一德到了他們家,說他們家壞就壞在祖墳上。
當時那個家族老輩都死絕了,小輩也不拿這個當回事,就一個小輩求他找找問題,玄一德這才告訴他,你們家祖墳一左一右兩個斜山,本不是白鶴亮翅,而是雙刀剖腹,主左右夾擊,自相殘殺,能得到好嗎?
Advertisement
小輩半信半疑之際,玄一德就指了兩地方,說你不信的話,可以找人看看這個土質。
真正的白鶴展翅,兩側應該是土質輕薄,隨風而起,可這兩個斜山,必有鐵礦。
小輩一查,果不其然,這就跪求玄一德想辦法,玄一德說這個好辦,但這兇風水,你得送給我。
小輩也不知道他們家要兇風水幹啥,但自己留著也沒用,自然就雙手奉上。
玄一德得了兇風水之後,給他在一個山谷,點了一個金盆育鯉生財地。
那地雖然稀鬆平常,但那家人遷墳過去之後,運勢立刻變好,一躍為全華夏都出名的製造商,每個人家裏幾乎都用得上他們家產的東西。
自此以後,玄家名聲大噪,玄一德也很快了天階。
這樣的事例不。他們家算是十二天階之中比較劍走偏鋒的一家,而他們名聲也很邪,還有人傳說,他們一家人看中的兇地,要是本地人不讓,那肯定活不了多長時間——因為他們既然擅長看兇風水,自然也擅長把好地改兇地。
所以到現在,只要知道他們家名號的,沒人敢得罪他們,也沒人知道他們家要兇風水幹啥。
雖然小葫蘆島上的事,搞得他們家元氣大傷,但越是這樣,他們家越有可能底反彈,報復社會什麼的,所以更沒人敢惹,生怕什麼時候自招了晦氣。
而那一對雙胞胎,就是玄家的一對雙胞胎孫子,也繼承了玄家兇狠暴戾的格,平時沒人敢惹——一個雙胞胎喜歡穿白,一個喜歡穿黑,表面人稱黑白雙煞,背地裏黑白無常。
這麼說,出跟烏一樣,是世家子弟。
而烏雖然歲數跟我們差不多,卻是個傻缺水貨,這倆難道跟他不同,是狠角?
Advertisement
程星河吸了口氣,低聲說道:「我可告訴你,這蒼蠅不叮無蛋,他們跟著咱們,八就是聞著味兒來的,依我看,是青龍局這麼一破,他們也想從中分一杯羹,找那個什麼真龍。」
跟馬元秋的目的一樣?
可真龍到底是個什麼鬼,為啥要通過我去找?
我就答道:「再怎麼說,也是小孩子,能翻起什麼大波浪。」
程星河一把捂住我的,左右看看,小心的說道:「你懂個球,他們倆本不是小孩子。」
我一愣:「啥意思?」
村民明明說是小孩啊!
正這個時候,白藿香所在的藥房忽然傳來了一聲尖,還有瓦罐之類破碎的聲音。
我趕跟程星河跑過去了,只見平時井井有條的藥房不知怎地,搞得一塌糊塗,而一個黑乎乎的影子蹭的一下從窗臺上溜走了。
程星河追上去看究竟,我沒他快,就看見白藿香握著一隻手——那手像是被燙了,正緩緩冒起一個大泡。
我也沒多想,立刻把弄了一個冰塊,敷在了手上:「怎麼了?」
白藿香搖搖頭,勉強說道:「是我自己不小心——進來了一個野貓,把罐子撞撒了。」
奇怪,這藥房平時不開門,因為葯的氣息,也沒有蛇蟲鼠蟻,貓來幹什麼?
這麼想著,我就在藥房裏四看,這一看不要,倒是看見房樑上有一個手印子的痕跡——房樑上常年沒人打掃的到,都是土,所以那個手印格外明顯。
「那個……」
我這才發現白藿香的臉紅了,反應過來,趕把手鬆開了:「無意冒犯,你沒事吧?」
白藿香正了正臉,才冷冷的說道:「你懂什麼,燙傷用冰,不管用,給我把涼甘拿來。」
涼甘……我順著的眼神,就登梯子爬桿的給找葯。
Advertisement
順便就看清楚了——房樑上纏著一團很長的人頭髮。
樑上寄發,那是剪不斷理還的意思——誰家房樑上有這個,家宅必。
有人要拿這個改這裏的風水——就是那兩個小孩兒?
我把那個東西取下來,沒聲,而白藿香則咳嗽起來:「還沒找到?」
我應聲找到了葯,回頭一看,眼角餘卻看見了白藿香角一勾,像是忍不住想笑——那是一種靈鬼馬,惡作劇似得笑容。
這跟平時那個冷冰冰的樣子完全不一樣,反而是明凈俏的。
人跟魔方一樣,還真是多面,誰能想到「見死不救」小鬼醫竟然並非面癱。
我拿了葯下來,白藿香的表早就冷下來了:「塗勻。」
俗話說吃人家,仰賴人家給我治好,這點也不難,我就幫仔仔細細塗勻了,抬起頭,盯著我,明靜如水的眼眸竟然像是在發獃。
但是一看見我抬頭,臉又冷了,飛快的回了手:「笨手笨腳,什麼事都干不好。」
說著又蹲下看著碎了藥罐子,出一臉惋惜,我就安,很重要的話,再熬一次?
回頭瞪我一眼:「你懂什麼?」
得,程星河說的沒錯,跟說話是跟拆彈似得,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炸。
我就了脖子,這會程星河回來了,說道:「誒嘿,這地兒竟然還有大猞猁,也不知道怎麼跑過來的。」
怕是那團髮引來的——那一對黑白雙煞,為什麼要盯著我們,又為什麼要壞我們的風水?
四相局,真龍……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不管是什麼,躲不過去,還不如勇敢面對。
做人,最怕的不是倒霉,是慫。
第二天,我們就應約去了土豪的那個鄉間別墅,臨走的時候,白藿香在門口摘藥草,我們走到時候,頭都沒抬,但我注意點,昨天給塗的葯,一直沒洗下去。
這玩意兒要敷很久嗎?
一路上程星河跟防賊似得,有意無意,總是回頭往後看。
不過一直也沒看到什麼,就到了地方。
到了山腳下,我就一眼看見了那個別墅,程星河孫悟空似得手搭涼棚:「這土豪是有錢——你說把材料搬到那麼高的地方,不說別的,人工就得費多大功夫,跟啞蘭家一樣,有錢就是任。」
不對……我卻看出來了,他們家別墅占的位置不對。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