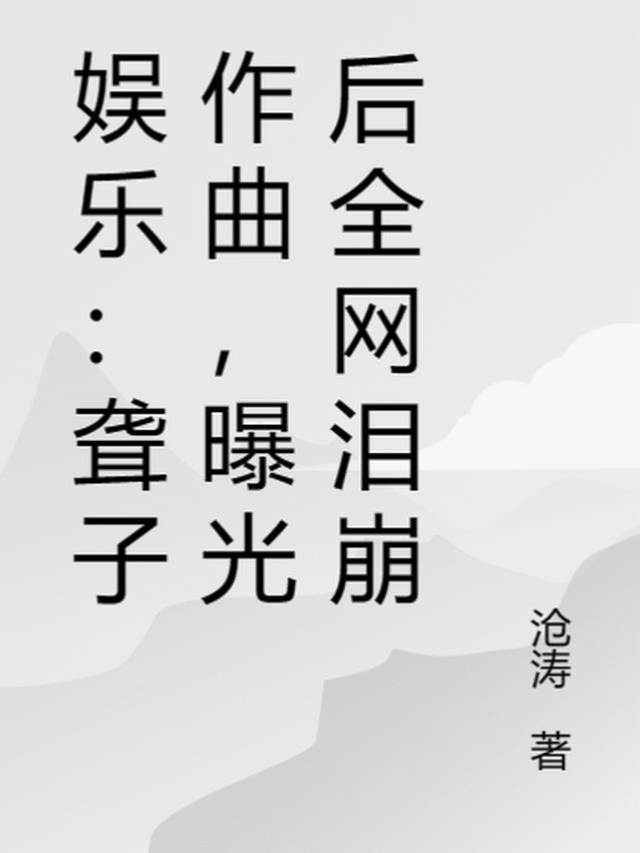《酷丫頭的貼身霸道總裁》 第63章 今夜,他又一次化身狼人
深呼吸,著窗外,舒服已經把窗簾給我拉上,這會兒隻能看到閃電似的忽明忽暗,對於外麵可能無比絢爛的煙花,這無疑很失敗。不過,我無心於煙花的繁華與否。我隻是擔心,我的監護人,這會兒,到底在哪裏,他究竟,有沒有事兒?
沒有答案,沒有辦法,我覺得,還是起來找找再說。有些辦法不是放在手上,而是在某個晦的角落,需要我們努力去尋找的。所以,為了不讓自己擔憂,我還是該起來找找。實在不行就拿家裏電話給他打一下。
看,才下床,就想到這麽好的辦法。不論可能有誰如何監聽,那家裏的電話撥打,總沒事吧?我欣的點點頭,發現一個真理:人還是得起來,才能得到好的結果。
曾聽過一個笑話,說男人人趴在一起等著生孩子,結果從年頭到年尾都沒有,後來請教高人,就有人給他指點:傻等是沒用的,得起來。
呃......好惡心,我怎麽想起這個來了?呸呸......
打開臥室門,客廳的燈開著,樓下也是亮的。難道,有人?我很懷疑。
趕回臥室,拿起我的刀子。再次出臥室,我安靜的站了一會兒,樓下似乎有靜。
看看殷亦桀的臥室,門虛掩著,一點燈,不亮,似乎是床頭燈開著。沒有運的聲音,沒有人的聲音,沒有任何聲音......
那麽,舒服呢?我第一反應,想到我們家還有個人。也許這不是我的家,這裏沒有我在家裏時那種明顯的安全。不過,舒服是在的,他在做什麽?
殷亦桀如果沒回來,他會怎麽做?難道也安靜的坐在臥室等著?
也許我該問問他,他一定知道況。他不大會騙我,而且剛才他的神很著急,一定有事兒。
Advertisement
“當......”
某個不知道的角落,傳來不怎麽悅耳的聲音,不知道是心被敲了一下,還是有東西掉到地上、、、
我忽然警覺起來。如果真的有人一直跟蹤我們,或者要謀害我們,隻怕我和舒服是對付不了的。家父混黑社會,我大致知道那些人的攻擊力,真要對付我們,那可太容易了。
手握著刀柄,這會兒沒有退的餘地,我應該勇敢一些,我可以的,因為,殷亦桀相信我。
把樓上大概看了看,聽一下,沒有異,我決定下樓去看看。
“妝小姐,您......還沒休息?”舒服安靜的出現在樓梯口,手裏端著杯牛。
我......點點頭,這個問題不用回答。
問題是,他怎麽也沒休息?
而且,他的神不大好。他手裏的牛,也明顯不是給我準備的。
我有非常明銳的直覺,觀察力也不差,雖然很用也缺乏鍛煉;但如果遇到很要的事,集中注意力,我還是可以發揮出來的。
舒服雖然看著依舊那麽安靜,和我說話也如常,端著牛,似乎正準備上樓。
但是,他的臉上繃;眼神有些閃爍;這會兒雖然上樓,但腳尖的方向朝外,正是急轉彎後的樣子。
而且,和我說話的時候,他的眼角在注意別的地方......
也許他平時也這樣,因為我很這麽注意的看一個人。
但今天不同,今天,我很擔心殷亦桀到底怎麽了,我想知道他究竟怎麽樣,所以,今天不論什麽事兒,我都會特別在意。
因為,他的牛太過明顯。家裏隻有我們,如果他以為我已經睡了,那他熱牛做什麽?
如果自己喝,端上來做什麽?
殷亦桀的臥室沒人,樓上,也沒別人......
Advertisement
簡單的判斷之後,我緩緩的抬,準備下樓看看。
“妝小姐,這麽晚,您該休息了......”
舒服繼續走上樓。
但他勸我的口氣,有點兒強。
生活每天每時每刻都在現場直播。
既然是現場直播,就算再出的播音員主持,也可能念錯臺詞說錯話。
和演員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NG重來一次的機會。
也許舒服自己都沒注意到,但是,他的這一舉,愈發出賣了他。
他堅持,我也不會退讓。
我做人有自己的原則。許多事求我也不會管,許多事再難也不能放棄。
我一向不管閑事,但今天的事,我不覺得是閑事,所以,我管定了!
“他呢?”我不想拐彎抹角,邊往下走邊問。
我其實一直都覺得自己是個大人了,這不是法律上有沒有年的界定,而是心理。
不過話問出口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還隻是個孩子,這種依和撒,很明顯。
深呼吸,我,接。
不過我可以依,但事還是要解決,因為,我不隻是個孩子。
舒服的態度和我一樣,或者相仿。
我一直往下,他依舊往上,旋轉樓梯上彌散著火藥味兒。
“殷爺還有點事兒,一會兒才回來。妝小姐,您......還是先休息吧。”舒服似乎也認同我並不是個傻子,所以,他的解釋,有點兒艱難,更多的還是大人式的強權。
他的口氣依舊很平靜,但眸子裏有種,有種……
很危險的氣息。
就是那種脾氣特好百年不發火的人,突然瞪直眼睛,會有一種特別讓人膽寒的覺。
甚至他的臉,也繃得很,牙咬。好像這危險來自於我,而不是別的什麽。
也有可能,我忽然變得這麽不聽話,讓他為難,也許他是該生氣。
Advertisement
可是,我不過想下樓看看,還沒做出什麽來,他憑什麽武斷的不許我下去?
就算我想出去看看煙花,大過年的,他也不能這樣對我。
不過這種辯解毫無意義,因為我們心裏都清楚,問題出在哪裏。
因為那個核心問題,正是我想知道而他又不想讓我知道的。
那麽,堅持的雙方,難免就要起衝突。
不過我沒想到的是,舒服為什麽會變得這麽危險?
難道還有什麽比我想象的更糟糕的嗎?
或者,比如說,呃......照電影裏的橋段,舒服是敵方的臥底?
所以這個時候他不想讓我知道況?
雖然是和諧社會和平年代,不過偶爾的還是會有危險,偶爾的還是有些不和諧的音符。這
個就不用多費口舌,因為我看過太多,包括殷亦桀上次被範老頭打傷。
如此說來,殷亦桀是有危險的,就是不知道什麽時候會威脅到他。
我一直不想細想,潛意識裏還是希他沒事。不過顯然現在他不可能沒事。
憑舒服的舉止,答案已經昭然若揭。
那麽,他到底到什麽傷害?
我,又該怎麽做?
舒服的腳步聲依舊那麽輕,踏著臺階,發出細微的悶響,一步步向我近。
我心裏也有一種細微的沉悶。也許,這會兒我不該堅持。
如果,萬一舒服真的是臥底,那我這麽做,是不是會讓他提高警惕,因此有所防備,削弱我有限的戰鬥力?
或者退一步來說,就算我這麽簡單的堅持,到底能不能見到殷亦桀?
我敵得過舒服嗎?
我想,應該不敵。
起碼我不能在毫無證據的況下捅他一刀,更不能確認,他有沒有幫手,在我捅他一刀之後跳出來將我製服,因此賠上我自己,將事弄得更糟。
所以現在使強很不明智。
Advertisement
暗暗搖頭,我呼了口氣,有些懷疑都這種時候了我還能泰然自若的理清思路。
不過我必須如此。殷亦桀肯定有事了,所以,我首先要保護好自己,然後再想辦法。
保護自己,我現在除了聽話似乎別無他法。
那麽,我就聽話,停下來,表明態度。
“他到底怎麽樣了?我擔心、、、、”
我的聲音有些抖,真的擔心。我想舒服早看出來了,所以沒必要編別的理由。
舒服眼皮重重跳了一下,腳下慢了半拍,一微不可查的歎息掠過,很快又恢複平靜。
他繼續上樓,不過口氣放鬆下來,說道:“朋友找他過年,稍微耽誤一會兒。”
可能見我沒,過了一會兒舒服又解釋道,
“以前殷爺一個人,過年總是和朋友一塊兒熱鬧。今年......況比較特俗,沒想到會變這樣......”
我安靜的站在那裏,看著舒服一個臺階一個臺階的靠近,然後,來到我跟前。
我已經卸去執拗,留下擔憂和依賴,無助的看著舒服,希殷亦桀安全會來。
“殷爺代,讓您先休息,下午......”舒服的話沒說完,聽著我跟前,安靜的看著我。
眸中有種說不出的,那種憂慮。
他的眼裏有種紅,似乎被煩擾了很久,甚至有點兒疲憊。
深深的憂慮,好像都是為我。
被我看久了,他竟然垂下眼瞼,不敢直視。
我想我明白了,所以我知道該怎麽去做。從他手上接過牛,我站在樓梯上就喝完了。
然後搖頭說:“他累了一晚上,回來先休息,下午的事兒再說吧。”
轉,我準備上樓,會自己臥室。
不用多說,樓下一定有什麽,我一定要想辦法下去,但不是現在。
停在臥室門口,著舒服下樓的略顯佝僂的背影,我說:“他回來了告訴我一下。我......要給他拜年呢。”
我似乎還沒這麽可以的說過謊話,沒想到還說得順口。
心下暗歎,不知道該喜還是悲?
舒服點點頭,繼續下樓、、、、
我回到臥室,悄悄的給我的手機定了鬧鍾,放進被窩。
然後又出一些茶葉,放進裏,幹咽了下去。
雖然聽說有心事的人會睡不好。
不過我喝了牛,又是第一次,麵臨的又是極重要的事,我要確保自己能醒來。
其實,最近這牛已經沒有以前那樣大的安定效果了。
我想,大概他們也不會給我用真正的強效安眠藥吧。
很多時候,我都極為懷疑這是出於某種神方麵的原因。也許開始是有一點的,可是後來,多半就是一種心理暗示了。
隻要在規定的時候一喝了牛,年心的我,就會睡得比較安穩。
後來我才知道,我第一天晚上在這裏睡覺,夜裏幾乎是低聲輕呤了一夜,惡夢不斷。
也許我一直如此,隻是沒人告訴我,我不知道而已。
躺在被窩裏,窗外的明明滅滅,有種在電影院看懸疑片時的覺。或輕或重的煙花竹炸響時的轟鳴聲,是或遠或近的人在喜慶新春的到來。
默默的盤算著,這裏有沒有我的新春。
恍惚中,有人推門進來,到我床邊看了一下。
不是殷亦桀的腳步,就算昏昏睡我也能聽得出來。
殷亦桀的腳步聲,就算再輕,也會有種特殊的力量,仿佛空氣在他腳下抖、臣服。
而這個腳步聲,輕微的猶如不存在,很有舒服一貫的風格。
嗬......一個人久了,不太和人流,我就轉了子換了習慣,開始揣度人的腳步聲、聲線、細微的作,還有潛意識的流等。
因此,就算閉上眼睛,我也能肯定,這個是舒服。
等舒服出去,我知道,應該差不多了。
但為了保險起見,我還得再等等。
大年初一淩晨二點,天地漸漸歸於寧靜,一年過去了,一年又來。
而我,還在苦苦的等候我的監護人。
不知道,他現在在哪個角落,我很想知道,他現在到底好不好?
世上並沒有黑暗,如果你的心是明亮的。
眸是最好的照明係統,在心的指引下,能於黑暗中找到前進的方向。
其實這個世界也還沒那麽黑暗。
甚至在都市中,已經沒有黑夜的存在,除非你拉上窗簾,將明嚴實的阻攔在外麵的世界。
或明或暗的路燈,無私的將輝灑向天地四方,供人用。
我沒有開燈,眼睛已經適應了昏暗的環境。
小心的關了手機鬧鍾。
心裏有事,我終於一直醒著,沒有用到它。
想來新年的第一課,就是能睡懶覺的除了累得半死,就一定是心裏無事。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919 章
強勢萌寶:爹地彆自大
傳聞,夜氏總裁夜北梟心狠手辣,殘忍無情。雖然長了一張妖孽的臉,卻讓全城的女人退避三舍。可是,他最近卻纏上了一個女醫生:“你解釋一下,為什麽你兒子和我長得一模一樣?”女醫生擺弄著手裏的手術刀,漫不經心:“我兒子憑本事長的,與你有毛關系!”夜少見硬的不行來軟的,討好道:“我們這麽好的先天條件,不能浪費,不如強強聯手融合,再給兒子生個玩伴……”五歲的小正太扶額,表示一臉嫌棄。
92.8萬字8 28955 -
完結1630 章

重生后,冷冰冰的大佬要把命給我
【團寵+爽文+玄學】前世慘死,重生歸來,戚溪一雙天眼看透世間妖邪之事。起初,戚溪,陸三爺懷里的小金絲雀,嬌氣的要命。后來,一線明星,娛樂教父,豪門大佬……紛紛求到戚溪面前:大師,救我狗命!陸三爺養了個又奶又兇的小嬌嬌,恨不得把自己的命都給她。“我家小朋友,身體不好,別惹她生氣。”眾人:“那個橫掃拳場,干翻全場的人是誰?”“我家小朋友膽子小,別嚇她。”眾鬼:“到底誰嚇誰?不說了,我們自己滾去投胎。”
147.4萬字8.67 559229 -
完結93 章

時光與他,恰是正好
最近年級突然瘋傳,一班那個季君行居然有個未婚妻。 一干跟季少爺自小相識的,打趣問道:阿行,你什麼背著我們偷偷藏了個未婚妻啊?季君行微瞇著眼,淡淡吐出四個字:關、你、屁、事發小立即起鬨的更厲害,大喊道:不否認那就是有咯。 終於,前面那個始終淡定的背影,有了反應。 喲,她耳朵根兒紅了。 文案二:全國高校比賽中,林惜被身穿比賽服的男人捉住,眾目睽睽之下,她黑色毛衣的領子被扯下,露出脖子上帶著的銀色鏈子,還有鏈子上墜著的戒指季君行看著戒指:你他媽戴著我送的戒指,想往哪兒跑?在年少時,遇到喜歡的人——《時光與他,恰是正好》【提示】1、傲嬌小少爺vs學霸小姐姐2、本文小甜糖,敲黑板強調,一切向甜看齊本文半架空,學校、人物均無原型哦——————————接擋小甜糖《黑白世界,彩色的他》,點進作者專欄,趕緊收藏一下吧。 文案:顏晗篇:作為手控的顏晗,一直因為自己常年做菜而有些粗糙的手有些自卑。 因為她一直想要找個有一對完美雙手的男朋友。 好友安慰她,男人的大豬蹄子有什麼好看的。 直到有一天,她在學校外面租的公寓對面搬來的男人來敲門。 顏晗看著他的手掌,心神恍惚。 端起自己剛做好的椒鹽豬蹄問:同學,要吃嗎?裴以恆篇:來體驗大學生活的裴以恆,在學校外面租了套公寓。 起初還好,漸漸,他有些煩躁。 因為對面每天做的飯實在太香了。 終於,有一天他忍不住去敲門。 門打開露出一張白嫩可愛的小臉時,他微怔。 而當她端起手中的椒鹽豬蹄問他吃不吃的時候。 嗯,他要娶她當老婆。
34.1萬字8 46732 -
連載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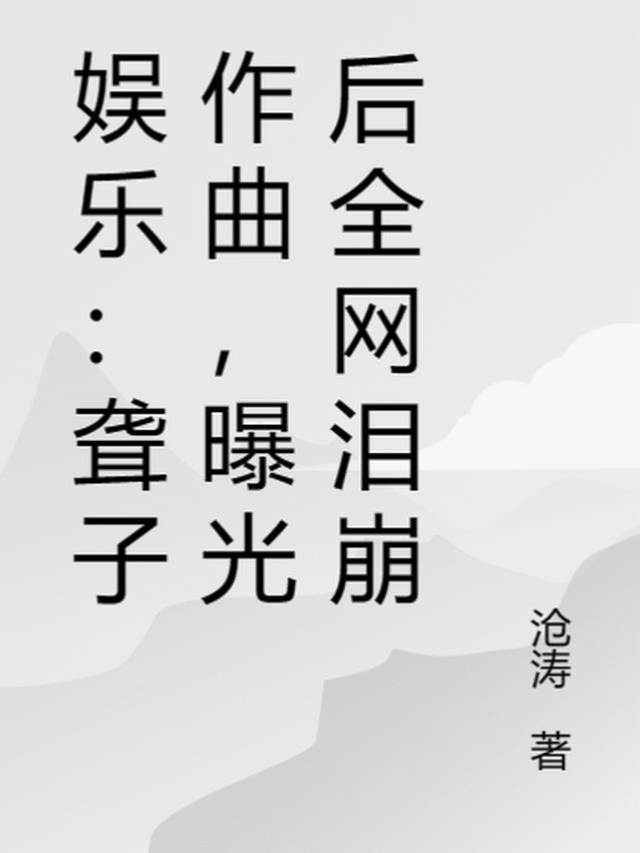
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
微風小說網提供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在線閱讀,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由滄濤創作,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最新章節及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就上微風小說網。
23.8萬字8.18 5622 -
完結1634 章

嫁給白月光,溫總寵妻上癮
溫珩是全城姑娘的白月光。所有人都說,楚寧嫁給他,是她單戀成真。婚后溫總寵妻上癮,高調宣布:“我只忠誠于我太太。”唯有楚寧清楚,所有恩愛都是假象。他待她毒舌刻薄,從來都不屑她。他寵她護她,只拿她當刀子使,成為他所愛之人的擋箭牌。離婚那天,她揮一揮手,決定此生再也不見。他卻掐著她的腰逼到角落,“楚寧,你真是這個世上,最薄情假意的女人!”直至她在雨中血流滿地,再一次被他棄之不顧。終于明白……在溫珩心里,她永遠只排第二。楚寧:“嫁你,愛你,我有悔!”后來,他丟下一切為愛瘋魔,“傷了她,我有悔!”
286.7萬字8 5107 -
完結90 章

陸總別虐了,沈小姐帶崽跑路了
和陸霆琛在一起三年,沈薇茗卻得知他已經有了未婚妻。她默默的捏緊孕檢單想要離開陸霆琛,誰料想,他卻想金屋藏嬌。“陸霆琛,牙刷和男人不可共用!”沈薇茗忍無可忍選擇遠走高飛,誰知,陸霆琛像瘋了一樣滿世界找人。他后悔,如果早點告訴沈薇茗這只是一場契約婚姻,結果是不是會不一樣?再見面時,她已不是陸霆琛身后唯唯諾諾的小姑娘。而a市也多了個八卦,據說向來不可一世的陸總被人甩了之后就得了失心瘋。
16.1萬字8.18 477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