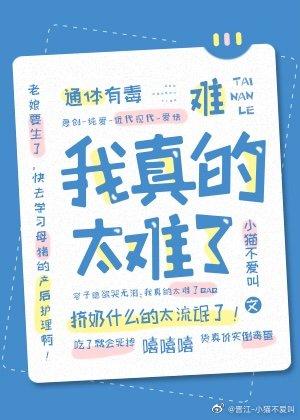《帝國第一妖豔主播[美食]》 第31章 縐紗餛飩(二更)
渝汐驚得猛地抬起頭,臉紅得像快要漿的櫻桃,邊搖頭邊支支吾吾地說:“、將,您,您怎麼……?”
話說到一半他自己都不好意思繼續往下說了,心中流下了悔恨的熱淚。能怨誰呢,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是踩了自己扔的香蕉皮,自作自了。
戎狄臉皮似乎頗厚,一點不好意思也沒有,坦坦地說:“我本來是不知道,但我手下的兵可是一個賽一個的八卦。還有不人是和你那大學裡的學生談著的,傳來傳去的,我想不知道也難啊。”
渝汐難為極了,小腦袋瓜飛速轉,尋找圓回去的辦法,“將,您千萬不要誤會。我這人就是心直口快,常常禍從口出,您千萬不要往心裡去,我只是……”我只是炮而已。
後半句話他剎住了沒說出來,但是那心虛的滴溜轉的小眼珠子早已出賣了他。
戎狄嚨裡溢出點低沉的笑,他明知渝汐是什麼意思,但還是忍不住想逗他,裝作一副通達理的樣子:“嗯,我明白,就和你說要我好吃到爸爸一樣的質對嗎?”
渝汐仿佛嚨裡卡了魚骨,不上不下的,憋得臉通紅。
怕真的把人逗急了,戎狄便最後了把年的發,說道:“走吧。”
戎狄帶著人從地下通道出來,繞開人群集的地方,直達到自己家。令渝汐驚奇的是,戎狄家裡居然更偏向中式風格,想必在這未來社會定是花了大工夫大數目來裝修的。
小小的驚歎一聲,渝汐對這裡拘謹的覺就放輕了些,覺更自在了。
應門掃過指紋滴的一聲打開了,戎狄領著人換鞋,一面朝裡說了聲“我回來了”。秋媽媽穿著家居服,無甚形象地倚在沙發裡用屏看時下最熱的偶像劇《曲》,笑得前仰後合,隨口應了一聲,看也不看一眼工作回家的親兒子。
Advertisement
戎狄無聲地歎口氣,提高了點音量再次說道:“汐汐來了。”
放肆的笑聲驟停,秋舒雅立馬一個鯉魚打端莊地坐起來,牽起一個溫的笑:“汐汐?你來啦,怎麼也不說一聲呀,阿姨穿得這麼不像話。”一邊說還一邊拿眼刀去剮木頭一樣的兒子,氣他不提前打招呼。
戎狄:“……”
渝汐趕說道:“不要的,夫人還是很。再說了現在都是大晚上的了,是我沒禮貌叨擾了。”
乖乖巧巧白白淨淨的禮貌小孩誰不喜歡呢,秋夫人一下子覺得自家不會說心話的冰塊兒子不香了,嫌棄地把他轟開,親親熱熱地想拉著渝汐去坐下。
戎狄不樂意了,人還是自己帶回來的呢,於是擰著眉,“媽,我還沒吃飯呢。”
秋舒雅納悶地回頭看他,“冷藏櫃裡不是還有很多營養嗎,自己去開一支。”
戎狄:“……”頓時覺自己的家庭地位下降了一級。
渝汐難得見戎狄吃癟一次,樂了,樂完還是幫著他說話:“夫人,今天戎將幫了我一個大忙呢,到現在還沒吃飯。我去給他做點東西吧,夫人一塊吃夜宵嗎?”
年的眼睛亮晶晶的,羽睫撲閃撲閃像兩隻翩翩飛的小蝴蝶,看得人心。秋舒雅捧住自己母泛濫的心窩窩,忙不迭點頭,把節食減計劃丟去九霄雲外了。
渝汐系上圍,踏進廚房環視一圈,工比自己家的似乎還全些,真不愧是副會長家的廚房呢。
他打開食材冰櫃看了看,有豬和,但剩的都不是很多了,還有一袋麵,和其他一些調味的東西。他有點訝異,怎麼食材這麼呀。
秋舒雅不太好意思地說:“戎狄他不怎麼吃我做的菜,天天就喝那營養,他爸工作更忙,常常在軍部吃了再回,所以我這邊也不常開火。食材也就準備的不是很多,不夠就算了吧,戎狄喝營養去。”
Advertisement
“大半夜的,怎麼這麼能作呢?”秋舒雅對自己的兒子一點也不客氣。
戎狄:“……”
秋舒雅為淨化師公會的副會長,本事肯定是有的,不過本不是在食材淨化這一塊最出眾。能量純度上是過得去,味道上對於口味極度挑剔的戎狄就有些勉強了,所以戎狄一般都是選擇喝營養的。
正因如此,那時他告訴秋舒雅他能吃天然食材的時候,秋舒雅才會那麼驚訝。
渝汐看現在的時間點不早不晚的,敲定主意做個縐紗餛飩。正好養生暖胃又適合做夜宵,不油不膩清爽飽腹。
縐紗餛飩是道江浙菜,是對吃食極為講究的江南人做出來的。縐紗,即織出皺紋的織品,而縐紗餛飩的面皮,自然就是輕薄帶皺的雅致手工小皮兒。這技,可極其考驗功力。
渝汐把等著吃的兩人哄出去讓他們坐著等就好,自己洗乾淨手準備做夜宵。
戎狄卻不肯走,靠過來說:“汐汐,你不直播嗎?”
渝汐一愣,覺得沒必要,想說算了。
戎狄輕笑:“你被帶走,雖然我們發了聲明,但是記者們見不到人,萬一發報道呢?”
其實他是說的,戎家發了聲明,哪還有膽大包天的記者敢寫。但渝汐那些真小們倒可能真的擔心的,事出到現在,他們還沒得到過關於渝汐的任何消息。最好的安的辦法,那就是直播了。
渝汐沒那麼多彎彎繞繞,一聽頓時覺得有理。可是他的手已經開始面了,現在就有些為難。
突然,一帶著雪原松木香的氣息靠過來,渝汐慌裡慌張地側頭看過去。戎狄分明的下頜線就近在眼前,他手臂一,替渝汐作起他的腦環,輕車路地點進了星網直播的主頁。
Advertisement
被男人侵略極強的氣息包裹著,渝汐說話都說不利索了,“謝、謝謝將……”
男人帶著點溫熱的下頜好似無意地過了渝汐的耳朵尖,若有若無地帶出一聲輕笑:“不客氣。”
然後一即離,他給渝汐的直播間開好了,自己走出了直播鏡頭的攝像范圍,懶懶地倚在門口。
【巡山小怪:渝汐!!你沒事吧!嚇死我們了,今天居然還能開一次播誒,好幸福哦。】
【加價不加量:汐汐的左耳朵尖怎麼那麼紅呀,右耳朵又不會,給小蟲子叮啦?】
【咕嚕:咦?沒見過的背景,汐汐是在哪呀?】
直播一開,關心他的觀眾就七八舌地問東問西。渝汐還在有點懵的狀態,索謝過大家的關心,然後說了句做夜宵,就不再回答什麼問題了。
戎狄還在後面看著,年另一側的白白淨淨的耳朵尖看著也很可口,弄得他也想把那邊也弄紅,這樣就對稱了。
渝汐還能覺到後灼灼的視線,現在左半邊子還有點麻,他不知道那是信息素製,隻覺得渾不自在。隻好可憐地回過頭,委屈求救般地看向戎狄,無聲地趕他走。
戎狄翹了翹角,如他所願出去待著了。他留下來就總想欺負小孩,忍不住做些耍流氓的事,實在辱沒帝國將這個莊嚴的份。
沒了搗的人,渝汐總算舒服多了,繼續面直至麵團,蓋上保鮮讓其靜置。
洗淨手,做餡心。
冰櫃裡的恰好是很適合的青蝦仁,青蝦仁的口比較爽脆,最適合拿來做餛飩、燒麥、蝦餃這樣的小點心。當然,拿來做腸裡的餡料也是很味的,鮮的蝦和這些的小玩意是絕配。
Advertisement
蝦子理乾淨,去殼去線,剁斜斜的粒狀。蝦仁是斷不可用菜刀去拍的,一拍,蝦脆弱的筋脈就很容易斷裂,Q彈的口就會下降很多。
切好備用,剁豬。這豬用的是前,又五花,這部分韌筋多,很適合做餡料,會相當有嚼頭。
依次下鹽、糖、白胡椒,順時針攪打餡至有黏合,這就是打出膠質了。期間加去腥去味的蔥薑水,接著攪。最後摔打幾次,上勁足夠,就是打好了。
混蝦仁粒、香油,提鮮提香。最重要的一步來了,做縐紗皮。
麵團已經餳好了,變了潔細膩的一塊彈麵團。渝汐找來一長湯杓,拆卸下杓頭,當做搟麵杖使用。
他的手變魔般,輕巧地將麵團搟了扁扁的長方形。然後是卷面皮,攤開,搟一搟,越搟越大,越搟越寬。反覆幾次,卷圓筒形,出杓柱,繼續按扁,再次攤開,便了更薄更輕的一張皮。
反覆三四番,面皮終於搟了薄如蟬翼的一大片。話說縐紗皮若是能,便是出師過關了;若能指,就是江湖手藝到位了;若能字,便是自一派,廚藝夠深了。
彈幕歎為觀止,彩虹屁不斷。
渝汐漸佳境,人自在了,話也開始變多,邊做邊教學。
【小邋遢:我靠,渝汐的面皮都能字了,好強!!!】
被一條彈幕一說,其他觀眾紛紛找起來哪裡有字。戎家的廚都是定做的,材質輕盈稱手又獨特,連這普通的案板也是專門定製的,上面均刻上了戎家的標志。
渝汐專注手法,都沒注意到突然山洪發式的彈幕——
【麻麻不麻:我看見了什麼!!!案板的左下角是不是有個字,是什麼字,彈幕的各位有沒有人能回答一下我怕我眼瞎看錯了!】
【方玉子:是戎字啊啊啊啊啊!!!】
【雲不喜:見家長這麼快就安排上了嗎?!雙廚狂喜.jpg】
卷最後的一次面卷,渝汐準備切出四方縐紗皮了,空抬眼看了一下彈幕,嚇得菜刀差點沒握住。
???
為什麼彈幕開始討論他和戎狄的婚期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77 章
天涯客
直屬於皇帝的特務機構「天窗」的首領周子舒,在厭倦了血腥生活后,自釘「七竅三秋釘」,帶著僅剩三年的殘命離開朝堂,下江湖游訪名山大川。本來悠閑自得的日子,卻因一時積善行德的念頭,捲入了一場撲朔迷離的江湖爭鬥中,還被酷愛「美人」的溫客行緊緊追纏、各種調戲。 傳說中的「琉璃甲」到底暗藏什麼玄機? 周子舒又能否從這場血雨腥風中保護憨厚的徒弟張成嶺? 迷一樣的溫客行反覆講起的貓頭鷹和紅水的故事,真的只是如同紅孩兒劈山救白蛇一樣的胡談亂編嗎?周子舒在三秋之後又是生是死? 故事從周子舒的角度來講述這場江湖武林的正邪之爭,其中有江湖遊俠暢遊五湖四海的浪蕩不羈,也有各門派之間挖空心思的相互排擠、打壓。在嬉笑怒罵的基調中,各種奇人怪事層出不窮,讓讀者欲罷不能。
23.6萬字8.18 6557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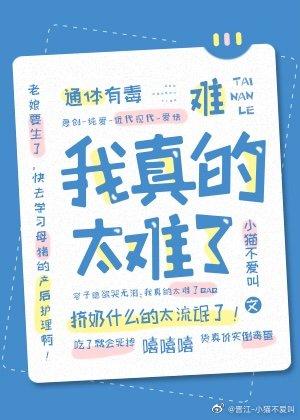
坑過我的都跪著求我做個人
容子隱是個貨真價實的倒黴蛋。父母雙亡,親戚極品,好不容易從村裏考出來成為大學生,卻在大學畢業的時候路被狗朋友欺騙背上了二十萬的欠債。最後走投無路回到村裏種地。迷之因為運氣太差得到天道補償——天道:你觸碰的第一樣物品將會決定你金手指方向所在,跟隨系統指引,你將成為該行業獨領風騷的技術大神。容子隱默默的看了一眼自己手邊即將生産的母豬:……一分鐘後,容子隱發現自己周圍的世界變了,不管是什麽,只要和農業畜牧業有關,該生物頭頂就飄滿了彈幕。母豬:老娘要生了,快去學習母豬的産後護理啊!奶牛:擠奶什麽的太流氓了!最坑爹的還是稻田裏那些據說是最新品種的水稻,它們全體都在說一句話:通體有毒,吃了就會死掉嘻嘻嘻。容子隱欲哭無淚:我真的太難了QAQ後來,那些曾經坑過容子隱的人比容子隱還欲哭無淚:我真的太難了QAQ,求你做個人吧!1v1,主受,開口就一針見血豁達受vs會撩還浪甜心攻注:1,本文架空!架空!架空!請不要帶入現實!!!文中三觀不代表作者三觀,作者玻璃心神經質,故意找茬我會掏出祖傳表情包糊你。2,非行業文!!!任何涉及各個行業內容,請當我杜撰!!!別再說我不刻意強調了,寶貝們~請睜大你們的卡姿蘭大眼睛好好看看我備注裏的感嘆號好嗎?內容標簽: 種田文 美食 現代架空 爽文搜索關鍵字:主角:容子隱 ┃ 配角:季暑 ┃ 其它:一句話簡介:我真的太難了
32萬字8 8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