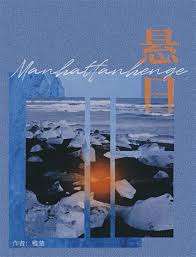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完了,少將彎了[星際]》 第151章
就這樣沉默的坐在地上,低垂著頭,淩的髮散落在的頰邊,讓顯得有些狼狽。
房間還是很安靜,年輕的將就這樣站在的前,仍舊是一言不發。
卻突然覺得很是無力。
繆特已經永遠地消失在的邊,就算像現在這樣遷怒,又有什麼意義?
“……他看到了你。”
塔紗說,的神已經變得平靜了起來。
“在你回來的那一天,在電視裏。”
平靜地將繆特說出的那句話轉告給了這個人。
“他說,抱歉。”
塔紗終於聽到了那個人開口說話,那個人的聲音帶著金屬的冷,低沉到給人一種無形的迫的地步。
那人說:“我不原諒。”
陡然之間,塔紗怒火上湧,猛地抬頭,怒視那人。
一抬頭,就和那人的目對視上。
而就在和那雙眼目相對的一瞬間,的口驀然一,張著,原本想要嘲諷而出的話竟是全部哽在嚨裏再也說不出口。
將站在前,俯視著,細碎的黑髮散落他的眼前,在他的眼窩裏落下深深的影,他的眼中像是有著裂開的冰封劍影。
他說:“不會原諒。”
男人再一次這麼說,轉離去。
轉的一剎那揚起的深披風邊角掠過怔怔地跪坐在地上的的鬢角。
“尤爾,送離開。”
“是!”
呆滯在一旁的警衛兵一驚之下立正應聲,他上前一步,抓住塔紗的一隻胳膊將其從地上強行拽起來。因為害怕這個孩又突然發瘋,他抓得很。可是他白張了,任由他拽起來,塔紗沒有任何掙扎,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茫茫然地被他拉出了門。
將那個推出大門,尤爾這才鬆了口氣。
Advertisement
他跟在後面也要走出門去,可是,就在他即將出門的那一秒,鬼使神差的,他回頭看了一眼。
線暗淡的會客廳裏,只剩下將一個人的影。
尤爾看見將又重新站在了那邊寬大的玻璃窗前,抬起的手按在上面。
他看見將微低著頭,額頭輕輕地在那冰冷的玻璃上。
突如其來一點微風,吹了細碎的漆黑髮,那額髮飛揚而起,於是籠罩在將眼窩上的髮的影也隨之掠過。
那一秒,尤爾看見了將的眼。
他的心臟劇烈地跳了一下。
他不知道那是因為什麼。
而來不及多想,他的前突然出現了狀況,原本安安靜靜地被他推著走出來的突然向前跑去。尤爾心一驚,立馬追了上去。
塔紗向前跑去,的腦子在這一刻一片空白,只有剛才和對視的那雙眼不斷在的記憶中閃過。
並沒有跑多久,只是跑了幾步就停了下來。
想是在逃跑,想要從那個男人的面前逃走,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抑,一種讓快要不過氣來的抑。
塔紗靠在金屬牆壁站著,呼吸急促,緩緩地著氣,靠著牆壁一點點地落在地上。
“……可惡……”
坐在冰冷的金屬地板上,神迷惘,慢慢地抬起右手扣了口,狠狠地、用力的,因為此時此刻的口深有一種讓幾乎無法呼吸的又酸又疼的覺。
坐在地上,仰著頭,大顆大顆的淚水從發紅的眼角掉落。
為什麼?
抬起手,捂住臉,發燙的淚水浸了的手指。
越是拼命用手去,偏偏掉得越多。
咬了牙,沒有發出一點聲音,可是控制不住簌簌掉落的淚水。
Advertisement
為什麼現實要這麼殘酷?
突然想起很久以前,還很年的看到的那個從水中走出來的年。
一漉漉的年低頭看著抱在懷中孩子的那一眼的溫。
那曾是記憶中最好的一頁畫卷。
【我不原諒。】
那個男人這樣對說,用那張面無表的臉,用那麼冰冷的口吻,還有那種殘酷的語言。
想應該憤怒、應該狠狠地反駁、嘲諷回去的,可是在和那個人的眼對上的那一刻,卻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想不該去看那個人的眼。
無法形容出那個人的眼神,只是知道,只要看到了那人那一刻的眼神,不管是誰,就再也不忍心再在那個人面前多說一句話。
…………
真正深骨髓的傷痛無需言說。
可是卻能讓所有人都看到。
哪怕是一無所知的旁觀者,也能清楚地看到。
…………
尤爾站著,看著抱著雙膝蜷著坐在冰冷的地面上無聲流淚的塔紗。他有些茫然,有些不知所措。
他在這一刻的心很複雜,在離開會客廳的時候,鬼使神差的,他回頭看了一眼。
那一眼,讓他的心臟劇烈地跳了一瞬。
他說不出來自己看到的那一眼的,可是他現在的心臟沉重得讓他莫名的到難。雖然他對於一切一無所知,可是他彷彿能明白眼前這個孩像是逃跑一般離開那裏之後失控流淚的理由。
……
那個時候,他看見將靜靜地站在窗邊,出的手按在冰冷的玻璃上。
他看見將的額頭輕在玻璃窗上,細碎的髮梢散落在眼前,撒下淺淺的影子。
在那額髮掠起的那一瞬間,在從窗外過來的星辰的微中,他看見了將看著窗外那顆藍星球的眼神。
Advertisement
他從未從將眼中看到過那麼的目。
他從未從任何人上看到那種明明如此卻讓人覺得像是在剜心的目。
【不會原諒。】
年輕的警衛兵還記得將說出這句話時語氣的冰冷。
可是尤爾覺得,或許他這一生之中,再也不會聽到比它更悲傷的語言。
…………
…………………………
我還在,你已沉睡。
當你醒來,我已化為塵埃。
若手無法及到你,那麼所謂的生離,與死別無異。
【抱歉。】
我不原諒。
…………
…………………………
在很久很久之後,終於有一天,冰涼的玻璃蓋緩緩打開,冷冷的白霧氣從玻璃櫃中噴湧而出。
白霧氣緩緩散開,出了被它籠罩著的蒼白得近乎明的年。
睫微微一,漆黑的眼緩緩在朦朧的霧氣中睜開。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09 章
情予溫寒
一個(偽)性冷淡在撞破受的身體秘密後產生強烈反應然後啪啪打臉的集禽獸與憨憨於一身,只有名字高冷的攻。 一個軟糯磨人卻不自知的受。 一個偽性冷、偽強制,偶爾有點憨有點滑稽的故事。 為何每個看文的人都想踹一jio攻的屁股蛋子? 面對“刁蠻任性”又“冷漠無情”舍友,他該何去何從?
25.9萬字8 38664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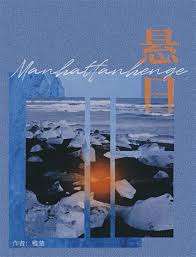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