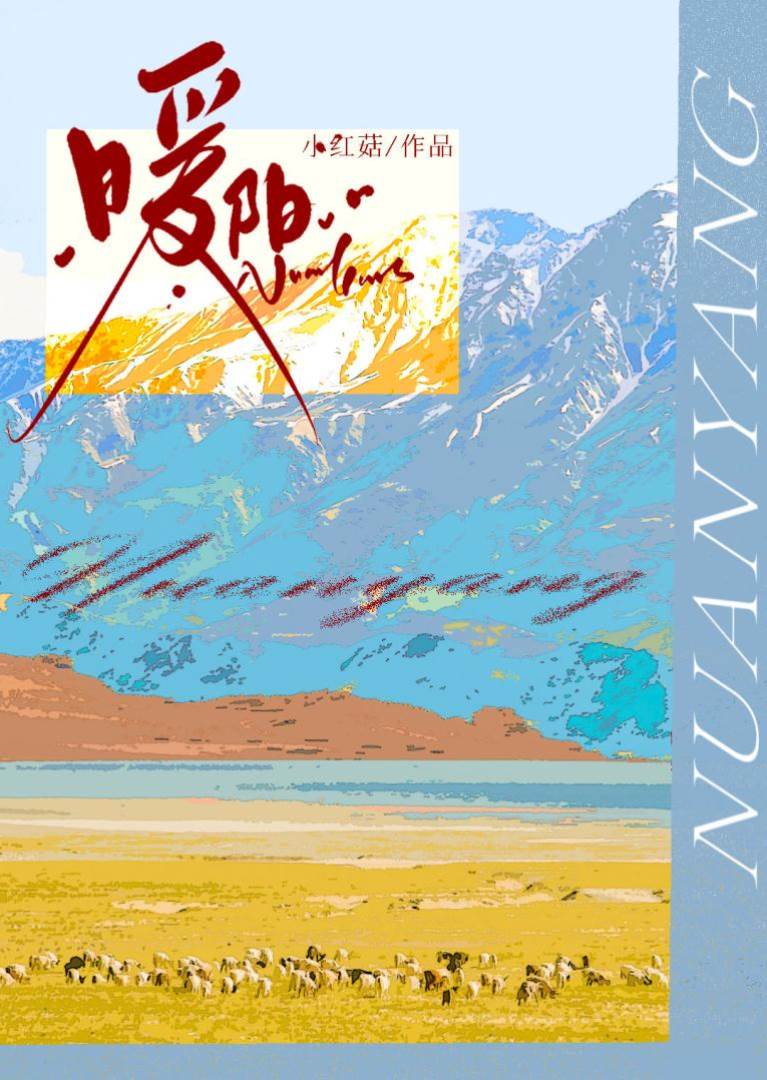《跪求老祖宗好好做人》 第一百七十章 0年前【二十七】遲時身上的謎團
“有點眼力勁兒嗎?”墨傾覺得跟他缺了點默契,略有些煩躁地提醒,“把袋子打開。”
“……”
見這般囂張,江刻無言半晌。
目在肩上頓了一瞬,江刻彎腰拾起那個藥袋,打開綁起的結,把裡面的品一樣樣拿出來,擺放在墨傾側的桌上。
“撕拉——”
忽而聽到布料扯裂的聲音,江刻愕然側首,便見墨傾撕開了服,出了雪白的肩膀。
銀發襯著香肩,莫名的香豔。
江刻將視線移開。
“又不是第一次看了。”墨傾閑閑地說,用腳尖了他的,“搭把手,拿點棉球。”
頓了下,江刻將包裝袋撕開,拿出棉球。
不過,等墨傾手去接的時候,被江刻躲過去了。
想到墨傾這個軍醫暴的手法,沒準能做出棉球塞傷口裡止的作,江刻眉微微一,說:“我來吧。”
墨傾質疑地打量他一眼:“你會嗎?”
江刻說:“反正比你細心。”
墨傾嗤笑一聲。
但是,將手收了回去,大剌剌地坐了回去,等著江刻幫忙。
江刻理論基礎扎實,理墨傾這點刀傷,還是綽綽有余的。
他有條不紊地清理著傷口。
同時,他觀察了下墨傾淡定的神,問:“不疼嗎?”
“疼。”
墨傾氣定神閑地回答。
江刻質疑地掃了一眼。
上說著疼的墨傾,還有心思同江刻閑聊:“你把他扔哪兒了?”
江刻眼眸一垂,專心理傷勢:“我房間。”
墨傾頓了下,說:“對他好點兒。”
聽到這話,江刻心裡稍有不快:“還沒證實他是原裝的呢。”
什麼都沒確定,就開始護犢子了。
墨傾懶得跟他辯,隻說:“是不是,都對他好點兒。”
Advertisement
作一停,江刻斜乜著。
江刻冷聲提醒:“他想殺你。”
“他又不認識我——”墨傾一說完,就覺肩上傳來劇痛,眼皮一挑,瞪向江刻,“你能不能輕點兒?”
“知道疼了?”
江刻涼聲反問一句,但手裡的力道明顯輕了些。
“他是個孤兒,被江延撿了後,一直待在邊。”墨傾緩緩道,“脾氣怪的,但一心護主。他把你當江延,以後會你一大助力的。”
“什麼助力?”
墨傾稍作停頓:“他會用命護著你。”
默了一瞬,江刻淡聲道:“這年代,已經不講究那一套了。”
墨傾眼裡閃過抹驚訝,爾後,半垂著眼簾,不再說話了。
江刻這話,倒也不錯。
對於百年前的他們而言,在這個時代,已經是被淘汰的老古董了。
井時唯一的願,就是護著江延。
哪怕犧牲命。
而現在,這種決心已經沒用了,因為沒有什麼機會,需要讓人“付出命”。
“他失憶的況,似乎跟我不一樣。”江刻忽然說。
墨傾看著他。
江刻條分縷析:“他跟戈卜林口中的遲時,長得一樣。如果是一個人,那麼,這事就很複雜了。”
墨傾頓了幾秒,同意:“嗯。”
如果真是同一人,“遲時”連戈卜林都不認識了,那麼,“遲時”有可能是這幾年才失憶的。
這也可以解釋,“遲時”為何活著,卻沒有回第八基地。
可,如果是這樣的話……
“遲時”活到現在的方式,大抵跟江刻的並不一樣。
墨傾懶得細想,直接說:“先送回去核對一下份吧。”
江刻沒再吭聲,細致地理著的傷口。
包扎好後,江刻站起,問了一句要的:“以你的,多久能恢復?”
Advertisement
墨傾沉了下:“幾天,不好說。”
雖然時常手,但真正傷的況,不多。
而且,真要傷的時候,都是重傷,沒個個把月,活不過來。
江刻微微頷首。
他將藥都收起來:“夏天容易發炎,你記得每天換藥,這幾天就不用沾水了。”
“……”
墨傾恍惚了一下。
好家夥。
差點忘了自己才是個醫生。
半晌後,墨傾應了聲:“。”
江刻又停了會兒,最後,他將敞開的窗戶關上了,回說了句:“我走了。”
墨傾頷首,繼而叮囑:“問到什麼,跟我說一聲。”
“嗯。”
墨傾忽而提醒:“對了,重點問一下他今天下毒的事。”
江刻有些疑。
墨傾說:“他那毒,由我所創。我記得,在寫那些配方時,他正好在我邊陪著,是看過的。他若是自己配出來的,十有八九是井時。”
“……”
江刻一時不知該吐槽誰。
他回了一聲“嗯”,便離開了。
*
江刻回到自己房間。
一開門,就見到跟門神一樣站著的遲時,眼皮跳了一下。
“江先生。”
遲時朝江刻點頭。
江刻瞥了眼他袒的上半,擰眉:“你服呢?”
遲時低頭,掃了眼自己才說:“忘了穿。”
他是洗澡時,忽然發現外面有人盯梢,沒來得及穿上,就跑了出來。
江刻往裡走,從包裡找到一件黑短袖,扔給了遲時。
遲時接住,遲遲沒,而是看向他。
江刻頭疼地了下眉心:“穿上。”
“哦。”
遲時這才反應過來,乖乖將短袖套在自己上。
他們倆高差不多,遲時穿上江刻的服,還合的。
江刻拖出一張椅子,坐下,問:“你什麼時候來的青橋鎮?”
Advertisement
“幾天前。”
“為什麼來青橋鎮?”
“不知道。”
剛開始問,就來了這麼一答案,江刻眉了下。
爾後,他繼續問:“不是為了劇組?”
遲時回答:“不是。”
頓了須臾,江刻繼續說:“你來這裡,總得有個理由吧。”
“不知道。”遲時答時眉頭輕擰了下,“覺在這裡,能找回什麼。”
這回答,跟不答,沒什麼兩樣。
江刻耐著子繼續問:“為什麼針對劇組?”
“不知道。”
“……”
遲時看著江刻的臉,又補了一句:“覺不能讓他們拍下去。”
直覺。
又是直覺。
江刻便道:“把你向劇組做的事,全說一遍。”
遲時停頓著,似乎是組織了下語言,然後才將他的行,一一詳細說出。
他來到青橋鎮沒兩天,就聽人說起這個劇組,本來沒放心上,但無意間得知劇組拍攝的劇和故事原型。
雖然沒有據,但他很明確的知道,這故事不能被拍出來。
於是,他開始干擾劇組拍攝。
導致男主演差點摔下樓的欄桿,是他的手腳。
墨傾吊的鋼忽然斷裂,也是他的手腳。
後來的花瓶,也是他扔的。
那晚向楚泱泱下手的,也是他。
至於今天的“毒”,也是他在附近山上找到草藥製作出來,放進水裡的。
聽到這裡,江刻想到墨傾的提醒,問:“那毒的配方,你是從哪兒弄來的?”
遲時停頓了下,說:“我記得配方。”
江刻瞇了下眼:“記不得從哪兒學的?”
遲時點了點頭。
不該忘的,全忘了。
該忘的,一點沒忘。
最後,江刻問:“你是什麼時候認出我的?”
“今天。”遲時回答,“我在路上見過你。”
Advertisement
但是,當時遲時沒同他相認。
本來決定晚上來找江刻的,但發現了上沾的末,便準備洗個澡,結果出現了意外。
聽完,江刻問:“你失憶了,忘了所有人,唯獨記得我?”
遲時點頭。
“墨傾呢?”
遲時搖頭。
江刻又問:“你的記憶,最早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
遲時回答:“五年前。”
對上了。
遲時、聞半嶺、戈卜林在燕城出現意外,正是五年前。
……
第二天一大早,江刻來敲墨傾房間的門。
墨傾有起床氣,開門時,一的火氣,但是,在見到江刻後,忽而意識到什麼。
沒衝江刻發火。
而是安靜地看著江刻。
江刻問:“吃早餐嗎?”
“吃。”
墨傾吐出一個字。
回了房間,花了幾分鍾洗漱,也沒怎麼整理著裝,頭髮抓了兩下,穿著一件睡,就跟江刻出了旅店。
哪怕是這樣,路上還遇到幾個衝吹口哨的。
不過,江刻眼神一掃,無人敢造次。
“睡得怎麼樣?”江刻似是沒話找話。
“啊?”
墨傾沒能明白。
江刻眉頭輕皺,換了個問話方式:“你的傷,會影響睡眠嗎?”
“哦。”墨傾掃了眼肩膀,“昨晚有點兒,現在已經不疼了。”
江刻領著墨傾進了一家早餐店。
墨傾有傷在,但隨意慣了,沒放心上,但江刻卻無形中關照到極致,給拖椅子、端早餐,甚至連筷子都提前給掰開。
細致微。
墨傾拿著筷子,看著,有些失神。
江刻一瞧,就莫名來氣,將自己筷子一掰:“個傷,就忘了怎麼吃早餐了?”
墨傾忽然被他一嗆,張口就回:“你會不會說話?”
“不會。”
江刻氣得很,將醬油放到墨傾跟前時,力道都重了些。
墨傾左手傷,右手拿筷子,瞧了眼醬油,理所當然道:“你給我倒。”
江刻起眼皮:“求我。”
“……”
墨傾眼裡冒氣一火,“你莫不是想死”這句話,已經寫在瞳孔上了。
僵持三秒,在墨傾要自己拿醬油時,江刻忽然出手,一把抓起醬油。
墨傾抓了個空。
江刻心頗好地給墨傾倒醬油。
墨傾咬著牙:“大清早的,你別給自己找啊。”
“正好,給我試試新保鏢。”江刻毫沒放眼裡。
墨傾:“……”
給他臉了!
不過,過了幾秒,墨傾又釋然了。
雖然偶爾,會從江刻上見到江延的影子,可多數時候,都是江刻玩“角扮演”的時候。
江刻本玩世不恭,隨散漫,跟後來的江延沒一相似。
算了。
墨傾將念頭拋在腦後。
“他人呢?”墨傾用筷子攪和著米,低頭吃了一口。
“讓他先回去了。”江刻說,“留了個他的聯系方式。”
墨傾繼續問:“你問出了什麼?”
二人一邊吃米,一邊聊天,把昨晚掏出的消息,都一一同墨傾說了。
沒有毫瞞。
墨傾喝完最後一口湯:“所以說,他確實是井時,又是遲時。”
“嗯。”江刻頷首,“再來點兒嗎?”
“不用。”
墨傾吃飽了。
只是不浪費糧食。
“有一點,我沒搞明白。”江刻說。
“什麼?”
“按理說,遲時在基地工作多年。以戈卜林的記憶,遲時最起碼十年前就在基地待著了。”江刻問,“他為什麼看起來這麼年輕?”
“……”
墨傾手一僵。
仔細一想,記憶中的井時,跟現在的遲時,也長得一模一樣。
墨傾忽而打量起江刻來:“你呢?”
江刻強調道:“我很正常。”
他醒來三年。
雖然差別不大,但長相仍是有細微變化的。
墨傾盯著他的臉看了半刻,最後點點頭,表示同意江刻的說法。
“這就是我想跟你說的。”江刻道,“他被帶回基地,待遇極有可能跟你一樣。但是,他待在基地,應該比外面更安全。”
江刻將選擇權給了墨傾。
“你對基地很悉啊?”墨傾狐疑地問。
記得,最初跟江刻說“第八基地”時,江刻是一無所知的狀態。
江刻不答,只是等的答案。
過了好一會兒,墨傾說:“先不上報。”
一想到剛醒來時,被基地各種檢查的經歷,以及這一年的各種報表、監督,就覺得頭疼。
“嗯。”
江刻似乎一點都不意外。
江刻又說:“我會讓他去帝城找我。”
墨傾點頭:“好。”
二人聊到這兒,這頓早餐也算是結束了。
他們倆一同回旅店。
結果,一到門口,就見到在等待的宋一源和戈卜林。
“你們倆起的可夠早的。”宋一源抓了下頭髮,隨後關懷了下墨傾,“你的傷怎麼樣?”
墨傾道:“無礙。”
爾後,墨傾看向戈卜林。
跟相比,戈卜林就慘多了,臉上青腫尚未消退,俊俏的臉蛋上,了好幾個創口,上也纏繞著繃帶,手被吊起來了。
傷得不輕。
墨傾抬手去口袋,發現自己穿得是一件睡,沒口袋,便同戈卜林道:“你待會兒從我那兒拿一瓶藥膏,外用的。”
“好。”戈卜林心思不在這上面,敷衍一應,就忙著問,“他呢?遲隊長呢?”
墨傾說:“他跑了。”
戈卜林:“啊?”
宋一源:“有你在,他怎麼跑的?”
墨傾反問:“贏我不容易,跑還不容易?”
宋一源:“……”說得有道理。
“那怎麼辦?”戈卜林急了。
他心道:早知道你們這麼不靠譜,就不把人給你們了。
接著,戈卜林道:“我知道他住哪兒,要不要去看看!”
“他不在了,已經離開青橋鎮了。”墨傾說,“你們收拾一下,我們九點離開。”
“這就走?”
戈卜林哪裡能甘心, 要跟墨傾好好一說。
可是,宋一源一直沉默旁觀著,在這時候,卻拉住了戈卜林。
宋一源勸他:“既然他還活著,肯定會遇到的。”
戈卜林有些不甘心。
可,無可奈何。
題外話
除夕快樂,新年快樂。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638 章
新婚嬌妻寵上癮
(桃花香)一場陰謀算計,她成為他的沖喜新娘,原以為是要嫁給一個糟老頭,沒想到新婚之夜,糟老頭秒變高顏值帥氣大總裁,腰不酸了,氣不喘了,夜夜春宵不早朝!「老婆,我們該生二胎了……」她怒而掀桌:「騙子!大騙子!說好的守寡放浪養小白臉呢?」——前半生所有的倒黴,都是為了積攢運氣遇到你。
245.9萬字8 30971 -
完結256 章

別和我撒嬌
痞帥浪子✖️乖軟甜妹,周景肆曾在數學書裏發現一封粉色的情書。 小姑娘字跡娟秀,筆畫間靦腆青澀,情書的內容很短,沒有署名,只有一句話—— “今天見到你, 忽然很想帶你去可可西里看看海。” …… 溫紓這輩子做過兩件出格的事。 一是她年少時寫過一封情書,但沒署名。 二是暗戀周景肆六年,然後咬着牙復讀一年,考上跟他同一所大學。 她不聰明,能做的也就只有這些了。 認識溫紓的人都說她性子內斂,漂亮是漂亮,卻如同冬日山間的一捧冰雪,溫和而疏冷。 只有周景肆知道,疏冷不過是她的保護色,少女膽怯又警惕,會在霧濛濛的清晨蹲在街邊喂學校的流浪貓。 他親眼目睹溫紓陷入夢魘時的恐懼無助。 見過她酒後抓着他衣袖,杏眼溼漉,難過的彷彿失去全世界。 少女眼睫輕顫着向他訴說情意,嗓音柔軟無助,哽咽的字不成句:“我、我回頭了,可他就是很好啊……” 他不好。 周景肆鬼使神差的想,原來是她。 一朝淪陷,無可救藥。 後來,他帶她去看“可可西里”的海,爲她單膝下跪,在少女眼眶微紅的注視下輕輕吻上她的無名指。 二十二歲清晨牽着她的手,去民政局蓋下豔紅的婚章。 #經年,她一眼望到盡頭,於此終得以窺見天光
45.4萬字8 21446 -
完結1693 章

離職后我懷了前上司的孩子
作為總裁首席秘書,衛顏一直兢兢業業,任勞任怨,號稱業界楷模。 然而卻一不小心,懷了上司的孩子! 為了保住崽崽,她故意作天作地,終于讓冷血魔王把自己給踹了! 正當她馬不停蹄,帶娃跑路時,魔王回過神來,又將她逮了回去! 衛顏,怒:“我辭職了!姑奶奶不伺候了!” 冷夜霆看看她,再看看她懷里的小奶團子:“那換我來伺候姑奶奶和小姑奶奶?”
165.2萬字8.18 38138 -
完結201 章

雙時空緝兇
【01】南牧很小的時候就遇到過一個人,這個人告訴他:絕對不要和溫秒成為朋友。 日長天久,在他快要忘記這件事的時候,他遇到了一個女生,那個女生叫做:溫秒。 【02】 比天才少女溫秒斬獲國內物理學最高獎項更令人震驚的是,她像小白鼠一樣被人殺害在生物科研室,連頭顱都被切開。
38萬字8 179 -
完結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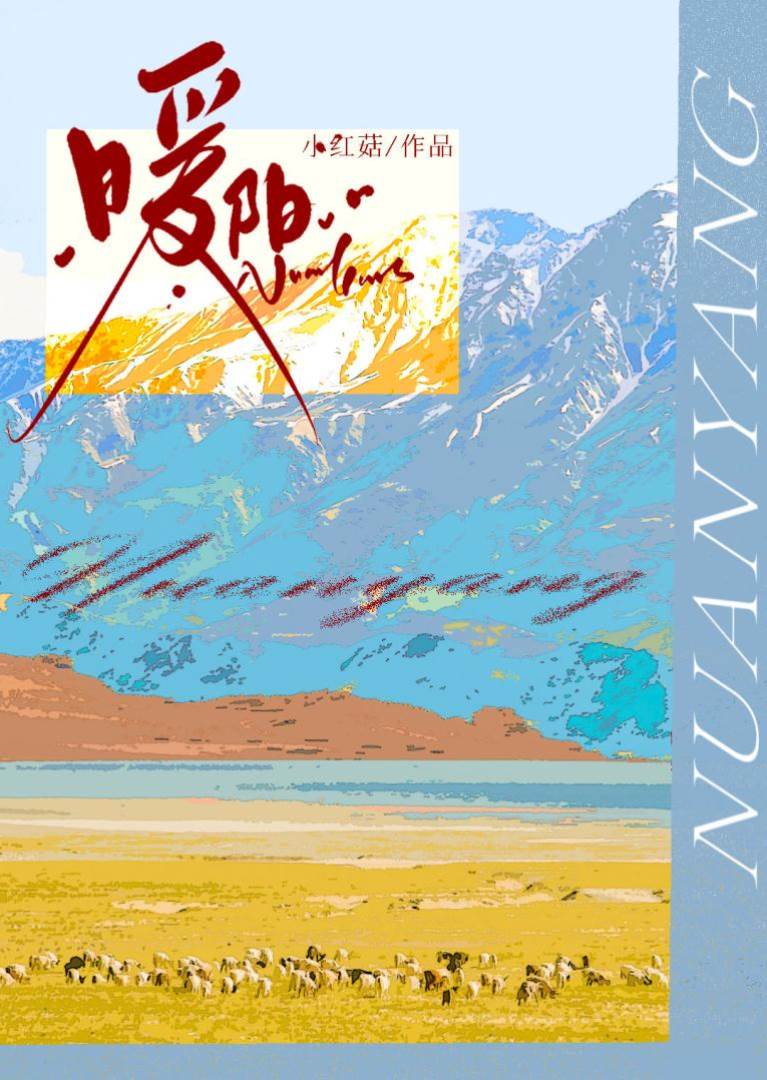
暖陽[先婚後愛]
文冉和丈夫是相親結婚,丈夫是個成熟穩重的人。 她一直以爲丈夫的感情是含蓄的,雖然他們結婚這麼久,他從來沒有說過愛,但是文冉覺得丈夫是愛她的。 他很溫柔,穩重,對她也很好,文冉覺得自己很幸福。 可是無意中發現的一本舊日記,上面是丈夫的字跡,卻讓她見識到了丈夫不一樣的個性。 原來他曾經也有個那麼喜歡的人,也曾熱情陽光。 她曾經還暗自竊喜,那麼優秀的丈夫與平凡普通的她在一起,肯定是被她吸引。 現在她卻無法肯定,也許僅僅只是因爲合適罷了。 放手可能是她最好的選擇。 *** 我的妻子好像有祕密,但是她不想讓我知道。 不知道爲什麼他有點緊張,總覺得她好像在密謀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卻無法探尋。 有一天 妻子只留下了一封信,說她想要出去走走,張宇桉卻慌了。 他不知道自己哪裏做得不夠好,讓她輕易地將他拋下。 張宇桉現在只想讓她快些回來,讓他能好好愛她! *** 小吳護士:你們有沒有發現這段時間張醫生不正常。 小王護士:對,他以前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不發朋友圈的,現在每隔幾天我都能看到他發的朋友圈。 小吳護士:今天他還發了自己一臉滄桑在門診部看診的照片,完全不像以前的他。 小劉護士:這你們就不知道了吧,張醫生在暗搓搓賣慘,應該是想要勾起某個人的同情。 小王護士:難道是小文姐?聽說小文姐出去旅遊了,一直還沒回來。 小劉護士:肯定是,男人總是這樣的,得到了不珍惜,失去了纔會追悔莫及。
22.5萬字8 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