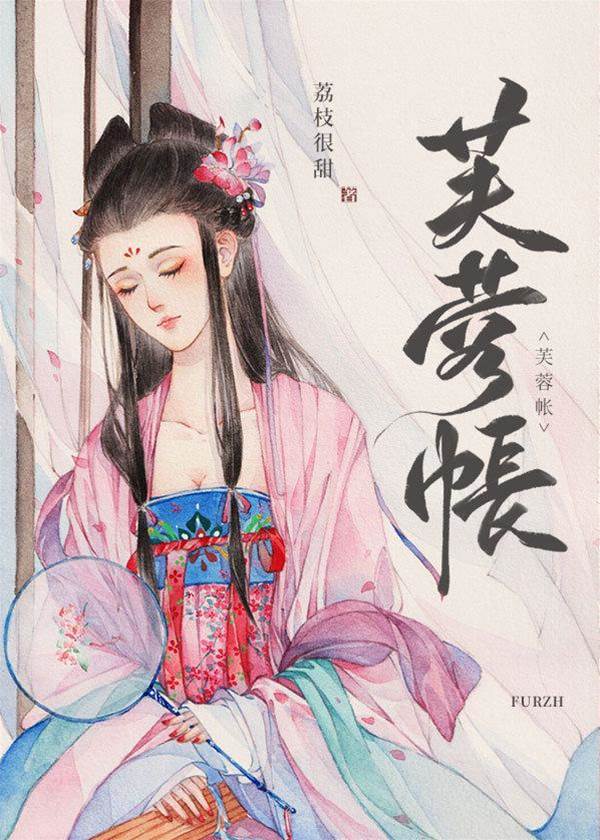《正妻不如妾ll》 六 籠中鳥
是夜,滿地歸去自己的房中,周媽見一狼狽回來,趕忙送上暖手的爐,不噓寒問暖,扶著坐在銅質地的臥榻,一番下來卻見面上如常,半晌終於晃過神來,淡淡地覷著周媽,那眸中竟無半亮,只聞聲音從中吐出:“晚晚呢?”
那是留學歸來,費了好大的周折人由渡帶回來的波斯貓,本是在法蘭西時室友的,只是室友時常不在,又因在新年舞會上不小心扭傷了腳踝休養在宿舍中,常常與晚晚相伴,竟也生出了些許,猶記得要回國的那幾日,晚晚才不到一歲,小小的懶懶的子,瞇著波斯貓特有的鴛鴦眼,日日伏在的腳邊,挨著。本就不是寂寞的人,那幾日不得而出,便與說說話,喂喂,抱著像抱著暖爐,明晰時常想,若不是上一個人,便要和晚晚過一生,即使貓的壽命不及十幾年,亦終會珍惜。
當年最後不得已,眼見得與晚晚難分難舍,晚晚又整日沖著喚不停,那親昵勁倒像足了人,誰都不忍心將與這貓分開,於是室友只得割讓出。
晚晚很乖,喜靜,有一對漂亮而眸均勻的鴛鴦眼,很,往日只懶洋洋地趴在的貴妃椅上,久久不,如今倒連它都不見了影,心下不覺有些揪心,面上雖無任何不對,只是嚨略有些幹,舌苔泛。
正想著,只聽見一聲尖細的聲,窗口落下一個一團白雪,那貓步步優雅,剔亮,瞇著鴛鴦眼,眸如天燈。
明晰心下一舒,手一,它一懶腰賴在懷裡撒,細聲喚著。
周媽覷著明晰神有些松緩下來,頓時舒了口氣,只打趣道:“這貓想是同隔壁姚公館家的那只貓玩耍回來的吧。”
Advertisement
“姚公館家的貓?”
“是呀,聽聞是姚四公子從洋人那兒花大價錢買來的,晚晚可喜歡它了,只要出現那貓的影,晚晚便不會安安分分地呆在這屋子裡了,想來啊是春天快來了……”
語末,那趣味的口氣,連明晰都頓時忘了上的寒冷,莞爾一笑:“你倒真是,我舍不得你生育之苦,仔細讓人看著你,這回怕是防不住了,可是喜歡上人家了?”邊逗弄著晚晚,邊對著晚晚說著,說完,不知想到了何事,角有些僵,冷氣又撲面而來,傷到至多反而累極哀默,不住了口,然後順著晚晚的發,仔細梳著又道:“晚晚,連你都免不了要這般的苦楚了?”
“……那貓可喜歡我們晚晚嗎?”
“聽聞是一只甚麼暹羅貓,可難伺候的很,老是見晚晚跟著他後頭,那貓連頭都不回,聽姚公館家的家僕說,這貓有皇室統,他們小心養著,比養著他們家四爺還要花大力氣得多了。”
“那可是犯愁的……”明晰不由地抱了晚晚,眸忽明忽暗,只到晚晚不舒服地扭了才意識到自己的失態。
失態……
今日已是幾番失態了。
猶記起數十分鐘前,的獨子維護著那子,猶如仇敵般地凝眉瞪視著,雖是被趙鈞默住了,可到這番地步,怎得起他這可笑的善心?
是錯了吧,從來爭強好勝,也盼這唯一的兒子能偉岸材,他豈能不敵視,對他如此嚴苛,只因他的日後是的全部,而許芳待他極好,只因到底不是親子,未來哪管得了其他,只知道一味護而已。
這般比較,是人都曉得如何選,不怨,但不能不痛徹心扉。
Advertisement
只是臨到頭來,已是不能用言語去訴說,只是心痛到極致,卻愈發靜了。豔致的臉龐如今眉梢都帶著頹廢靜婉的氣質。
發抖,終是撐不住了,嚅囁地喚道:“周媽,我冷。”
“小姐,我們趕仔細沐浴吧。”
見明晰發白,周媽終是不能再由著,不開口,年邁的嗓音帶著關切的強制口吻。
“好。”
一番洗漱下來,已好了許多。
住的是三樓洋房的最頂樓,為中院,他來的時候,屋的燈已熄滅,掐滅煙,終是在樓下佇立了良久,然後離至書房。
……
翌日,收到兩封信箋,一封是母親的,信上說:吾,這幾日傳聞輿論已盡吾耳中,吾足足想了五日,實在是氣難平,本直奔趙公館而來,只是汝父如今行事舉步維艱,凡事多有不便,多數要賴於鈞默周旋,故此,你多忍,多思,莫要沖,三思而行。
母親勸三思,從來要莫要被欺辱的母親也不免在當今局勢下,虛至此。
笑幾聲,在妝臺前看的,臉不慘白,原是本不用梳妝已經夠白了。
再一封竟是自瀘寄來的,是年時私塾學堂的舊友,董香之。
信上有些好似沾的印記,想來許是沾上了水漬,許是哭了一番,那人字跡清秀,寫得並不那麼流暢,明晰記得那人沒讀幾年書便嫁給了與自己已有婚約的男子,聽聞對方還是名門族,見著這字跡,就如格般,想到低眉順耳,靦腆的樣子。信上竟出多了明晰記憶中董香之幾分有的緒。
把母親的信箋放在一旁,方好不易收回緒,努力地平心靜氣地開始看起來。
只見信箋上寫道:
Advertisement
“隨安,這方與你通信,你莫要計較,你我已有家室,原不該擾你,只是我心有不甘,實難平心靜氣。
隨安……
他不我,這些年來,我侍奉公婆,謹守婦道,可他頑固地不我,就如我頑固地著他。
想來自是我多年一廂願,原以為他也是願意的。後來我本想順了他的意同他離婚孑然離開,但我自舉目無親寄人籬下,自懂事以來便呆在陶府,不及年便嫁與他為妻,維持生計的本事竟是半沒有,我惱,更恨我自己,我再三忍讓卻已不知讓到何種地步才能他滿意。三日前,他邀任職國立中央大學藝系主任,我們將舉家搬遷至南京。
此信不知你幾時收到,甚至能否收到,眼見如今政局混,我這等婦人亦到憂心忡忡,我曾妄想申請公費留學,到時歸來令他另眼相待也算不枉冷落一場,只是皆是忍之恨的奢一場,我本沒讀過多書,亦沒走過多路,至多不過柴米油鹽醬醋茶罷了。
我也不知為何頭裡一熱寫這封信與你,你我已不見數年,只是當年學堂裡,你帶著我們造那八文許先生的反,好似還在眼前,我想著這世間沒有你不能解決的問題,因你一貫是幹脆決絕,傲然剛烈,熠熠生輝,你應是覺著我的話過於恭維了罷,可這卻是我心裡話。
心中滿是飄搖竟不知向誰訴說,只能向你,向那個小時領著我們造反的你訴說,若是能與你在南京見上一面,想來應是我至大的安。
在此,你一切安好,勿回。”
凝眉許久,才一牽齒,竟是一陣哭笑不得。
這世間沒有你不能解決的問題。
原以為也是這樣,不曾想,是多心了。
Advertisement
“小姐,茶。”
這時,周媽推開門,送上上好的景德鎮白瓷杯,剎那茶香四溢,這時,一低頭,才低呼道:“小姐,你怎地連鞋都不穿?”
竟是赤足在妝臺前,一雙腳凍紅得不行,知自家小姐生平最重視面,特別是著裝禮儀。
明晰上頭原是有個姐姐,一次,老爺牽著那孩子出門,只是因老爺一時不查那孩子竟從二樓銅質樓梯間的細中跌落至一樓客廳,其模樣人不忍心去看,因此,自小姐出生,不知是出於愧疚還是冥冥中的有意彌補,明晰顯然是明家唯一也是就連明鉉都不可及的掌上明珠,從前名竟是“懷珠”,可見其鐘的程度,只是懂事後連同家族長輩皆略嫌此名甚是俗不可耐,老爺夫人也便不再那麼了,反而“隨安”二字喚得多了。
而自小老爺夫人請來的家庭教師在課後與的便是各國禮儀與著裝考究,每季都有裁師傅來趕制裳,對搭配也素有心得,從不見渾有一不對,即使淋過雨,跌過腳亦是明傾城,豔姿得,怎會如現下這般,連鞋都不穿,甚至半胭脂不上,素慘白,竟是比昨日整個子得渾還要不堪。
沒有作答,只是著窗前,微雨過後,斑駁樹葉皆像是煥然新生。
半晌,回神。輕輕折好兩封信,完好地將其放白法式家的一格屜裡,方道:“周媽,將我那些首飾拿去變賣些,能籌多是多。加上我以往的積蓄,應是足夠了。”
“小姐?您……”
周媽不由瞠目,已是不知該如何問其原由,只見那素白凍紅的手關起窗,只聽得窗外鳥鳴陣陣,人心憐。
半晌,目如水,從未有過的寂靜著淡的澤,方緩緩道:
“我已是籠中鳥,但盼他人能自此……海闊天空。”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814 章
醫妃逆天:腹黑鬼王猛纏妻
她,21世紀的天才鬼醫,一刀在手,天下任她走。一朝穿越,成了宰相府人人可欺的廢材大小姐。 他,鐵血無情的戰神王爺,亦是行走在生死邊緣的黑暗之王,卻因功高震主而被害成殘廢。 一場算計之下,她被賜給雙腿殘廢的王爺,成了整個北齊茶餘飯後的笑料。 初見,她一臉嫌棄:“玄王爺,我爹說你不舉,莫非你軟到連椅子也舉不起來?” 再見,他欺上她的身:“女人,感受到硬度了?” 感受到身下某物的變化,慕容千千嬌軀一顫:“王爺,你咋不上天呢?” 夜景玄麵色一寒:“女人,本王這就讓你爽上天!”
171萬字8 51238 -
完結1833 章

惡後歸來:陛下,娘娘又動手啦!(半支菸頭)
“陛下,娘娘已關在後宮三天了!”“悔過了嗎?”“她把後宮燒完了……”穆王府嫡女重生。一個想法:複仇。一個目標:當今四皇子。傳言四皇子腰間玉佩號令雄獅,價值黃金萬萬兩。穆岑一眼,四皇子便給了。傳言四皇子留戀花叢,夜夜笙歌,奢靡無度。穆岑一言,四皇子後宮再無其他女子。於是越國傳聞,穆岑是蘇妲己轉世,禍害江山社稷。穆岑無畏,見佛殺佛,見神殺神,利刃浸染仇人鮮血,手中繡花針翻轉江山社稷,光複天下第一繡房。眾臣聯名要賜穆岑死罪。四皇子卻大筆一揮,十裡紅妝,後座相賜。後來,世人皆知。他們的後,隻負責虐渣,他們的王,隻負責虐狗。
320.6萬字8 34351 -
完結600 章

娶妃后,我有了讀心術
【異能】大雍十三年六月,雍帝選秀,從四品御史之女顧婉寧,使計想要躲過選秀,原以為計謀得逞能歸家時,其父因扶了當今圣上一把,被賜入六皇子府為繼皇子妃。夫妻二人大婚之后相敬如冰,直到六皇子中了藥被奴才送回正妃院中。隔日,六皇子竟是能聽到別人的心…
110.2萬字8 15504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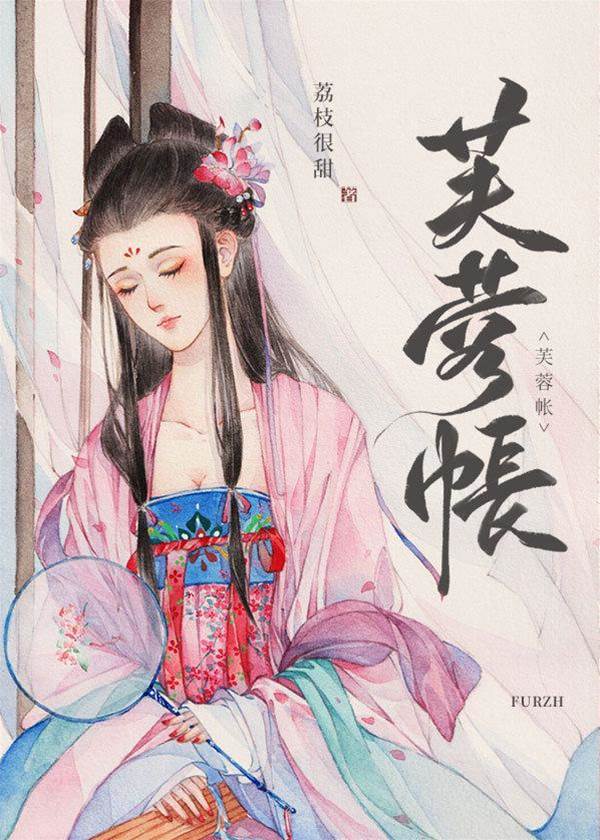
芙蓉妝
文案:錦州商戶沈家有一女,長得國色天香,如出水芙蓉。偏偏命不好,被賣進了京都花地——花想樓。石媽媽調了個把月,沈時葶不依,最后被下了藥酒,送入房中。房里的人乃國公府庶子,惡名昭彰。她跌跌撞撞推門而出,求了不該求的人。只見陸九霄垂眸,唇角漾起一抹笑,蹲下身子,輕輕捏住姑娘的下巴。“想跟他,還是跟我?”后來外頭都傳,永定侯世子風流京都,最后還不是栽了。陸九霄不以為意,撿起床下的藕粉色褻衣,似笑非笑地倚在芙蓉帳內。嘖。何止是栽,他能死在她身上。-陸九霄的狐朋狗友都知道,這位浪上天的世子爺有三個“不”...
37.3萬字8 29264 -
完結191 章

新婚夜,瘋批太子奪我入宮
【強取豪奪+追妻火葬場+瘋狗男主】十六歲前,姜容音是嫡公主,受萬人敬仰,貴不可攀。十六歲后,姜容音是姜昀的掌中嬌雀,逃脫不了。世人稱贊太子殿下清風霽月,君子如珩
34.6萬字8 3881 -
完結121 章

假千金和真少爺在一起了
薛瑛在一次風寒後,意外夢到前世。 生母是侯府僕人,當年鬼迷心竅,夥同產婆換了大夫人的孩子,薛瑛這才成了侯府的大小姐,受盡寵愛,性子也養得嬌縱刁蠻。 可後來,那個被換走的真少爺拿着信物與老僕的遺書上京認親,一家人終於相認,薛瑛怕自己會被拋棄,作得一手好死,各種爭寵陷害的手段都做了出來,最後,父母對她失望,兄長不肯再認她這個妹妹,一向疼愛她的祖母說:到底不是薛家的血脈,真是半分風骨也無。 薛瑛從雲端跌落泥沼,最後落了個悽慘死去的下場。 一朝夢醒,薛瑛驚出一身冷汗,爲避免重蹈覆轍,薛瑛乾脆一不做二不休,重金僱殺手取對方性命。 缺德是缺德了一點,但人總得爲自己謀劃。 誰知次次被那人躲過,他還是進了京,成了父親看重的學生,被帶進侯府做客。 薛瑛處處防範,日夜警惕,怕自己假千金的身份暴露,終於尋到一個良機,欲在無人之際,將那人推下河,怎知自己先腳底一滑,噗通掉入水中,再醒來時,自己衣衫盡溼,被那人抱在懷中,趕來救人的爹孃,下人全都看到他們渾身溼透抱在一起了! 父親紅着老臉,當日便定下二人婚事。 天殺的! 被迫成婚後的薛瑛:好想當寡婦啊。
31.3萬字8 11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